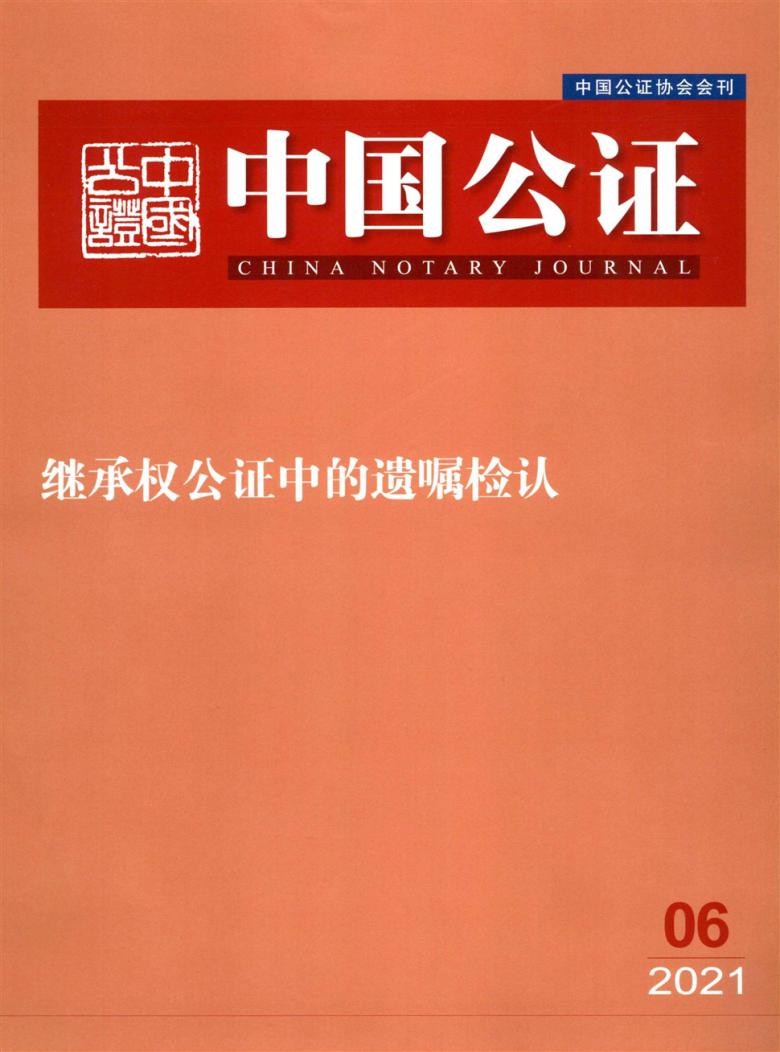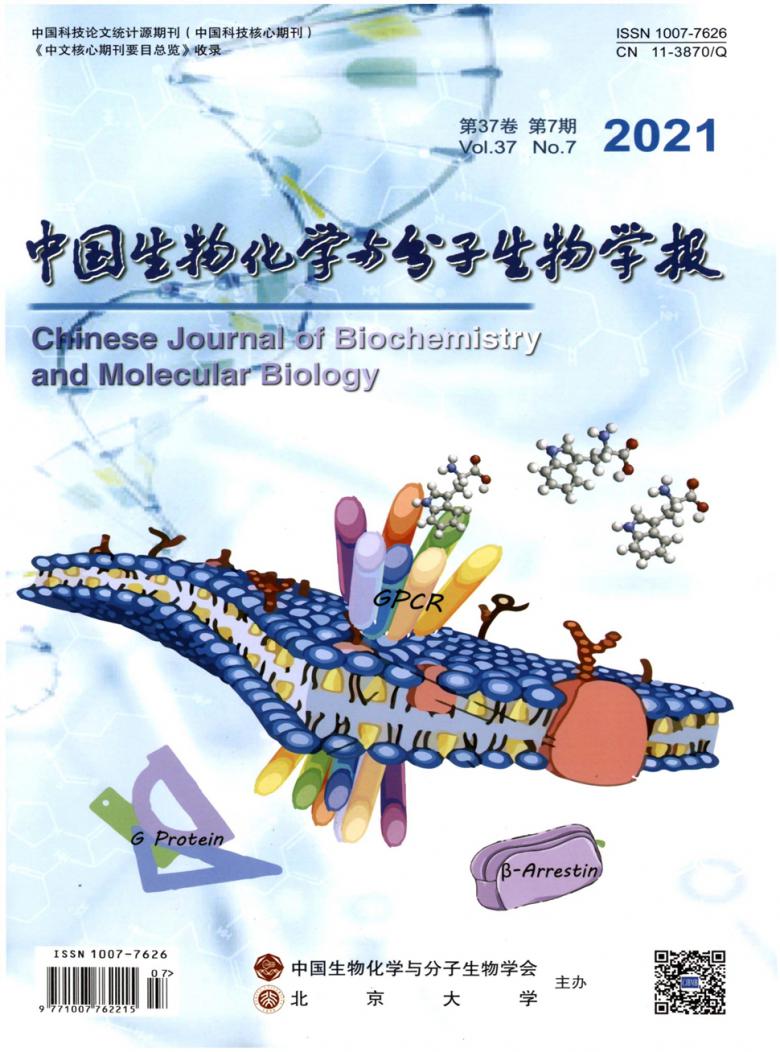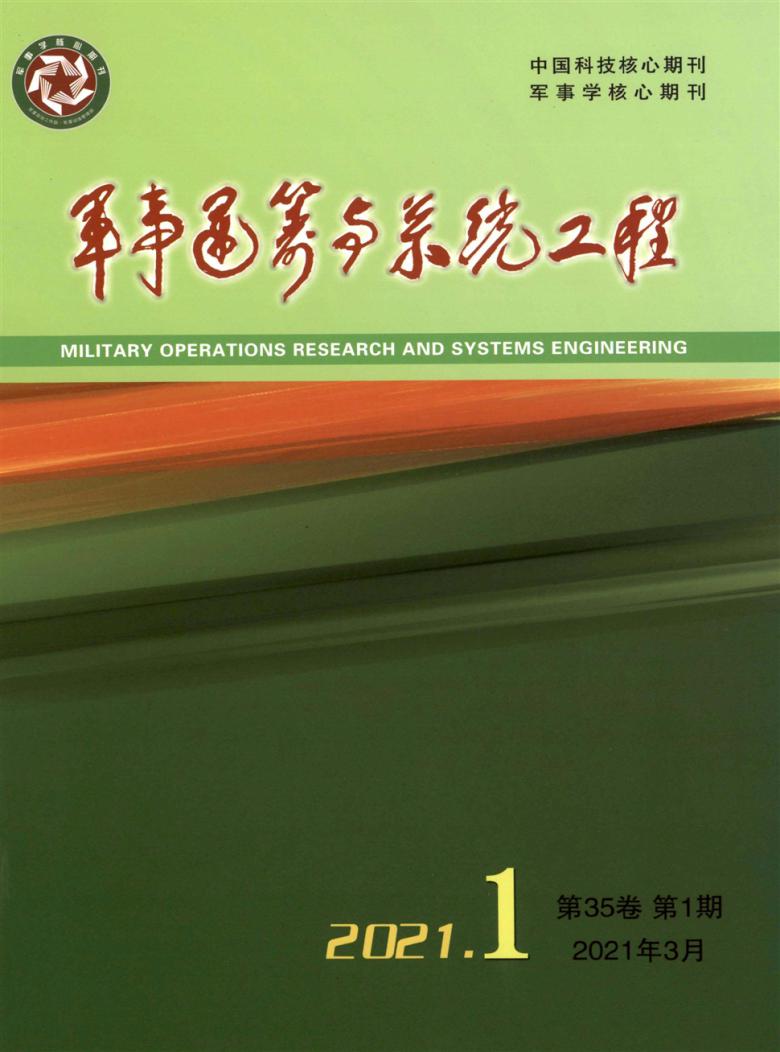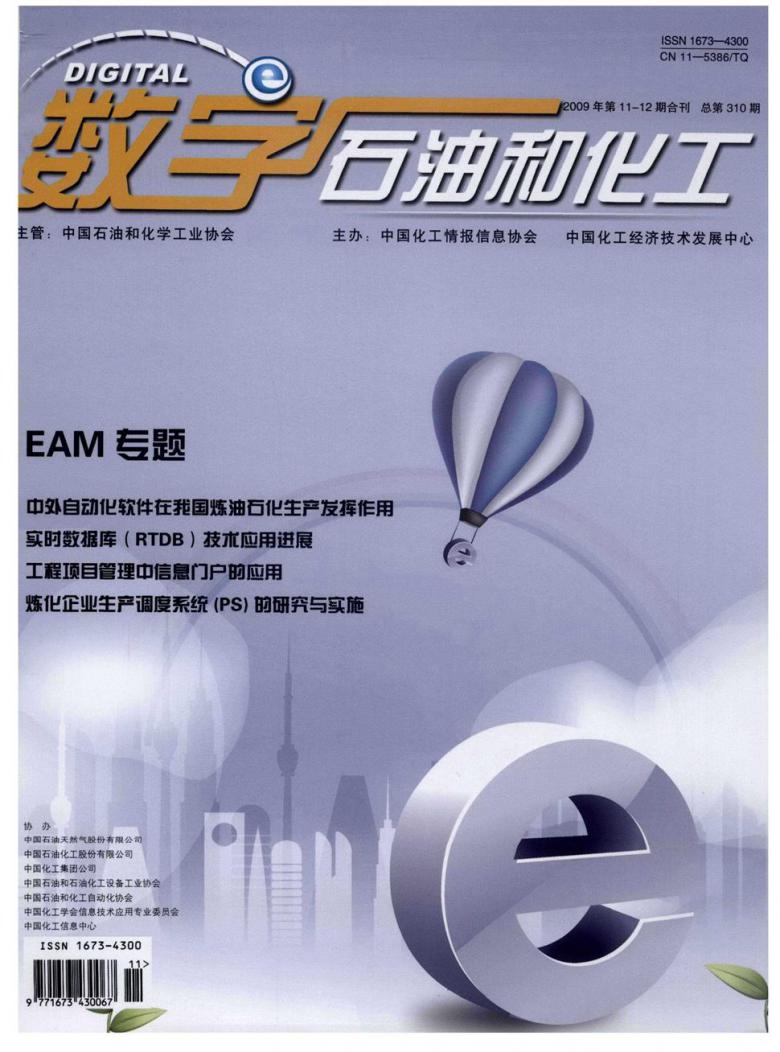现阶段中国农村血缘与姻缘博弈现象探析
张庆国 2006-01-20
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村特别是南方农村,家族势力重新“抬头”,并且修家谱、立家庙等活动颇为盛行,这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界引起了一股家族研究热。以杨善华、刘小京、郭于华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学者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家族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即将社会学对家族的研究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上,让人们“从最常见的农村社会现象中去发掘和显现原本是潜在的家族意识和家族活动,进而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到家族存在的意义及其在变动的农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1]。这就使家族研究跳出了历史文献、组织结构和风俗礼仪的拘囿,与农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可以说是社会学对家族研究的巨大贡献。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在实际运用“家族”这个概念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姻缘关系归入了家族之中,认为“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2]。这种“泛家族”化的研究优点是简化了概念,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家族的演变、现状以及它在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上,避免了多面用力。但它过于强调血缘与姻缘的同质性、统一性,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到一定程度,我们却突然发现,两者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协调,姻缘关系正在不断融入原先由血缘所统治的中国农村“差序格局”,“进入了过去只包容血缘关系的同心圆中”[3],并且正在与血缘关系为争夺这个同心圆的中心位置展开一场博弈。至于博弈的结果,尚不得而知,有的学者如杨善华认为,姻亲关系在家族关系中作用的增大已经威胁到男系家族关系的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4];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塘东村30个住户的社会互助调查却发现血缘关系在农村社会互助中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见下表)。不论哪一方占有优势,现在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姻缘关系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典型的例证是农村生产合作中,姻亲合作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清楚地认识,本文拟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对现阶段农村姻缘、血缘的博弈过程和现状进行初步探析,并进一步从农村家庭关系、继替关系、婚姻圈的变迁等角度对促使姻缘关系提升的诸多因素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思考和总结。
数据来源: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第142页
二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思路与来源: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继续坚持了社会学的家族研究传统,采用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事件——过程”研究法,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农村社会单个的社会成员身上,分析其在处理农村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对血缘、姻缘的倚重和认同程度,从中探寻血缘、姻缘博弈的过程和现状。
2003年寒假期间,作者深入山东省莱芜市的一家乡镇企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访问,从中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现介绍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
│
┌──────────┐
李A(过世) 李B
│ │ │
┌───┐ ┌───┐ ┌───┐
李C 李D 李E 李F 李H 李L
│
李G
个案背景:
(1)上图为简化的家族谱系图,本个案涉及的家族成员主要有李B、李C、李D、李E、李F和李G,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李G和李F的关系要明显好于李G与李C的关系,尽管他们血缘上相对较远。
(2)九羊公司为山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员工2000多人,95年乡镇企业改制,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将下属车间承包给个人,由个人负责招工,并按规定每年上缴企业一定利润。
个案内容:李G,28岁,高中文化,曾参过军,退伍后回乡待业。李G由于在外历练多年见过世面,95年乡镇企业改制期间,便组织家族成员集资承包了九羊企业公司的一个铸造车间,参加集资的有李G和其父李D,以及三个叔叔书C、李E、李F,集资者同时也是车间工人,后来因人手不够,李G又将好友韩二招进车间,车间的经营权记在李G名下。在利润分红上,李G及其父亲李D占50%,剩余四人占50%,在头半年里,企业发展比较顺利,企业效益非常好,为了扩大企业规模,李G和其他成员商量着增加企业人手,而这时恰巧李G的小舅子贾三高中毕业正急于寻找工作,会驾驶拖拉机的二姨夫王四正农闲在家,李G便想将他们招进企业,但不巧的是本家李H和李L主动找上门来,让给安排活干,迫于情面以及考虑到企业的合伙性质,李G只好先将两个本家安排了,但这件事使李G产生了将企业变成自己的打算。又过了半年,企业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先是作为长辈的李C和李E经常上班迟到或以各种借口旷工,而作为晚辈,李G虽看不惯,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后来,随着李G企业主地位的逐步稳固,便开始以作假账的方式偷偷将利润划归自己名下,开始时,其他成员并没察觉,但时间一长,他人突然发现,货物销量在不断增加,而他们分得的利润却没有增加,于是便开始怀疑和私下议论李G.。特别是李C和李E唆使李B运用族长的权利,在家族仪式特别是逢年过节的聚会中影射李G,劝戒他做事不能太黑,要照顾家族利益,这样李G和李C、李E的矛盾不断深化。后来,李G多次暗示李C和李E要他们主动离开企业,但由于企业利益颇丰,李C和李E仍坚持留在企业中。97年乡镇企业效益普遍不好,李G以九羊公司裁员为名将李C、李E解雇,其实当时李G的车间并未受到影响。过了一个月,李G便将小舅子贾三和二姨夫王四召进企业。现在企业运行良好,但李G和李C、李E除见面寒暄外,已基本不相来往。当问及其他村民对李G的行为的评价时,村民们好像并未有多大的反应。
(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介入已经改变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5]。案例中,李G之所以选择了贾三、王四,因为他们或是有知识、年富有为,或是拥有专项技术,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对血缘宗族成员的解聘,也出于同样的利益考虑。在这里明显的透露出一个信息,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同样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疏远[6]。“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标准的巨大挑战,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冲突中,“利益”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人情”+“利益”的双重人际关系调节标准已经建立。另一方面,自我中心主义的关系格局正在形成,家族中心主义正在被自我中心主义所取代,农村基层社会关系网络正在由家族关系网络向家庭关系网络过渡。家族中心主义以家族为本位,个人不过是家族网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它强调家族的整体性,鼓励个人对家族的责任,甚至是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而自我中心主义以自我为本位,个人处于家庭网络的中心位置,家族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之外还有姻亲、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等组成部分。在个案中,企业建立、演化、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显示出了自我中心主义对家族中心主义的强大优势。
正是利益认同的加剧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两者互动共同导致了血缘认同的下降、姻亲关系地位的提升,而利益认同的加剧、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体现出的是人们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衍化。
(二)从案例中我们还应看出,姻缘关系对血缘关系网络的侵入,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社区记忆的弱化”,所谓“社区记忆”是指“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7]。如果“社区记忆”较强,传统的伦理道德对村民仍具有普遍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李G的举动肯定被认为是“胳膊肘子往外拐”的行径,唾沫星子淹死人,李G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及村民们的好评,这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李G往往不得不向强大的社会舆论低头[8].但事实是49年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实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体系,宗法解体,使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依托和支柱,“社区记忆”完全消失;79年后随着国家权力退出基层,“社区记忆”有所恢复,但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传统宗法又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社区记忆”再次走向弱化。[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G才敢于做出清退宗族成员,转而雇用姻亲成员的举动,个案中村民的反映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条件是农村社会特殊的信任机制。现阶段,我国城乡信任机制具有巨大的差异,城市信任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契约信任”,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契约签订,从而对对方产生了稳定的预期,继而产生了信任;而农村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互动信任”,互动越频繁,对对方越可能产生稳定的预期,信任度也就越大。这就使在由血亲、姻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组成的人际关系圈中,从内向外,随着互动频率的依次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因此,在个案中当血缘关系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后,姻亲关系便成为了首选对象。 三 具体原因分析
上文我们主要是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对血缘、姻缘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了利益导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在这场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一个个案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下面我们着重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继替关系、婚姻圈的变迁等方面对姻缘地位的不断提升进行归因,具体探讨一下利益导向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导致现阶段农村血缘关系下降,姻缘关系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重心的转移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两个方面。
费孝通认为“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连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10],也就是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其中夫妻关系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是姻缘的缩影,而亲子关系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缩影。共存就意味着矛盾,两者总有一个要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则要居于从属地位。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注重的是亲子而非夫妻关系,婚姻的缔结不过是传宗接代,“上以继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一种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妇女的地位甚至与生育子女的数目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姻缘关系不被重视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断的弱化,而家庭的生产、娱乐、消费等功能得到了突出,婚姻的质量正在不断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重心正在不断有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调查显示,在农村社会网络亲属关系中,按关系的构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11],夫妻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凸显。
在夫妻关系上,男子集权正在向男女平权过渡。主要体现在:(1)家务分工的平等性。现今“甩手丈夫”越来越少,夫妻之间逐步趋向合理化分工(2)家庭决策的协商性。在重大礼仪活动的操办、大宗消费品的购买、家庭投资、子女职业选择等方面妇女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3)家庭经济的民主化。夫妻双方消费基本持平,妻子经济相对独立。(4)闲暇生活的独立性。女性逐步从操持家务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夫妻双方特别是年轻夫妇之间平等的享受闲暇时间。[12]家庭中女性地位正在不断的提升。
在亲子关系上,家长集权制正向民主制过渡。父母在家庭中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在婚姻、教育、职业、交友等活动上具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父母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特别是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大部分年轻人为“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或“完全由本人决定”,父母包办婚姻已非常少见。在包办婚姻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父母的社会关系圈,而婚姻自由的情况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子女的社会关系圈,由于婚前双方便早已熟悉,结婚后向姻亲关系偏重的比例也就大大增加。
总之家庭关系的变迁,使夫妻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度也在不断得到增强,这些都有利于姻亲关系地位的不断提升。
(二)社会继替关系的变迁
建国后随着分家现象的普遍化,家庭继替关系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农村社会在家庭继替上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财产的分配、义务(如赡养义务)的履行是约定成俗的,因循着“习惯法”,有着固定的继替标准。这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纷争的作用,即使分配不公,义务的履行不等,因为祖辈们也是这样的,人们在心理上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平等的原则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成为了日常生活规则的重要标准,而平等作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标准是难以衡量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种情况下,在家庭财产的分配和赡养义务的履行上所产生的利益纷争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对血缘关系的“杀伤力”是难以估计的。现在农村社会,因利益之争而导致“兄弟隙于墙”“父子对簿公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而姻亲关系之间,既不存在财产继承上的纠纷,也不存在义务履行上的矛盾,在血缘关系因利益之争被弱化的情况下,姻缘关系的情感维系作用、互助作用便得到了突显。
(三)婚姻圈的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不断扩大,而是在不断的缩小,并且村内通婚和邻村通婚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霍宏伟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的通婚范围的研究发现建国后农村社会婚姻圈的变化趋势是一条起始上下波动,后半部分不断下滑的曲线。(见下表)
数据来源: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
特别是1980到1990年这十年,婚姻范围的平均值已有7里降到了5.87里[13]。婚姻圈的缩小,直接带来的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互动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同村内血缘宗族正在由聚族而居向分散居住转化,宗族圈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宗族成员的互动频率在减少,宗族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
(四)择偶标准的变化与离婚自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补”的心理使然,“人们不仅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事业有成绩等隐性的能转化为物质潜能的因素,同时依然注重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现行的经济实力,人们对物质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体验。”[14]由此可见,择偶标准中利益考虑仍为首选,情感需求仍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利益导向使人们在择偶时,自觉不自觉的把对方的家庭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相对比,并把对方家庭在经济、权利、声望等某些方面的特殊优势作为择偶的重要标准,姻亲的这种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性”也为将来向姻亲的倚重埋下了引线。
姻缘关系具有获致性的特点,这就使姻缘关系既可以通过法律的缔结而确立,也可以通过法律而解除,并且现在人们在离婚上越来越自由,“合则来,不合则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离婚特别是女子离婚不再承受来自双方家庭、单位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再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在这种情况下,离婚率不断的上升,人们的婚姻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婚姻中感情的维系和调试也越来越受重视。而血缘关系由于具有先赋性,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正是这种永恒性使人们往往忽视了对它的调试。历时一久,血缘认同必然下降,姻缘认同必然上升。
四 结论与预见
(一)从以上的个案与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血缘与姻缘的博弈过程中,导致血缘地位下降、姻缘地位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就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价值理性由于过分注重过程而忽视结果,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理性,只适用于血缘地缘这种初级组织。而工具理性它包括了对目标、利益以及达到利益的手段的全盘考虑,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正式的组织以至整个国家、全世界[15]。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血缘认同向姻缘认同的转化是值得肯定的。
(二)随着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可以预测,当血缘姻缘关系不足以满足个人发展对稀缺资源和合作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冲破血缘姻缘的樊篱,转而在亲属关系之外建构新的社会关联,启用新的社会支持。以家族企业为例,先是以血缘成员为核心,然后是姻缘成员的加入,现在朋友、乡亲、熟人正在家族企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终随着亲属成员的不断减少,“外人”、生人的不断增多,家族企业必将完成向现代企业的转轨。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的信任结构的影响,人们在建构这些关联时,并非以契约、协议为中介,而是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来的业缘关系转化为类似血缘的关系即拟似血缘关系,从而使之融入“差序格局”范围内[20]。这就出现了一种正式关系非正式化的趋向。同时由于“差序格局”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像“摊大饼”一样,饼越摊越大,也越摊越薄,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率减少,感情的密度不断降低,这又导致了一种非正式关系正式化的趋向。两种趋向互动使“正式关系带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时也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16]。
(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虽然现代社会削弱了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17]由于血缘的先赋性以及农村聚族而居的状况,血缘始终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之中 ,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起着重要的情感维系作用。只不过这种维系作用正在从“事件性”领域不断退出,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婚丧嫁娶等“仪式性”的活动和日常生活领域。血脉不断,亲情就不断,“血毕竟浓于水”。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岳庆平:《家族文化与现代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3]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J],《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4]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J],《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5]折晓叶:《村庄的再造》[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J],《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7]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集刊》2000年第4期
[8]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9]徐晓军:《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J],《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J],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59页
[11]张文宏:《天津农村居民社会网》[J],《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2]邓伟志、许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J],《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13]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J],《社会》2002年第12期
[14]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5]潘必胜:《家族化企业能走多远?》[J],《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1期
[16]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J],《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7]Eisenstadt: Tradition, Change and Modernity.[M] New York1973年版 第209-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