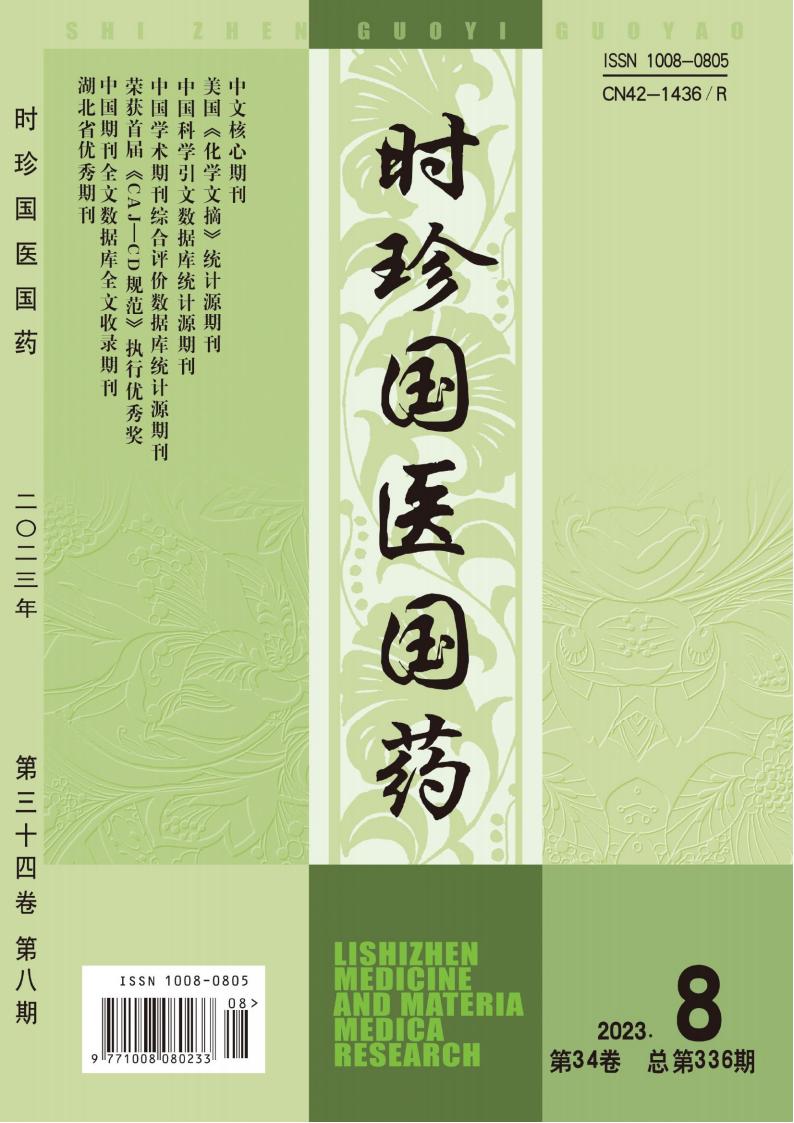论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朝军
「内容摘要」 本文比较分析了大陆法系以德国为代表的行政本位强制执行和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代表的的司法本位的强制执行模式以及各自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起源和形成原因以及现实的缺陷,以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本质属性为突破口,从我国文化政治历史,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三方面论述,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该回归行政机关。并站在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角度,从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建构,司法审查方式的转化,告诫程序的设计和救济制度体系的完善四个方面,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提出建议和构想,以期实现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正常有序运转,最终达到行政经济原则和权利保护原则的统一和谐。
「关键词」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 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 告诫程序 救济制度体系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1]作为冲突着的社会里一种普遍的存在,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向“福利国家” 转型的历史潮流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痼疾已经越来越显出对行政效率的滞痼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保护的软弱。本文正是基于深切关注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前提下,提出重新建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以希望达到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分配和制约,实现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和谐。
一、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评介
(一)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产生背景概要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模式源于80年代初。[马怀德教授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律建设处于停滞不前是甚至倒退的阶段,严格地讲此时的行政处理决定基本上依靠行隶属关系得到执行。”笔者赞同此观点,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拨乱反正”之后我国法制才逐渐恢复。参见马怀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年第2期。]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复苏,我国原有的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另外,社会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纵深,也需要考虑如何在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同时做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在发挥行政权积极管理社会事物的同时,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其标志是《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执行程序。]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陆续颁布的大多数行政法律和法规都对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作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执行主体的划分及原因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划分大致有以下三种:
1、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行政机关为其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采取相应的措施强迫当事人履行或达到与履行相一致的状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61条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 值得指出的是,拥有自力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相当少,仅有海关、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
2、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行政机关为其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经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依民事诉讼执行程序强制执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方式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占主导地位。此种立法模式已经形成习惯,以致于90年代后,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已无对违反义务而需强制执行的执行机关作出具体规定。这并非立法的疏漏,而是由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一方式确认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即法律未授权于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均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90年代的许多立法都未对执行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34条的处罚条款就没有规定处罚的权限和处罚执行机关。]
3、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这是指某些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选择自力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没收或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方式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例外,也只有在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才有选择权。
以上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执行主体的划分是建立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上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被学者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2]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呢?[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而法院在执行中占主导地位,这与中国整个法律体系都与大陆法系近似的情况是十分不合拍的;而事前的司法审查方式(形式审查)又与英美法系大相径庭。因此,笔者认为这是经过中国改造的十分有特色的执行体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对行政权的担心。这是基于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监督行政权运行,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滥用的理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财产等重大事由的权力,其执行一旦做出就可能会给公民造成不可挽回和补救的损失,因此需要提前司法审查程序,防止这一危害的产生。“政府部门总的来讲是卓越的;但仅仅靠行政法与他所规定的监督与制裁不足以防止这些事件”(事件是指权力的滥用)。[4]因此,在做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审查,对其合法性进行事先的判断,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给公民人身、财产带来的损害。
2、对行政人员的担心。由于我国行政公务人员的素质不高,而且“官本位”思想严重,因此给予他们过大的权力,会助长这一不正之风的蔓延,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
3、成本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势必在行政机关部门下增设新的执行机构,在我国行政机关本身就臃肿混乱的情况下,会导致部门的重复设置和权力交叉,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可能会成倍地增加,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新的浪费。
4、国家利益的需要。由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可以减少行政强制执行中的违法情况,在没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完善的程序规则和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国家赔偿的负担。
(三)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实践运行中的缺陷
尽管上述的考虑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有合理性,也确实对行政强制执行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执行模式在法理上始终是有缺陷的,对此,笔者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细的论述。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以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在社会实践运行中的不足之处。
1、破坏了行政强制执行的完整性,严重地阻碍了行政效率。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过分地强调了司法审查的作用,这一理念导致了执行申请往往需要经过冗长的申请程序,法院对其审查的费时也比较多,而且由于我国行政审判庭和执行庭是分离的,因此,申请机关往往需要来回奔波于两庭之间;而且由于两庭不可能完全协调,因此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拖沓繁冗。“程序属于外壳,而效率属于内核。具体表现为程序为偏,效率为大;程序为目的,效率为手段;程序为形式,效率为本质;程序为机器,效率为产品。”[5]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颠倒了程序和效率的关系,跨越了司法和行政两权,人为地破坏了行政执行的完整性,延缓了其执行的空间。
2、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软化,执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民间流传“偷树的不怕法,管树的怕违法,公检法没办法,《森林法》是豆腐法” [6]的顺口溜。这固然指出了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的软化。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规定从立法者主观的理想来讲是对司法权的尊重,但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直接导致了行政机关威信的降低。“如果我们把一种要求做为政策来考虑,那么,我们必须同样地考虑另一种要求……如果一方被视为权利,另一方被视为政策,或者一方被看作是个人利益而另一方被看作社会利益,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无助于做出决定。”(在美国,社会利益往往冠之以政策的名义)[7]所阐述的平等的观点一样,我们应该平等、公正的看待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利弊,而不应戴上有色眼镜,如果歧视性地看待行政权的弊端,那么其优势也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
3、混淆了行政强制执行权主体,不仅造成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权责划分的混乱,还严重地破坏了司法的中立性和裁判性。“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常采用形式而非实质审查,使得很多申请执行的案件流于形式,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8] :“行政机关与法院联手设立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等机构,法院出名义,行政机关出钱出办工设施,共同强制执行”。[9]这些现象说明了我国把大陆法系(法国除外)和英美法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简单的嫁接是不成功的,一方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另一方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中立裁判的形象,行政强制执行的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4、相关配套措施和规定的缺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并未就法院在受理行政机关的申请后应在多长的时间内予以答复;如果法院不同意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的答复期等相关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往往会出现行政强制执行久拖不决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况,即少数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数额不大,范围较广的执行对象,也需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仅不能做到提高行政效率,反而可能导致行政义务人逃脱行政义务。
5、严重加大了法院的执行量。我们知道,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人民法院不仅要负责民事和刑事的执行,还要插手行政执行事务。在我国诉讼案件成倍增长,案情相对复杂的情况下,法院的执行工作日益繁重,众多的执行案件从客观上来讲削弱了其审判的职能。“执行难”成为了我国近年来困扰司法审判权运行的老大难的问题。
二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模式述评及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质属性的探讨
(一)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是指“特定的主体对一国行政强制执行法依一定的效果而确定的主要的立法目的,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整体风格和特征,是行政强制执行法价值取向的法律化。”[10]
由于各国法律文化、民主传统以及行政法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国形成了以行政强制执行权归属为划分标准的两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和法院介入的司法强制执行。
1、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这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国除外)的执行模式。其代表国家有德国、奥地利、日本。下面以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为代表简述这种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的模式。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以1953年4月27日颁布的《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1997年12月17日最近一次修改)为建构内核。这部执行法法典不仅为解决其本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提出了方案,也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提供了建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蓝本。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1]:(1)、强制执行的机关。原则上由行政机关处理行政强制执行。同时,行政机关也可以委托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官署和公法人一般不得实施强制执行。这样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机关下令权包括了强制执行权的国家政策。(2)、强制执行的方法。该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主要有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3)、强制执行的程序。该法以告诫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核心程序,辅之规定了诸如执行援助、搜索、证人立法、催告及在通知等。(4)、强制执行原则。强制执行原则在该法中体现为“比例原则” 、“适当原则” 和“最少侵害原则” .这一执行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执行权当然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然有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因此,只要行政决定一经做出,便产生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普遍效力。任何人不得非经法律规定变更或停止其效力。行政机关不但有权实施这种决定,而且也有义务实现这一决定的内容,这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行政的命令权和执行权应该是统一的。
2、借助法院介入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采用这种模式。下面以美国为代表简述这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
美国奉行严格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但是她将行政命令和执行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和司法审查之下。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除了极少数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外,原则上都是通过司法执行的方式进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中体现:[12](1)、由法院处义务人以刑罚。(2)、法院确认义务人构成蔑视法庭罪。义务人不履行行政机关命令所规定的义务,行政机关请求法院促其履行义务,法院判令义务人履行义务后,义务人仍不履行即构成蔑视法庭罪。(3)、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相对人履行义务。
这一执行模式的理念在于:司法权优于行政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权力,应该受到法院的最终审查。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公民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归属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行使。
(二)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质属性的探讨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在我国是有很大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执行权。[13]执行权的性质决定于执行依据做出时所体现的国家权力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具体行政行为,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是行政权力。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权同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力的性质是一致的,属于行政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司法权。该观点主要以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为立论基础,即认为凡是由司法机关行使的权力即为司法权。[14]这一观点深受英美法系“司法至上”原则的影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复合体。[15]这一观点同样也是以我过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为立论依据,认为强制执行中部分职权具有司法权的特点,部分职权具有行政权的特点。
笔者认为,确认一种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应该就一国现行法制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依据进行考察;同样地,也不能将实际生活中各种现实的其他权力因素的附合、渗透和交叉强加于其本质属性之内。换句话说,探讨一种权力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对该权力应然性而非实然性的考察。因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执行权,是一种管理权,因此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相比于“上位”的立法权,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执行权”。但两者仍有根本上的差别,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就在于司法权是判断权,而行政权是管理权。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16]“判断”是一种认识,而“管理”则是一种行动。“判断”的前提是争议的存在,司法权即是对存在于过去的是非、真假、曲直的客观证据的选择和确认,其全过程是建立在既定规则即法律和客观证据即事实之上的程序性、综合性工作;而“管理”则发生于整个现实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之中,非以争议的存在为前提,只要行政权认为有必要,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它都可以以“积极”的行为实施其管理活动,执行是管理的需要,也是管理之所以能达到目的的唯一方式,其内容包括了组织、管制、命令、许可、劝阻、服务、协调、警示等多方面。
“行政强制执行”这一短语的中心词是“执行”,“强制”是方法和手段,是执行的保障和威慑,它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客观上的使用手段。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行政义务人的强制,它是管理得以存在和作用的生命。如果管理不能执行,不能被尊重,不能有有效排除障碍的手段、方式和权利,那么管理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而管理的设立也没有必要。“执行”是目的,或者说是理想的,管理所期望达到的状态;也是“强制”的终极归属。“执行”在整个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关键。行政强制的“执行”使强制成为必要并依强制得以实现和完成。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决定,其产生和决定过程均以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为成立的要件,具有单方行为的性质。尽管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执行主体以人民法院为主 ,但其所执行的仍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并未因法院的执行而改变执行内容及性质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强制执行的根本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17]整个行政强制执行的应然运作过程都是一种“命令-拒不履行(客观因素除外)-强制执行-目的实现”的单线的管理模式性质,保证上述管理模式实现的根本因素,就在于其管理的强制力来源于先赋予行政权的公定力、执行力,而不具有一种平等对抗和公平辩论的司法性。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是执行权,属于管理权的一种,具有行政权的性质。“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8]把执行权交还给行政机关,将判断权交由法院行使,是法理应然的要求。
诚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并不当然地决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因为这种具有明显公权力性质的,且对于公民的人身、财产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和威胁的权力归属的决定因素还有很多方面[19]:1、效率的追求;2、公正的追求;3、行政权力行使状况的影响;4、传统和既有制度的安排和制约。但是基于上述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本质属性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应起决定作用。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和其强制执行机关的属性相一致,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总比两者相异的配备更为畅顺、合理。
另外,在考察一种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时,我们还需对人文历史传统、现时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加以足够重视。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下面几点将值得我们着重考察:
1、历史因素。我国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态下经过非充分民主化过程发展而来的。皇权、专制是过去一直以来的特色。行政具有强大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论是社会意识还是政治理论,都有一种集权的传统。只是由于近代改革、革命和“西法东渐”潮流的影响,宪政、民主等法制观念方才进入我国。但纵观我国的法制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宪政、民主的思想也只是略显进步,其茁壮成长的土壤仍未成熟。因此,那种司法优先(judicial supremacy)的司法执行体制(rigime judiciaire)并非我国传统,其成长也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2、经济发展现状和法制环境。尽管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客观理智地讲,我国的经济水平仍然不高,法制环境仍需改善。在对兼顾管理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巨大任务的行政权予以考虑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成本节约,不能不讲求行政效率。“从一般意义上讲,效率是指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20]效率与时间的消费、费用的消耗、人力的使用、程序的合理以及结果的好坏息息相关。效率的追求就是要以最少和最小的投入换来行政管理目的最大和最优的实现。行政成本和效率应该是行政机关生命的底线。从理论上讲,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不需其他机关参与,不需其他机关转手,肯定会减少权力部门的跨越和流转的环节,达到费用和程序的精简,实现效率的提高。另外,对现实的法制状态,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从第一件“民告官”案件的出现,到近十年来行政诉讼案件的成倍攀升,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复苏和进步;政府公务人员的选拔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素质的不断提高;立法机关对政府监督检查方式的具体化等,这些都标志着我们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认为行政强制执行不受司法机关事先审查的制约,会导致我国脆弱的司法审查遭到破坏,进而影响法制与法治,笔者以为,也不应该用牺牲行政机关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而应该采用综合治理的观念,从司法审查方式、程序规则和救济制度等多方面来防止和恢复行政权可能带来的危害。
3、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属于经济转型时期,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在这样一个急剧要求行政权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的时代,笔者认为扩展行政权的执行范围是有益的。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维护和管理手段,经济越发达,对管理能力的疏导和排除障碍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的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21]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职能也必将围绕如何维护经济交易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与国际社会接轨等诸多管理和保障事务展开。给行政机关更多的职权,以发挥其管理的灵活主动性和严肃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我国和其他许多向“ 福利国家”迈进的西方国家的必由之路。
有资料显示,自1989年到1999年底10年间,人民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和一审受案数相比处于直线上升的趋势(见下表)[22]而且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非诉行政执行案远远多于一审的受案数。以1998年为例,非诉执行案件竟达到了一审受案数的3.32倍。而1999年,法院受理了356,117件非诉执行案件,裁定不予执行的5906件,占总数的1.66%,强制执行43,609件,占12.25%,自动履行243,211件,占68.30%.年度 一审受案 非诉执行案 年度 一审受案 非诉执行案
1989 9934 7455 1994 35083 136795
1990 13006 9919 1995 52596 191258
1991 25667 15687 1996 79966 256897
1992 27125 65156 1997 90557 270133
1993 27911 88971 1998 98463 326783
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
1、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大幅度增长,说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现象正在与日剧增,这与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模式引发的行政机关权威弱化和执行不力的因素休戚相关,同时也大大加重了人民法院的执行数量和执行压力。
2、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不予执行的案件数量相当少,仅占1.66%,可以基本上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大多数没有重大的违法情况,证明我国行政人员的素质还是有了相当的提高,行政处罚决定机关作出的执行决定是有相当正确率和合法性的。
综合上面所有的论述,我们从法理上、从现实的基础中都可以找到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到行政机关的合理理由。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弱化现行司法审查和法院执行,会导致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保护的不力,会给他们的权利造成损害。但笔者认为上述的担心是多余的。笔者完全同意孙笑侠教授提出的现代行政法是“控权法”的观点。“控权法”是一种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而积极驾驭支配行政权力,它是对行政法功能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法民主或者自由价值的一种定位”。[23]“控”是驾驭支配的意思,而“限”是阻碍、阻断的意思。“控”是积极的而“限”是消极的,我们要更好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应该以积极的方式掌控强制执行权的优缺点,而非一味被动消极地防止其不足。“依法行政”并不一定推出司法权一定要在行政执行权行使前就要控制,也不一定推出其要由法院代理执行,何况这种“限制”也不能当然地保证执行的合法。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改造司法审查的阶段、方式和范围;进一步完善行政人员的选拔;加强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体系;强化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定完善的程序规则等多种方法多管齐下的方式和理念来构筑一种既能发挥行政权力灵活、快捷积极作用的特点,又可以使其在规定范围里实施,减少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损害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
三 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几点构想
“如果能够使一个程序规则同时符合若干价值选择,那就是理想的。如果在若干价值选择中必须择其一,显然根据行政权归属主体的关系原理,效率选择应当为先。其他若干价值取向应服从效率的价值选择。作为能够促成效率的优良程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必须是规范化的;……二是必须是最廉价的;……三是其确认的环节应当少;……四是程序规则所确认的行为序列应当短,而且不能间断。”[24]笔者将以以上文字所阐释的精神为构筑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核,对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提出几点构想,以期达到“如果该国执行管理机构在履行其职责时遵循正常程序,……又如果存在某些措施防止这些机构滥用权力,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法制度的理想状态”。[25]
(一)关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设想
基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应该借鉴德国模式。但是是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来执行还是由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来执行呢?笔者认为,为了相对地集中人、财、物力,降低执行成本,更容易规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尽量防止执行中的违法情况,应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之所以考虑在县级以上,一是因为县级为我国最基本的一级政府系统,直接面对大量、繁琐的行政处理决定,设立执行机关,可以解决大量的行政执行问题;二是由于县级以上政府的公务员的素质水平相对较高,业务能力相对较强,可以最低限度地保障执行的合法性]另外,基于某些特别机关和少数部门以及特殊情况,可以有限制地授与个别行政部门以一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这样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强化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讲,“三权分立”就是基于对权力的制衡和协调。我国虽然不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实际上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分工和制衡,特别是的行政权,它是严格地受着同位的司法权和“上位” 的立法权监督的。但是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是第一道监督,也是比较经济,比较效率的监督。这种监督有其他监督不具备的优势,如业务的熟悉程度、程序简约等特点。当然,自力监督的效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因其监督者毕竟是局内人而非旁观者。但我们仍然可以充分利用其优势,用制度规则促其达到效率提高和最低正义的实现。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与行政行为决定机关的分离,正是行政执行权和行政命令权的分离,其效果相当于事前的司法审查,只是审查主体另换为了一个行政机关而已。
2、降低执行成本。与其在每个有行政命令权的行政机关下分设执行机关,不如设立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这样可以做到人、财、物力的节约;经验、手段、范围等资源的共享,最大程度节省成本花销,做到经济原则。
3、提高行政效率。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成立可以比较有效地杜绝以前由于机构设置不明带来的职权重叠或真空造成的相互扯皮或相互推委的现象,有效地提高执行效率。
4、执行协助的需要。“行政机关只能就本辖区内由自己掌管的事物作出具体决定,而且每个机关的执行手段都是特定的。这样原决定机关往往必须请求其他机关协助才能实现其管理目的”:“工商部门在执行处罚过程中如遇到抗拒,需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这类请求往往不易得到满足。”[26]因此,统一的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设立,可以弥补由于协助不能满足而致使行政义务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纸空文的尴尬。
关于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可以有以下具体设计:
1、实体上的设计。采用统一的考试,在各行政机关内选拔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有相当法律知识的公务人员组成。配置相当的执行手段,赋予相当的执行权力,给予相对丰厚的薪金和较高的地位,以防止其他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制订管理细则,明确其成员的权利以及违反规定所应承受的责任。
2、程序上的设计。(1)、申请。这是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启动的先决条件,非经申请,不得自力强制执行。(2)、审查。对申请执行书、理由、事实、法律依据以及其它相关文件材料审查,包括法律和事实的审查。规定审查时限,以短为好。较为复杂和影响重大的可以延长适当期限。(3)、告诫。以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名义向义务人提出告诫,发出告诫书,义务人仍不履行的,由其作出执行决定书。(4)、执行。由综合行政机关负责强制执行,执行完毕后将执行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机关。
(二)关于处理人民法院司法审查问题的设想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采用的人民法院事前审查的方式。这样的模式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笔者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论述。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需改为“以事后审查为原则,事前审查为例外”的模式。这样的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事前审查一是不仅延误了行政效率,二是即使法院的事前审查也不能完全保证其执行的合法,不符合经济原则。
2、事后审查可以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义务的有效实现,但是不利于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国家赔偿任务的加重。
3、采用事前、事后双重审查固然可以有效地兼容并蓄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但事实上成本过高,程序也太过复杂,周期冗长,也不符合经济原则。
笔者认为可以将法院司法审查的方式按下述步骤实现:首先,将法院的审查权和执行权剥离,法院只负责审查,而执行则完全回归行政机关。其次,由行政强制执行法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的原则,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不经法院司法审查即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对影响重大、复杂的,可能严重影响行政义务人人身、财产的执行案件可以在行政机关的申请下予以审查。再次,对法院审查的组织方式、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限予以明确规定。在行政机关申请后,由法院签发执行或不予执行令并作出书面说明,然后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这样可以较好地兼顾职权利保护、效率实现以及国家负担三种价值的统一,而且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控制的灵魂-司法审查也可以得以保留。
(三)关于围绕“告诫”为核心建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想
“没有事先通知其利益可能因政府决定而受到影响的人,一切其他程序权利都可能毫无价值。”[27]从本质上讲,告诫是一种通知行为,是指义务人不履行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行政机关在采用强制执行之前将强制执行的决定告知义务人的方式。它包括通知执行的措施、执行的时间和执行的地点等,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告诫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1、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在执行前对义务人进行再一次的说服,可以弱化因行政义务人情绪激动而产生的抵触,在行政义务作出后与执行前的一段时间内,让义务人较平静地思考其行为并予以劝说,可以较好地促使义务人自动自愿履行其义务,体现了“先说服,后强迫”的指导思想。
2、促使行政机关的反思。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在发给义务人执行通知的时候,同样须对作出执行的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多方面予以考虑,也是一种对执行行为的正当性认识的“反刍”。
由于我国目前的告诫只是界于“行政强制决定作出”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之间,并且只有一次告诫,因此笔者考虑可以作如下改进:一般的告诫程序可设计为在行政决定作出的同时作出简单的告诫,即用平缓劝诫的口气对不执行的后果作出说明;当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之时再作出正式的告诫,其应该包括执行内容、措施、地点和时间等,需以较为严厉的口气;最后对仍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强制执行(由于客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况例外)。对于标的重大或对义务人人身、财产等有重大影响或执行后难以恢复原状的,可以增加一次告诫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告诫以书面形式为原则,口头方式为例外。
(四)关于救济体系的设想
行政救济“通常是指行政行为给相对人权益造成侵害或负担的情况下,一定机关根据相对人的请求或依职权防止和排除这种侵害或负担,以保护、救济相对人的权益。”[28]行政法律“只有赋予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私人权益在法律上的请求权,并尊重它;赋予相互义务与权利,才有产生这一法律基础的根本基础”[29]救济是否能实现,是可否把强制执行权划归行政机关的重要衡量因素之一。如果说没有救济金手段或者救济手段有瑕疵,会使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控制成为一句虚言。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虑救济手段的时候应遵循以下思路:
1、行政机关在对相对人的行政义务作出时即需告知义务人的救济手段和途径,如申请复议或起诉;在告诫阶段,同样需要告知义务人的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执行完毕后,要告知义务人可以通过诉讼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上述三个阶段,都要明确告知权利时限,严格说明行政机关的执行方式、手段、执行权限和范围。一经违反,即应看作是违反行政程序,不能依法产生随后的行政行为或效果。
2、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可诉性。笔者认为,如果执行机关在执行中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些执行措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可以成为诉讼对象的;但是如果这些措施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只是为达到先行行政义务的手段,那么,它只是原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列为诉讼标的,只能对整个行政义务决定提出诉讼。这样做,有人可能会说其不利于权利的保护,但是笔者认为由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执行,并辅之以法院的事前审查己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上述行为的不可诉导致的利益损害,并且对未形成新行政法义务的执行的不可诉也可以通过向作出行政命令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提出复议或在执行措施不当造成损害后提出国家赔偿予以弥补或救济。
3、完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不可否认,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纵观其内容和现实的运行,仍可发现不少漏洞。基于本文内容所限,不予详细论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赔偿法,这部代表权利救济的最后法竟被民众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可见其对权利的保护有多么的不利!因此这三部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它们应该和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执行法一同构成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屏障。否则“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这一古老的法谚将成为一句空话。
“一个把自己仅仅限制于使别人服从的政府,会发现让人服从是非常困难的,……最完全的权威要能洞悉人的内心深处,不仅关心他们的行为,而且关心他们的意志。”[30]在本文写作完毕之时,笔者深深地感到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种“粗暴”的手段并不能使人真正从内心服从,“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它可以使他的表面行为从有害变为有益,虽然它不是达到那个目的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可是他不能提高他的思想,或者说只能使他由最卑鄙最无耻的动机驱使走上正道,它使他变成一个奴隶,全心全意为个人,受着自私的情感中的最卑鄙的畏惧心理的驱使。”[31]强制并非目的,扩大行政机关的执行权也不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漠视。笔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当前我国行政权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存在,但纵观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史,笔者认为对行政权的限制有偏激和“矫枉过正”的倾向。正是基于理性,笔者认为“三权分立”应该彻底,制约和平衡应该大致相当。我们的态度应是积极地控权,而非消极地限权;不是“司法主治”而是“法律主治”。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完善的立法和程序同样可以保护相对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当前“民告官”的民众意识的觉醒潮流和国家赔偿暂时的增多,也可以从反面促使更多相对人权利意识的复苏,使我们行政机关的素质和能力真正有提高和改善,真正地使“依法行政”不再成为一句美丽的口号!!
[1](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P.164.
[2] 应松年著《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3](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 张雁琛译。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P.154.
[4](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P.59.
[5] 关保英著《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P.282.
[6] 张庆福主编《行政执法中的问题及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P.59.
[7] Rascoe Pound “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 ” .57 Harvard Law. Review 1943.
转引自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P.239 .
[8] 马怀德著《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年第2期
[9] 马怀德著《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年第2期
[10] 杨建顺。关保英。戚建刚著《行政强制执行法的模式分析—2000青岛法学年会综述》。《法学家》。2000第6期。
[11]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P.227—229.
[12]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P.226—229.
[13] 刘瀚、张根大著《强制执行权研究》。转引自信春鹰、李材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P.431.
[14] 刘瀚、张根大著《强制执行权研究》。转引自信春鹰、李材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P.431.
[15] 刘瀚、张根大著《强制执行权研究》。转引自信春鹰、李材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P.431.
[16]汉密尔顿著《联邦党人文集》。 程逢如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P.391.
[17] 张尚鹫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P.245.
[18](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琛译。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P.156.
[19]傅士成著《行政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P.118—120.
[20]关保英著《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P.81.
[21](英)艾伦著《法律与秩序》1945年英文版。 转引自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P.219.
[22]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统计处。 转引自刘莘著《行政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年版 P.279
[23]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P.3.
[24]关保英著《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P.278.
[25]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87—288. 转引自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P.127.
[26]贾苑生、李江、马怀德著《行政强制执行概论》。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P.127.
[27](英)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著《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 黄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P.133.
[28]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P.188.
[29](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 米健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P.131.
[30](英)查尔斯•;范。莫特玛•;阿德勒著《西方思想宝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版 P.659.
[31](美)威廉•;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 第二、三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