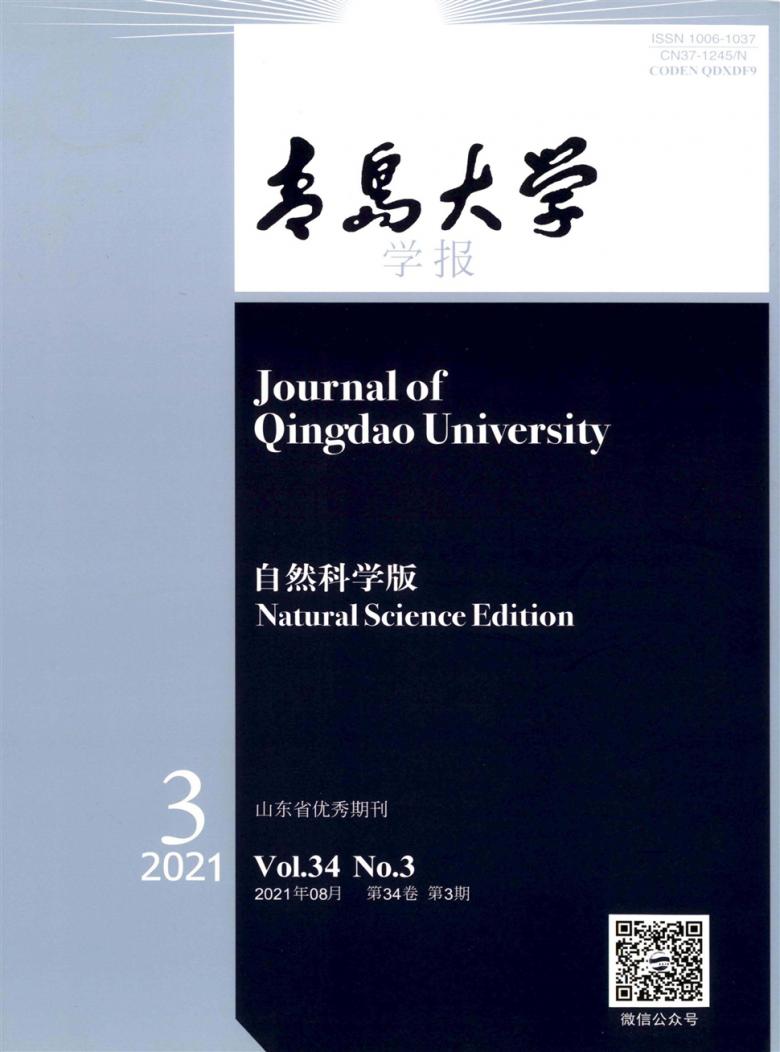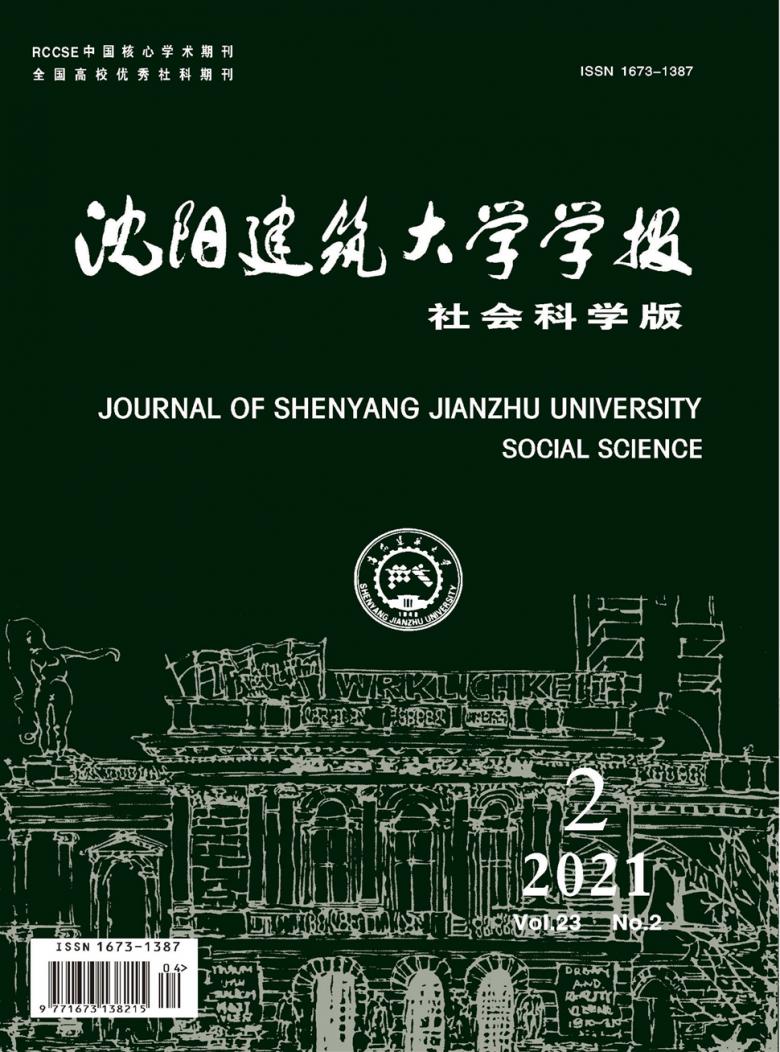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研究——以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
赵银翠
关键词:公民参与机制 行政民主 参与权 知情权 救济权
传统行政法理论是以国家与社会、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二元对抗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其关注的重心是对行政权力的消极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对公民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两极对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为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会对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三极甚至多极的行政法律关系,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研究从立法对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行政过程本身的关注,试图通过对行政过程的调控,形成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论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传统之下还是在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传统之下,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化、正当化的意义不断凸显,公民参与从对行政处分过程的参与扩展到对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评价、行政救济等行政过程的参与。本文以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典型事件——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通过分析该事件中公民参与缺失的问题,分析我国行政机关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应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1],确保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
一、在禁与不禁之间——电动自行车事件的简单回顾与反思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电动自行车上牌[2];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并粗暴执法,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并最终诉诸法院[3];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成为首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立法例。电动自行车在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等理由频遭封杀,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允许电动自行车依法登记后上路;哈尔滨、南宁则允许生产销售而不许上路;广州、长沙则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4]
这是一个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相互冲突与纠结的时代。在电动自行车禁与不禁之间,暴露出我国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其一,行政决策过程没有充分的公民参与,缺少民主性与正当性,主要表现为:复杂利益关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广大居民作为道路资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专业知识作为行政决策的技术支持缺少充分的论证,等等。其二,司法权软弱无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非常有限,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损害后缺乏获得法律救济的制度保证,从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后参与的积极性。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千千万万,我们没有看到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报道。其三,在我国现有的规则审查机制之下,对规范性文件具有审查权的机关不作为,导致了对制定规则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后全国仍有不少地方无视该法的规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规或行政决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再次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问题摆到我们面前。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以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如何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
二、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必要性
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基础建立的传统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机关的事前授权为前提、以司法机关的事后合法性审查为核心架构起来了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于确保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即运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规则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对私人利益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合法化”。[1]但这样一个制度模式仅适用于消极行政,即将行政行为限定在立法机关设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内,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定权限行事。在立法机关的授权日益广泛、行政职权不断扩张、公民对行政权的依赖与期盼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各国皆呈现出逐步扩大行政的裁量范围,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积极能动地作出政策判断之权能的倾向”[2],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功能被不断弱化。这当然并不是说传统的行政法的制约功能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在此基础之上,必须寻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以适应不断扩张的行政领域,更好地实现公共福祉。公民参与作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机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广泛采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诉求利益等方式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为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正当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
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的进程势不可挡,合法化、正当化的诉求日益强烈,行政机关自身也在为其行为的合法化、正当化而努力,以寻求民意的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各项行政管理活动。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为合法化、正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传统行政法意义上的对行政权力的消极制约功能有待完善,现有制度的运作不能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滥用,形式正义(合法化的诉求)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现代行政法意义上的对行政权力的积极引导功能尚未建立健全,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实质正义的机制也没有形成,实质正义(正当化的诉求)也难以实现。)在民主制度下,民主为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行政又为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电动自行车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制度性保障。
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在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之间,不仅涉及到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电动自行车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包括潜在的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到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竞业者的利益;不仅关系到交通发展战略,而且关系到广大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自由;不仅涉及到本行政区域内相关主体的利益,而且其影响扩展到其他行政区域;不仅涉及到电动自行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样也涉及到一般民众对该政策的认知及态度,因此行政机关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作出禁与不禁的行政决策时,除了要尊重法律的优先性之外,还必须通过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虑民意及相关因素,重新审视其拟定的行政目的及实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终决策,而不能简单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碍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为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多元主体参与行政决策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考虑相关利益,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形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将纠纷解决机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妥协与让步,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可能导致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行政机关难以决择;利益主体的参与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偏向某种利益,如组织化的利益;民主参与机制也必然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扩大与效率低下,等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行政机关可能会尽可能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程序或者采用私法方式达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机制的虚置。如在法律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时,行政机关可能会选择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提交意见等形式而避免采用正式的听证程序。即使在法律规定采用正式听证制度的领域,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行政机关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间选择决策方式。[5]尽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决策中的意义。在民主制度下,行政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三、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
一项行政公共决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赖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及信息输入,因此,有必要探讨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笔者根据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础不同,将公民参与分为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和基于专家知识的公民参与。
(一)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
基于主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基于其主观利益可能会受到行政决策影响而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其功能意义在于防御行政权的滥用,以防对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广大的消费者、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竞业者等主体的利益即属于主观利益,电动自行车的禁与不禁与他们的财产性利益息息相关。基于主观利益进行的公民参与,因参与主体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和组织化的利益主体参与。二者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差异悬殊以及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在参与动机与能力以及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方面明显的不同。
大量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主体由于高额的组织成本和搭便车效应,缺乏足够的动机参与决策程序。即使参与行政过程,也会因为在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方面的限制而显得“人微言轻”,因此,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利益往往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相对而言,组织化的利益由于其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利益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资源占有方面都有更强的优势,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进而影响行政决策,规制捕获理论也由此产生。
(二)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
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是指参与者以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成员而对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该种参与与参与者的主观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公民责任,基于对公共生活的关切而进行的参与。因为行政决策对一些主体而言,其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这些主体有足够的利益动机去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而对其他主体只产生间接而细微的影响,从利益的角度看,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参与行政决策。但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责任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公共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圆明园防渗工程由于公民参与而被扭转,孙志刚案由于公民参与而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以及在此次电动自行车事件中,许多学者纷纷质疑《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合法性,等等,这些事件都彰显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责任的重要性。
基于客观利益的公民参与,除了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之外,非政府组织在行政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开始不断凸显,并促进了行政民主化进程。在国外,NGO组织在行政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演进,NGO在我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并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如在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建设、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建设、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市动物园拆迁等事件中,由于NGO的积极参与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
基于专业知识的参与主要指的是专家参与。因为现代行政事务日益专业化、技术化,行政机关的决策必须经过对专业问题的科学论证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因此有赖于专家为其提供决策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如在电动自行车事件中,对涉及到的专业技术问题,如污染问题、安全技术标准问题、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城市交通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需要专家的广泛参与和论证。(专家参与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更为恰当,因为如果没有专家参与的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无法得到保证。)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而且会涉及更广泛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即使是同一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在专业方面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专家知识也并不能构成行政决策的惟一依据。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左右行政主体的最后决策。决策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最终出台,取决于信息的充足性、事务的专业性、利益的权重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判断及价值取舍等多重要素,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最终判断。通过公民参与,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获致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四、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体系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参与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权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权、知情权和救济权。
(一)参与权
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传统行政法中,公民参与是通过选举民意代表机关的代表来实现的。公民通过定期选举的形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由代议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约束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公民对行政机关的间接控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行政疆域不断拓展,立法机关通过大量的授权性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空间,民主的重心随之由通过立法实现的民主转向通过行政实现的民主,因此必须赋予公民广泛的参与权,包括行政决策过程的参与权、行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权以及行政政策评价的参与权,其权利形态可以表现为投票权、参与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表明意见权,等等。
(二)知情权
“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3]信息共享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权;其二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决策的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积极表达意见,献言立策,参与行政过程,否则不能有效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与公民的知情权相对应的则是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公共决策时,除法定保密事项之外,有义务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布行政决策的基本目标、手段、事实根据、政策的形成过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为此有必要建立经常性的、规范化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6]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形成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的互动机制,使公民能够更有效地参与行政管理活动,使行政机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决策信息。
(三)救济权
参与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资格,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而救济权则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证。参与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对该项权利的保障,应当在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保证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之所以要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其理由在于,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授权范围内作出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结果,当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济手段可以为行政机关自我改正错误提供机会,促使其反思行政决策过程,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4]
在此基础之上,必须确保司法的最终救济。为此,必须通过扩大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范围,以此来促成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策时,为相关主体提供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并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司法审查的最后手段来保证受到损害的利益能够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这样的利益不必一定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的“合法权益”[7],“任何一类利益主体,只要制定法(隐含地或明确地)要求行政官员在制定行政政策时必须予以考虑,就享有起诉资格。”“大范围存在的、未经组织的分散利益主体——诸如消费者或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可以获得司法审查,即便这些个别主体在行政政策中的实质利益相对而言是非常微弱的。”[5]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司法权力的界限问题。司法权的界入并不是要代替行政机关作出政策选择,而是通过司法审查,促使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适当地考虑相关主体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如何决策是行政机关政策判断的结果,司法机关无权界入。民主作为手段的意义及其限度也正在于此。
五、结语——我国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保障
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中并不缺少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该规定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提供了宪法依据。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如《价格法》(1998.5.1)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立法法》(2000.7.1)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行政立法过程,《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行政许可法》(2004.7.1)规定了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些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政策性规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精细的制度设计,包括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选制度、专家制度、对话、协商制度,公布结果并说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国现实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8]
在救济制度方面,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以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性权利保障为目的的,参与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保障有其困难性,尽管如此,却并非不存在法律救济的制度空间。对参与权的救济在我国也应遵循“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首先通过正式的行政复议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诉程序,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进行审视,由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自律性救济,并改进和完善其行政决策程序。在经由行政程序而救济不得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9]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以行政程序违法侵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主观诉讼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据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对行政决策过程进行审查,如果违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则应确定行政程序违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义上的制定法准据主义,通过法解释学,从宪政体系及行政法目的出发,综合衡量各种要素,对公民是否享有参与权作出实质法治主义的判断。这并不违背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相反,通过此类司法实践,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法治主义进程。(在现代社会,法院是“法治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形式”,其意义不限于“简单的权力划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参与形成和执行国家决定的——各方力量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与均衡”[6],共同促进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
[1] 见2004年《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 2002年8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的形式,决定“对目前本市范围内已有的电动自行车(本通告发布之前所购买的)实行核发临时号牌和行驶证管理。”“自2006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电动自行车在本市道路中行驶。”(2005年1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又发布《北京市关于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的公告》,决定“自2006年1月4日起,为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办理车辆登记。”)
[3] 参见中国能源网:“电动自行车冲突要求变革公共决策机制”,http://www.china5e.com/news/jichu/200505/200505310401.html;中国网:“电动自行车:一个政府不喜欢的产业”,http://www.china.org.cn/chinese/news/925807.htm.
[4] 参见中国网:“一路尴尬,电动自行车驶向何处”,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Aug/940579.htm
[5] 如我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计价格[2001]2086号)明确列举了国家计委举行价格听证的目录。由法律的概括性规定到行政机关的明确列举,行政机关在执行《价格法》规定的听证制度时,对价格目录之外的公益产品的定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之下,成功地避开了正式听证程序。
[6]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信息公开制度,如福建、广州、上海、深圳等地都出台了相应的信息公开制度,国务院也于2002年启动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工作。由此,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
[7] 《行政诉讼法》第2条。
[8] 相关分析可参见王万华:“中国行政决策听证的现状及问题”,《法制日报》2003年12月18日第九版。
[9]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并不是要否认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序选择权。
--------------------------------------------------------------------------------
[1] [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
[2] 杨建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辩析——《宪法修正案》与行政法政策学的方法论[A].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论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44-460.
[3] 同上。
[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651-652.
[5] [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3-84.
[6]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M].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