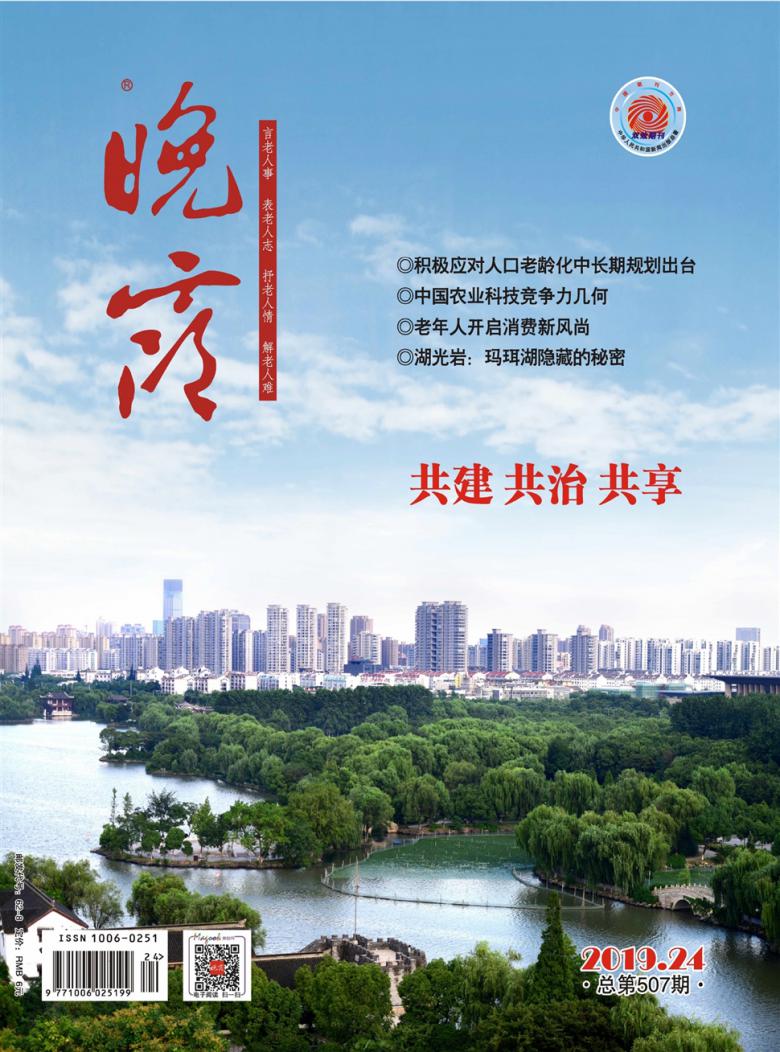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
佚名 2003-09-18
一、为什么古希腊? 为什么雅典?
说起西方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历史和传统,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雅典,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怀疑,一个独特的西方文明正是从那里孕育和繁荣。古希腊人对权力和正义的理解,对民主制度的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系统的理论批判,以及对阶级冲突和公共利益等问题的辩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深刻地启迪着人类。这一切无不让我们惊叹,令我们着迷,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古希腊之所以独特、之所以神奇在于它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专制体制。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史基本上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尔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1] 和当时邻近的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比起来,古希腊的确是奇特的。
古希腊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学者都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理论(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就不在此讨论了。总之,历史的事实是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发展出一个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和垄断公共事务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够容忍一个强权的君主政体,只有极少数城邦维持了比较稳定的贵族制,绝大多数城邦都是采取某种程度的共和制,在这些城邦里面,占大多数的非有闲阶层在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都显得及其重要。
正是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社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古希腊的政治精英们充分认识到他们这种无法垄断公共事务的状况是反常的,因此极力想达到垄断公共事务的目的,而那些非精英阶层又尽一切可能阻止它的发生。这样一来,那些少数的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操纵政治事务的权利就不得不与大多数为了维护他们公民权利的非精英阶层进行不休止的谈判和辩论,当然其间也偶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构成了当时城邦主要的政治生活。其发展的结果是有的城邦极其动荡,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而且经常十分剧烈,而另一些城邦却保持了高度的社会和政治稳定,雅典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中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一方面,它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捍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而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现代的民主制度是通过一种不可剥夺的宪法或法律权利的理念来捍卫公民的“消极自由”,而古代的雅典则是通过赋予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从而使公民更多地获取并维护他们的“消极自由”。为了捍卫珍贵的自由,公民通过政治方式来对抗那些随时企图夺取他们自由的少数政治精英,因此,在雅典,“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不可分离并相互依托的。可以这样说,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为争取多数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从而打破了极少数统治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操纵政府权力的神秘。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也展露出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那就是自由的公民所追求的是要避免成为那些只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的奴隶,然而,他们本身却又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规范别人。
正如前面讲到,雅典的民主理念所展示的是公民对于平等、正义和自由的追求。诚然,这些价值观无一不是美好的,无一不是我们所渴求的,但它们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追寻的一切吗?雅典的民主实践带给了社会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吗?雅典的贵族精英们当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根本上讲,他们是反民主的,他们想要证明为什么将政治平等和自由赋予大多数人是错误的,为什么其它一些非民主的价值观对人类社会更为重要,更值得人类去追求。这种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初期的美国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后来随着自由主义的繁荣和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它极权思想的出现,人们对于极权的恐惧感越来越深,对极权政治也越来越忧虑,从而开始更多地倾向于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丝毫不能否认这些反民主精英们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精彩的文字所揭示的正是人类所渴望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局限,他们的思想为完善和发展一个自由正义的,并能保持社会长久稳定的政治制度补充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养分。另外,与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批判不同,雅典的精英们继承了一种尊重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文化,他们深信民主自由的理念是错误的,但要纠正这个错误,就必须坚守自由表达和自由言论这个前提。这种宽容的精神,在批判中互相汲取的竞争精神,都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借鉴的。
为了帮助我们更全面更仔细地了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弄清楚公元前五世纪前后雅典和整个古希腊的宏观历史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紧接下来,就让我们围绕发生在古希腊爱琴海沿岸,雅典曾经全面参与了的两场著名战争 --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简洁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吧。
二、雅典的兴盛和衰亡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2]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3]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4]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5]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6]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
三、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
雅典的民主思想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它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有区别的。今天的民主指的是少数人不能专制大多数人,它反君主制,反专制,反贵族制,而且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受到绝对保护,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漠不关心也是正常的。因此,今天的民主更多地是从消极意义上讲的,而雅典的民主则强调积极地参与。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知道,雅典的民主起源于梭伦变法和克利斯提尼改革,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马其顿统一希腊诸城邦,雅典沦为马其顿的附庸国。在此期间,寡头们仅有两次非常短暂的复辟,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在雅典(至少是成年男性公民中)是很流行的。但有趣的是,除了古希腊戏剧等一些文学作品之外,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对雅典民主和民主制度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很多时候,人们对希腊民主思想的搜寻大多来源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例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录了锡拉丘慈民主党领袖Athenagoras讲的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民主即不慎重又不公平,那些有财产的人才应该是统治者。但我首先要说的是,民主是全体人民的,寡头制仅仅是为了一少部分人;其次,有钱人最会理财,聪明人能提出最好的建议,而大多数人则是最好的审判官。民主制度就是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最大的平等。”[7]
雅典即不存在正式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精英们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这样说过:“几乎可以这样讲,政治理论的发明就是为了去展示那种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必定演变成一种暴民的统治。”
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对支持民主的人来说,政府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不管一个人是穷是富,也不管他出身卑贱或高贵。但对于民主的敌人而言,民主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虽然富人更有能力制定国家政策。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家们认为,这种民主的暴政并非是一种偶合,它是民主制度下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的必然结果。有一篇匿名的评论雅典政治制度的文章这样写到:
“在每一个国家,贵族和民主总是相对立的。贵族最有控制能力,最为公正,因而是最道德的,而人民总是无知、卑鄙和没有秩序的,贫穷和缺乏教育导致了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平。”[8]
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理斯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误政策。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引向灾难。虽然修昔底德不一定反对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是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失望和惊恐。
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和埃索克里特斯(Isocrat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民主已经完全背离了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真正的民主。埃索克里特斯认为雅典早期的民主珍视“部分平等”(the principle of propotional equality) 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以他们各自的能力为标准来分配权力,遗憾的是,后期的雅典完全放弃了这一原则,使得穷人也拥有了同样多的政治权利。虽然这种理论在论证方式上不同于早期的反民主思想,但他们却都认为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公民道德水平的高低,穷人参与政治只能导致政府的腐败。
自从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希腊诸城邦丧失自治权力以后,对于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攻击日渐增长,这其中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谴责和批判最为系统也最为深刻。
这种哲学批判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文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寻觅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将它归纳为反对民主或是赞同民主,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找寻到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很多置疑和批判。
在“Crito”里面,苏格拉底力图说服Crito他逃离监狱的决定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因为民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在另一本对话集“Gorgias”里面,诡辩家Gorgias想证明修辞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苏格拉底却反击说修辞只会对无知的人产生作用,有可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贤人,修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格拉底接着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别人轻易说服的无知的人手中,而并非是由贤人掌握的。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反民主的柏拉图一样都认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对善恶优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柏拉图对雅典和民主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后期的两本对话录---<<理想国>>和<<法律>>---里面。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问什么是正义,但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里,他用人作比喻,并解释说如果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和谐统一,那人就是正义的,接着他又将这个比喻推广到国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谐统一,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他继续论述说这种和谐统一只能建立在各个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它们各自的功能各行其事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坚信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也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是永恒不变的。
基于对正义的这种理解,柏拉图理所当然地推倒出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哲学王,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由监护者(Guardians)、辅助军(Auxiliaries)和其他所有被统治者三部分所组成。监护者和辅助军共同组成统治者阶层,被统治者指的是农民和其他一切社会劳动者。监护者只能出生于统治者阶层内部,并从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而他们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应当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出最明智的,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决定。辅助军掌握军队、警察并执行监护者的行政命令。柏拉图说这三个阶层是在土中分别搀入了金、银和铜铁三种物质而造成的:
“在这个社会里,你们都是兄弟。但当上帝创造你们的时候,他在那些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人中加入了金;在有资格成为辅助军的人中加入了银;而在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中加入了铜铁。”[9]
这三个阶层如果各施其职,统治者统治国家,辅助军守卫国防,农民种田,鞋匠做鞋,各部分达成和谐的统一,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就是最完美的了。
接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后半部分集中描述了四种不完美的社会,包括Timarchy, 寡头制(Oligarchy) ,民主制(Democracy) 和僭主制(Tyranny) 。他指出如果一个次完美的社会执政出现错误,那这个社会就会先演变成为Timarchy,再变成民主制,最后变成僭主制,这个演变过程通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在此,柏拉图耗费大量笔墨对民主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认为寡头制用财富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势必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战争,当穷人取得胜利之后,柏拉图说:
“穷人处死或流放他们的反对派,将同等的社会权利赋予其他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从而开始实行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10]
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再尊重权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没有人再顾及别人的安危,任何人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做出重要的决定,这样一来,所有以前的规范都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民主的特征。这样的社会里五花八门,不管人和人有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得到同等对待,社会显然处于无政府状态。”[11] 这种极端的自由一定造成党派斗争,并最终产生极权暴政 。“正如我刚才讲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过度的自由最后一定导致民主的崩溃。”[12]
《法律》是柏拉图所有对话录中最长的一篇,全文基本上都是在描述如何建立一种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政治制度,其中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对于雅典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讨论那个崭新的城市(Magnesia)是否应该建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的时候,柏拉图认为港口国家很容易带来奢华和腐败,很显然这是在影射雅典。 文中的那位雅典陌生人是这样说的:
“如果城市建在靠近海的地方,我们会有好的港口,但也就不可能种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作物。为了抵御港口城市受到各种复杂、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上天赐予的救星。一个靠海的国家看起来会很好,但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人民的心灵将会受到外界的腐蚀,公民们不仅对自己的国人不再信任,而且对别人也充满了敌意。”[13]
又比如说柏拉图认为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国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当然又是在暗指雅典。他认为海军(不包括舵手、桨手和船长)都胆小如鼠,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撤退到船上并逃走。然而,这些人在国内却享有极高的荣誉,那些本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比如陆军)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当合理的尊重和爱,那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长久了。
亚里斯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柏拉图一样都鄙视从事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的劳动者,他认为农民是更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从事政治生活一向冷淡,很少参加公民大会,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名著 <<政治学>>中这样写到:
“农民是最好的公民--因为没有太多的财产,所以他们总是忙于生产,极少参加公民大会。同样也由于他们缺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得不整天在田间劳作,他们也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他们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只要从参与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统治国家没什么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想赚钱而不是为了名和誉。”[14]
他认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国家要远远优于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家。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坚信幸福和智慧只能从思考中获得,而思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乍听起来,这两种看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前一种想法只是他迫于现实的妥协。他深知在雅典现存的民主制度里面,与其任由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城市居民思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不如寄希望他们和农民一样远离政治事务,只去关心他们各自的生计。国家只需要由少数聪明的贤人来管理就是最理想的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是最佳的政治制度。他将希腊当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民主制走向极端就和僭主制没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共同缺点是它们不可能产生出合格的人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参与政治,但显然缺乏政治智慧,而在寡头制下,执政者虽然有钱,但又缺乏高尚的道德。由此,亚里斯多德建议一种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在这种制度下,一少部分贤人从事军事、政治和宗教事业,而其它人则去种田和进行别的生产性活动,理想的状态是这些人有公民投票权,但并不担当任何国家公职。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主张所谓的“部分平等”,两人拥有非常相似的正义观,认为个人的幸福只可能建立在正义的国家基础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以人天生的不平等为基石的。他们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来在智力、道德上是那么的不平等,却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生在民主制盛行的古希腊时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他们原创的思想和大量流传至今的作品做出了一个对后世具有无法估量的启迪意义的回答:雅典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自然的金字塔结构,因此它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并扭曲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的稳定和秩序。
另外,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它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幻想,而不是冷静的法律和人的智慧。雅典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狂热使得他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进而做出草率的、不合理的政治决策。处决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前面已经提到,从罗马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等极权思想的出现,源于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革命时期的美国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法国人所追求的恐怕更多地倾向于斯巴达和罗马,而不是雅典;美国的创建者们也同样将雅典当作一个反面的例子,麦迪逊(James Madison) 和亚当斯(John Adams) 都曾报怨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民主的优越之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无论民主与反民主的思想如何嬗变,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古希腊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是美国Providian Financial Corp 的风险分析师。)
注 释: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66.
[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106.
[3] Brummett, Palmira et al., Civilization Past & Pres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64.
[4] 同上, p.65.
[5] 同上, p.66.
[6]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Group, 1972, p.49.
[7] 同上, p.435-436.
[8] 转引自Roberts, Jennifer T., Athens on T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8.
[9] Plato,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The Republic, Penguin Group, 1987, p.123.
[10] 同上, p.313-314.
[11] 同上, p.315.
[12] 同上, p.321.
[13] Plato, translated by Trevor J. Saunders, The Laws, Penguin Group, 1975, p.159.
[14]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T. A. Sinclair, The Politics, Penguin Group, 1992, 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