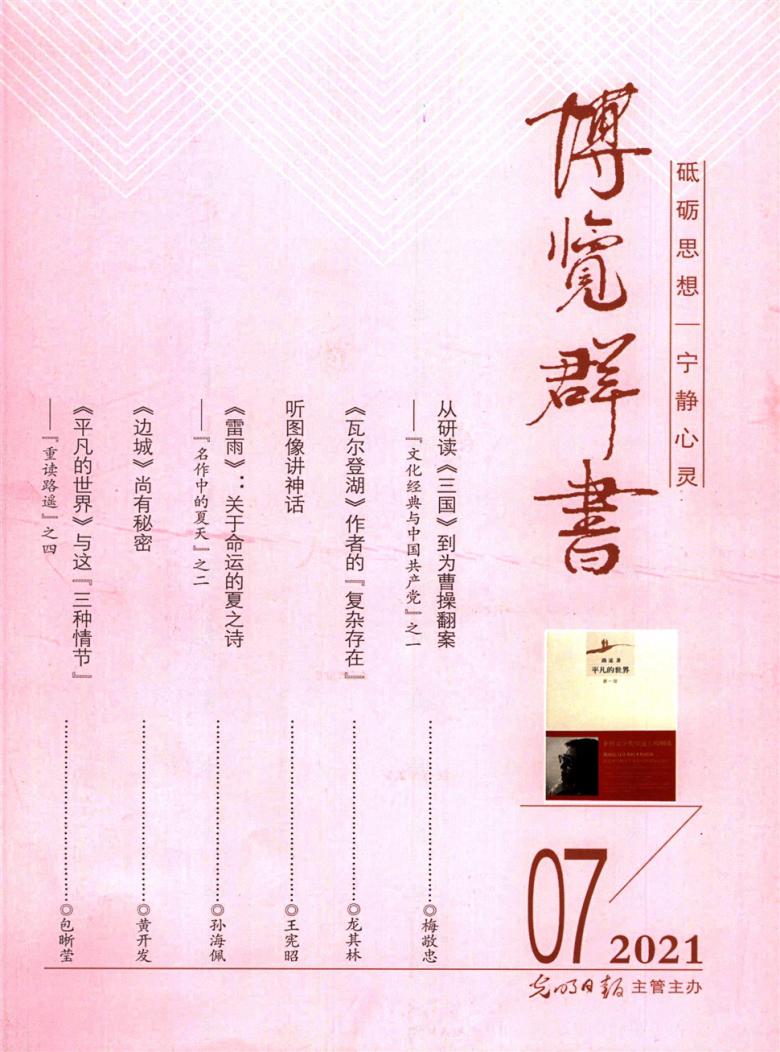列宁美学与毛泽东美学的“血亲”关系
佚名 2013-01-14
一、列宁是转折点,也是新起点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说:中国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美学(文艺思想)的祖师爷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艺思想)为指导,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继承和发展,云云。今天回过头来看,笼统说,这话当然也对;但是细究起来,又觉得不准确或不太准确。毛泽东当然也像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再三声称自己学马克思,但就文艺思想而言,其基本精神和关键之点却是学列宁。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列宁的学生,是列宁(经瞿秋白)的再传弟子,得列宁之真传。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
这里要先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作些比较。列宁当然也说自己和俄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但是就美学(文艺思想)而言,马恩和列宁却并不相同,仔细考察,二者差别还不小。 (一)先看马克思恩格斯 马恩的美学(文艺思想)对中国当代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著上个世纪头几十年即已陆续翻译过来,今天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美学(文艺思想)的篇章历历可查,还有单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或《马恩列斯论文艺》),且不止一种。 马恩的美学思想很丰富,很精彩。其最突出的是讲什么呢?它们所强调的理论关节点在哪里呢?我个人体会,其核心在现实主义,即真实地描写现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中国人背得最熟且引用次数最多的是马恩在几封通信中的几段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原有重点号)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原有重点号)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 “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清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1885)还有,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信中提倡“莎士比亚化”(原有重点号)而反对“席勒式地(原有重点号)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中评论以狄更斯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小说作家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恩在继承西方传统美学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加以改造和强化,对人类美学思想作出了伟大贡献,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值得全人类珍视。 (二)再说列宁 列宁有关美学(文艺思想)的论著中国读者同样不陌生,它们也是在上个世纪头几十年陆续介绍过来,而且比马恩美学力度更大、影响更深远。今天更有《列宁全集》,有《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种版本)以及《马恩列斯论文艺》中有关列宁的篇章,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 从马恩到列宁,随着历史的发展、形势的变化,美学(文艺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宁强调的重点不再是马恩当年强调的现实主义、写真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党的文学的原则”,即文学事业要成为党所开动的革命机器(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丝钉”。这是列宁美学(文艺思想)对马恩美学(文艺思想)的巨大改变,也是列宁与马恩的巨大差别。对于列宁的美学(文艺思想)论著,中国读者最熟悉、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1905年发表的集中阐述文学党性原则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近年来改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其实没有必要,内容实质没有什么改变),以及随后十来年间(1910年前后数年)有关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和给高尔基的信。它们也的确是列宁美学(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其中《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尤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圣经。在这篇文章里,列宁高喊:“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几个字原有重点号)。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列宁为了堵住某些人的嘴,也说到文学“自由”的问题,说到两个“无可争辩”:“无可争辩,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辩,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但是,列宁紧接着就强调:“可是这一切只是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列宁在上面所引最后一句话里一连用了几个意思相近、步步加重的副词“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连用几个“最最最……”一样,可见他强调的力度和急切的心情。他是在引起读者的加倍注意:你的“自由”必须服从“党性”。打个比方:“自由”是天上的“云”,“党性”是整个的“天”,文学再“自由”也跑不出“天”去;或者,“自由”是孙悟空自如翻滚的斤斗,他再“自由”翻滚,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总之,文学的党性比天大。这里的党的文学的“自由”就如闻一多当年所说的作格律诗:带着镣铐跳舞。
上面提到的列宁的其他书信和文章,实际上也是从党性原则出发说事儿。譬如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基本说的是托尔斯泰与“革命”的关系和对“革命”的作用、意义,虽然列宁也说托尔斯泰是“镜子”,但他说的却不是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问题,不是现实主义问题。与高尔基的通信,也是强调:“把文学批评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这几个字原有重点号)联系起来”。总之,它们都几乎无时无刻无字无句不在阐明文学的党性原则;相对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现实主义、真实性等等,在列宁那里几乎不占什么位置。 这在世界共产党人的美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变化。列宁是转折点,也是新的起点。列宁创建了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或革命共产党人的一种新的美学:以文学的党性原则为标志、为旗帜的列宁美学(文艺思想)。它是一种突出政治的美学(文艺思想),或者可以叫做一种新的“政治”美学(文艺思想)。“政治”美学(文艺思想)可以有多种,譬如有“学术政治”美学(文艺思想),即着重从学术上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还有一种叫做“地缘政治”美学(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2年出版了一部书,名字就叫《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和空间》)。列宁不是。他是从革命实践的角度规定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即文艺必须绝对被革命政治所笼罩。而这种革命政治在列宁那里很明确只是革命政党(共产党,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他所讲和所要解决的是文艺与革命的政党政治的关系。所以我把列宁美学(文艺思想)命名为“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 二、列宁政党政治美学的嫡传子弟兵 在20世纪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形势下,列宁开创的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有数支嫡传子弟兵。我没有作过精确调查,据粗略观察,以下三支比较明显。 一支在列宁的祖国苏俄——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列宁在世和去世之后,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人在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上也出现过许多派别(如果以列宁为“中”,那么还有对于列宁来说是“极左”的或“右”的,还有学院派的,还有庸俗社会学的等等),有过各种争论和斗争。但其主流美学(文艺思想)在相当长时间里奉行的主要是列宁美学(文艺思想)路线。后来(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掌权时期)发展到极致,就是以日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极左政治美学(文艺思想)。这里要说一句:列宁自己也不一定预料到后来的极端状态,而且也不一定同意后来极左政治家们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日丹诺夫等人的所作所为也不能由列宁完全负责;但是,不论日丹诺夫等人如何走极端,最初毕竟是沿着列宁美学路线一步步推进的。一九四六年八月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影片(《灿烂的生活》)及剧场上演节目连续作了三个决议,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等,就是将列宁美学发展到极致、发展到极端乃至畸形时的代表作。 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对创作倾向和艺术流派进行政治宣判,称左琴科是“市侩和下流家伙”(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社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则干脆谩骂说,左琴科是“凶狠的下流胚和流氓”),称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无思想的反动文学泥坑”和“贵族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是古老文化世界的“残渣”,而且更进一步,说她“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一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日丹诺夫还把艺术上的象征派说成是“反动的文学派别”,并归罪于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霍夫曼,认为苏联的“不论阿克梅派也好,谢拉皮翁兄弟也好,他们的祖先是霍夫曼,贵族沙龙颓废主义和神秘主义底创始者之一”,以致对整个西欧文艺进行全盘否定。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要求“文学领导同志和作家同志都以苏维埃制度赖以生存的东西为指针,即以政策为指标”,“把思想战线拉上与我们工作底其他一切部分并列在一起”。① 日丹诺夫的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是在俄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的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手握生杀大权,并且常常付诸行动,因此十分可怕。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十分敬重日丹诺夫,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郑重出版了《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扉页上印了他的标准像,《出版说明》称“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著名理论家和天才的宣传家、国际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书中收进了上面这篇报告及其他讲演,编者说:“它们对于苏联文学艺术和哲学研究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起了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
认为它“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永垂不朽值得学习”;有人认为《武训传》“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武训不足为训”。即使对武训其人其事学术上有不同看法,对电影《武训传》艺术上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用艺术竞争、学术讨论来解决,但却动用行政权力大开杀戒。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毛泽东审阅并加写和改写了主要几大段文字——后来此文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收入《毛选》五卷。毛泽东一针见血:“《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毛泽东给武训和《武训传》定性:“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丑恶行为)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还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为了证明批判《武训传》的正确,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一手炮制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洋洋45000多言在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整版整版地连载,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是建国后权力政治美学的第一次大行动。而且对《武训传》的这些判断和结论都变成实际行动了,采取行政措施了:电影被勒令停演,编剧、导演、演员同电影作品一起遭到全国性各种形式的批判,以至几十年后文革中被残酷批斗抄家。
这是建国后毛泽东权力政治美学的第一次大行动。用行政命令、甚至用专政手段解决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其实是连某些古代帝王(譬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都不如的。萧衍佞佛,把佛教定为国教,四次出家为僧;而范缜则撰《神灭论》与佞佛势力展开激烈对抗。按帝王专制时代的一般做法,贵为皇帝的萧衍完全可以用握在手里的生杀大权轻而易举地除掉范缜和他的神灭论学说;但梁武帝没有。他虽然也下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敕旨,并发动王公朝贵、高僧“大儒”(曹思文就以儒家礼制证明神之不灭,说范缜“欺天罔帝”、“伤化败俗”)对范缜进行精神“围剿”,却基本上“君子动口不动手”,大致限定在公开平等的学术辩论范围。范缜始终坚持己见,毫不退让,据理反驳;而武帝也未采取行政措施和专制手段加害于他,不但仍让范缜当他的官——位居国子博士,其著作《神灭论》也未被取缔,反而作了更精辟的修订,一直传播至今。 权力政治美学采取专制手段造成更可怕后果的是胡风反革命事件,一下子让胡风在监牢里蹲了几十年。今天看来,胡风的文艺活动、文章、书信,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益无害。即使他的“万言书”(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的一份陈述关于文艺问题意见的30万言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完全符合宪法。今天看来,某些共产党人与胡风的争论,只是不同思想见解和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可是不幸,胡风遇上了权力政治美学,以权力政治解决美学问题,解决文艺创作问题、文艺思想问题、学术观点问题,酿成悲剧。此事因尽人皆知,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