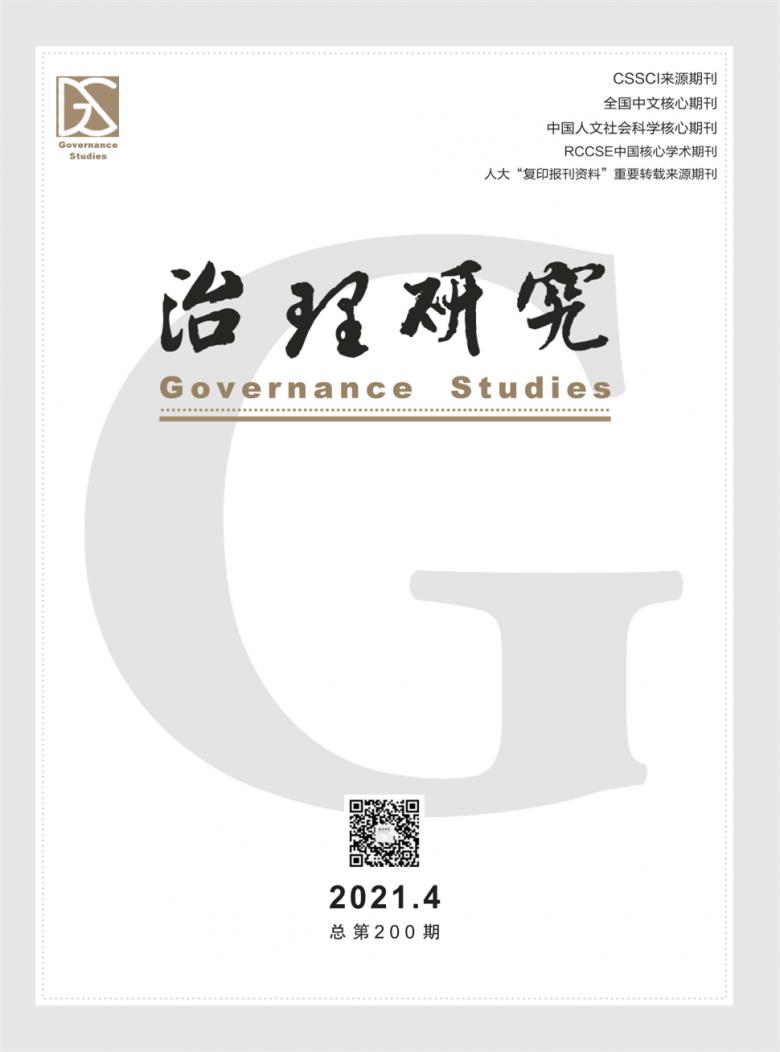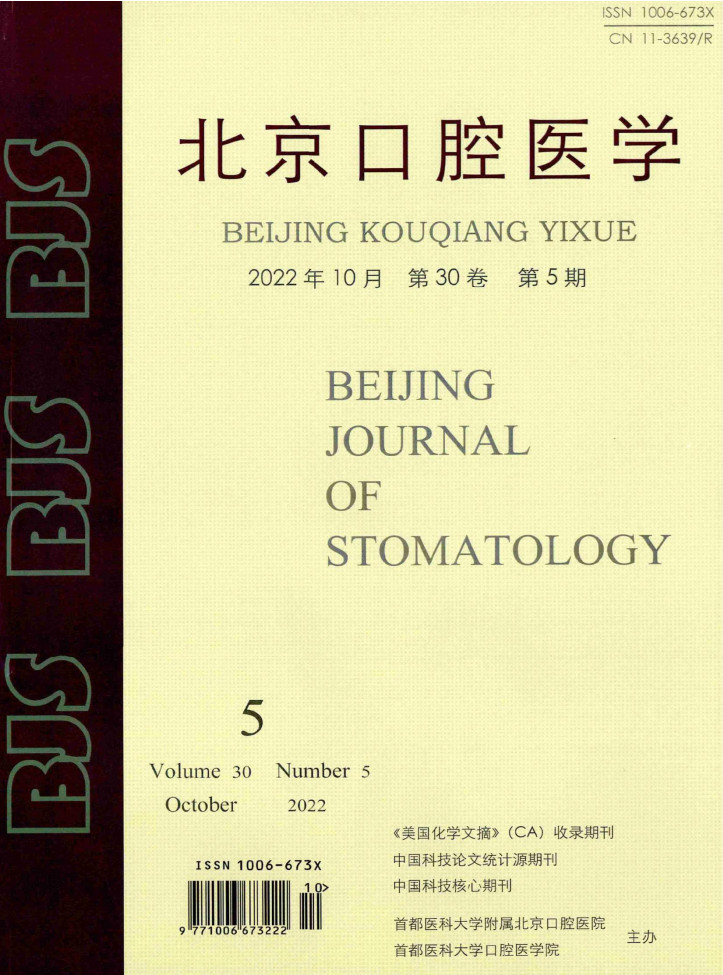浅谈对司法实践中现行诉讼调解制的度审视
项磊 2013-04-21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社会分工愈加严密,社会关系愈加复杂。为了更加高效地定案止争、化解社会矛盾,“能动司法”应时而生。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大调解”的格局逐步形成。随着法院调解制度的复兴,学界对此也发表了诸多见解。事实上,法院调解制度并不符合宪法中对于法院职能的定位,如果过度拔高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甚至将调解结案率作为业绩考核的指标,从而违背当事人意愿而进行调解,无疑不符合相关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长远来看,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相当大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在讨论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基础同时,进行了有关法院附设型人民调解的论述,希望达到法院审判工作和调解工作的分离,回归其宪法框架下的定位。
论文关键词 诉讼调解 宪法 调解优先 法院附设型人民调解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着深厚的调解文化。历史上,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官方或非官方的争议解决途径,一直在我国化解社会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便充分结合地方实际,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的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其中注重调解便是这种审判方式的一大特色。建国以来,调解制度也曾经长期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得到过广泛的运用。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作重心的转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被摆到事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法律的正当性和程序性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重视。因此,90年代以来,我国调解制度逐渐式微,审判结案率上升。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案件由于简单下判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乃至无休无止的上访等问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并影响了法院定纷止争能力的发挥。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要尽量通过诉讼调解达到平息纠纷的目的,要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愿调、不会调的问题。豍2009年3月,随着《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出台,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被正式提出,诉讼调解制度走向复兴。在讨论之中,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具体实务工作有着其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违背相关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精神实质的做法的大量出现、调解运用方式和范围的不合理,从而影响了诉讼调解制度的预期设计效果并在学界和实务界产生了重大的争议。故而,我们有必要对这项制度所涉及的学理及实效进行两方面的审视与思考。
一、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现实背景
法律是一种通过对法律主体设置权利义务规范来调整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的社会规范。它主要的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是诉讼。但作为社会规范,法律并不是唯一的一种,除了法律之外,社会规范还有风俗习惯、道德约束、宗教习俗等多种形式。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民间有着深厚的耻讼文化。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豎孔子在春秋时期所提出的诉讼观在国民心态之中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性。且在农村中,这种现象更加有甚。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豏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写道。正是受这种排斥诉讼的文化传统影响,我国的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性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长期受到推崇。 西方的诉讼调解发源较晚。随着“诉讼爆炸”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接近正义运动走向第三波,以英美为首在全世界刮起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旋风豐,以弥补诉讼的不足。在ADR运动中,调解犹如沉睡已久的巨人,从ADR的各种形式中脱颖而出,调解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调解被许多国家视为解决纠纷的优先机制。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大量新型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伴随着这些社会经济和结构的剧烈变革,原有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定纷止争”的能力受到严重考验,出现案结而事不了的情况。在这种新形势下,一度受到冷落的诉讼调解制度重新强势回归。 随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多个关于调解的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人民法院调解工作作出了规定。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调解在法院审判中不断得到强化。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倡导大调解运动中还进一步确认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但是,2009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2009年7月28日至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正式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并定下将来法院调解工作的基调——强化调解,在2010年最终发展成“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并形成文件。豒自此,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调解格局正式形成。
二、“大调解”背景下的学理争议和实效分析
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伴随着学界与之的众多争议。实际上,国内外围绕诉讼调解制度的法理、实效、程序性和正当性等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众多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其中更不乏对诉讼调解的猛烈抨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斯(OwenM.Fiss)就曾尖锐地批评调解是对法治、审判的冲击,是二流的正义。豓我国有学者认为,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很可能缺乏社会结构基础的支撑,忽略了社会的法治化取向,是一个不符合社会结构现状且逆社会转型方向的国家政策,这样的政策会导致权利得不到法律维护,社会公众对国家愈加不满,引起社会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豔 1.诉讼调解和法院定位的问题。作为积极探索法治道路的国家,司法体制是宪法体制的一部分,司法改革无疑不能脱离宪法框架而独立运行。在我国《宪法》第123条和126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这些原则性的内容对法院的宪法定位、工作职能、工作方式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得认识到,依据宪法,法院是专职审判的机构,在它运行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仅仅依靠法律。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必须是明确的,人们可以从既有的法律规范中预测判决的结果。法律的预测作用可以使人们在法律的范围内,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防止不可预见的后果的出现。豖正如英国著名法官布莱克斯通所宣称的那样,法院是“法律的保管者”,“活着的圣谕”,法律也被定义为“法院将要作出的判决的预言”。正是因此,将调解职能加给法院并不符合宪法中对于法院这一审判机构的定位,调解的灵活、能动性也影响了法律结果的确定性。长远来看,更是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法院这一社会纠纷解决机构的正确定位,这对于构建人人崇尚法律的现代法治社会无疑有其消极的作用。美国学者戈尔丁指出“显然,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尽管我们期望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
2.调解范围的过度扩大与人为设定指标的负面性。近年来,不仅民事领域的诉讼调解得到了广泛的复兴,这种调解的风向还吹向了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领域。自最高人民法院将“刑事和解”确立为改革措施之后,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力度大为加强,并先后出台多个规范性文件。例如,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首创的刑事和解“检调对接”机制,该模式在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得到推行。该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我国刑事司法的刚性制度被柔化。豘在行政诉讼中,甚至出现了“变相调解”、“行政和解”,其表现为说服或压服原告一方,使其对行政机关的控诉不至于过分严重,其采用的方法是“劝撤”———说服原告撤诉。豙我国调解原则一贯强调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而上述调节范围过度扩大的情况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强势一方压迫弱势一方进行调解,并作出其所不愿的“让步”的可能性,显然对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平等”大大增加了难度。再加上一些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暗箱”操作,不仅不利于案结事了,还带来了日后不断上访的可能,从而造成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足,严重影响了法律作为纠纷最终解决方式的公信力。 随着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一些地方司法机构错误的理解相关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人为确定调解结案率,并将法官的业绩考核、评优评先、年终奖惩与其直接挂钩,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各地调解结案率的飙升。据《法制日报》报道,截至2006年8月底,河北省保定市两级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达到61.8%,同比提高21.4%;易县、定州、容城等基层法院的调解率超过70%。而易县西陵法庭庭长樊德生个人所办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达到了98%。据《铜川日报》报道,截至2007年11月22日,铜川市各级法院民事调解率达到了64.19%,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77.73%。据《驻马店日报》报道,新蔡县人民法院佛阁寺法庭2008年上半年共收案67件,结案50件,均为调解结案,调解率100%。据《人民法院报》报道,宣威法院在2009年受理案件86件,调解结案82件,调解结案率高达95.3%。据《人民法院报》报道,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在2010年1至3月份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53件,调解结案47件,调解率达88.7%。豛于是在这大调解的格局下,各地各级司法机关纷纷比拼调解率,似乎调解结案率越高,业绩就越突出。有学者不无犀利地指出,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人为地事先确定调解结案率,乃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突出表现。通过院长、副院长们“踱方步”、“拍脑袋”事先确定下来的调解结案率,尤其是在各个法院之间经过相互“攀比”并“层层加码”后确定下来的调解结案率,除直接导致了民事审判工作中主观唯心主义的大膨胀、大爆发、大流行之负面影响外,根本就无丝毫的可取之处!豜 据此我们可以预见,这种情况下,法官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以及自身业绩考核与奖惩的考虑,对诉讼调解产生了极大的偏爱。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基层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法官面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当事人时,有意无意地使用各种手段诱导、强迫当事人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部分应得利益而同意调解。法官自身则既为调解者,又为审判者,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分别接触双方当事人,进行俗称的“背对背”调解。这种不公开性和其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是容易让当事人一方产生对法官不公、“幕后交易”的担心,而不能做到心悦诚服,并且埋下”战端再起“的隐患。此外,由此带来的法官职权主义倾向也是值得注意并思考的。 3.诉讼调解的实际效果被高估。一贯以来,诉讼调解得以被重视和复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其与判决相比具有节约诉讼成本,便民利民的特点。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角度而言,发展诉讼的替代性解决机制具有它自身重要的价值。由于这种价值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因此主流立法大国都在致力于创设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的“司徒加特模式”,日本正在研究的“辩论兼和解模式”,其中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最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所效仿,我国国内也不乏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 然而这并不能否认诉讼调解制度同样具有不节约、不经济的一面。如前文所述,调解结案率作为一种指标被分配给一线法官,并与他们的业绩考核、评优评先以及奖惩挂钩,使得法官为了完成指标必须进行调解。此外,法官进行调解还有至少三个方面的好处:(1)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2)调解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回避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困难的问题;(3)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豝由此便有可能造成法官以调代判,不调不判的情形,再加之我国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容易导致案件迟迟得不到解决,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其次,我国法院调解在调解书送达当事人之前,其效力不稳定,只有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无效,诉讼继续进行。这种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豞甚至使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可乘之机,钻法律空子,不仅严重威胁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更是对法院权威的损害和藐视。正因以上原因,我国诉讼调解的实效在全国各地、不同案件中所发挥的效果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从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角度考虑,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同样具有亟待完善的地方。
三、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设想和方向
随着诉讼调解制度在现实司法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渐渐得到重视和承认,近几年以来,各方学者针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理论界和实务界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和制度构建的设想,为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同样站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角度,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设想和方向进行讨论,并以法院附设性人民调解为思路,提出自己的看法。 笔者始终认为,法院的职能定位应该严格按照宪法中的规定来设置,即123条和126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将法院作为处理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共识。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该严肃法院的定位和职能,让法院真正发挥定案止争的作用。这不仅事关法院的尊严、法律的尊严,更事关培养全社会尊重法律的风尚,事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社会基础。如果法院的工作“柔性”过大,则对于上述目标的建设是具有负面作用的。 那么,应该如何做到符合宪法定位与缓解法院压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统一呢?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可供参考、借鉴,并通过对其的适当改造,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根据《人民调解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制度是为了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显然,人民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这不仅能够将法院的职能和定位重新回归到审判上来,符合宪法对审判机关的定位,还有助于对案件进行诉前分流,减少法院的收案率,缓解法院的压力。人民调解制度的运用,符合我国民事司法改革指导思想的要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与诉讼共同构成我国纠纷解决体系。豟 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的人民调解制度由于存在种种不足,在经历80年代的短暂繁荣后,如今一直萎靡不振。虽然近年来我国从事人民调解员数量一直保持在500万人左右,但却出现人多案少,作用不明显的情况。其人均每年调解的案件仅1件左右,与法院的工作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河南法制报刊载的消息,2008年全省28.3万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近38万件,人均1.3件;2009年上半年26.2万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近16万件,平均每个人民调解委员会2.9件,人均不足1件。豠2010年6月的《检察日报》则在文章标题中就直接写道“人民调解:人均调解不足2件”。这都说明,我国大量的民间纠纷不是以人民调解的形式解决的。 分析以上状况的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当前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工愈加细致,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各种新型的社会矛盾大量涌现,亟需专业化、专门化的队伍建设来应对;(2)人民调解员文化程度偏低,截止2009年底,我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调解人员为298万余人,只占调解人员总数的60.3%。由此带来的政策、法律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3)人民调解理论和方式的落后,以及人员的非专业化、非职业化,同样影响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挥。 笔者认为,创新现行人民调解制度,引入法院附设性人民调解对于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帮助。法院附设型人民调解是对“诉调对接”实践中新型解纷方式的概括,指的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置专用办公室,由司法局向该办公室派常驻人民调解员进行诉前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豣作为诉前调解的一种,在台湾和日本都有相类似的制度设置。 该制度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立案法官可以在立案时,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建议双方到法院附设调解机构先进行调解,若调解成功,则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若调解不成功,当事人双方仍然可以正常进行诉讼程序。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将调解人员和调解组织转移到法院内进行工作,不仅可以极大的方便当事人双方以及法院节约司法成本,重新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让人民调解员有案可做,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法官与调解的相分离,使法官可以专职于审判,有利于法院宪法定位的回归。同时,还可以实现法官考核与调解结案率的彻底脱钩,杜绝其中可能发生的对当事人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发生。 和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相比较,法院附设性人民调解制度有着场所优势、人员配置优势以及调解成功后的司法确认程序上的优势。由于调解场所设在法院的专门办公室内,不仅方便当事人进行调解,也方便了双方在调解成功或不成功时进行司法确认和开始诉讼程序,同时法院的氛围也有助于提高双方对调解的信赖和结果的认同。在人员方面,通过由司法局安排专职、专业人员负责调解,统一纳入法律从业人员系统,使其职业化,还可以有效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保障其文化水平,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此外,法院附设型人民调解还可以在当事人双方调解成功后,对调解结果及时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法律效果,从而杜绝了因为调解效力不稳定造成日后一方反悔,浪费司法资源,以及恶意调解拖延时间的可能性,有助于迎来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社会纠纷的复兴。 据以上构想,法院的工作将与调解制度脱钩,法院附设型调解仅仅是以法院为场所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不在是法院的负担。我们本不该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希望和职责都交给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为了让人民法院更加高效地工作,我们有必要让法院将重新回到其本质的审判功能上来,更好地发挥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作为调解制度本身,它必须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尊重私法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它必须在符合宪法精神的前提下运行。调解制度不能为调而调,不能因为调解制度而使法律变得过于“柔性”以致不可预期,更不能只看重其社会效果而将法律仅仅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司法,是一个国家定纷止争的机构,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牺牲公平正义可以作为换取短暂“和谐”的代价时,司法权威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和撼动。而司法机制如若失灵,党和政府就无法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各种纠纷,民众便只能诉诸于暴力等非理性手段,如此,损失的将是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牺牲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