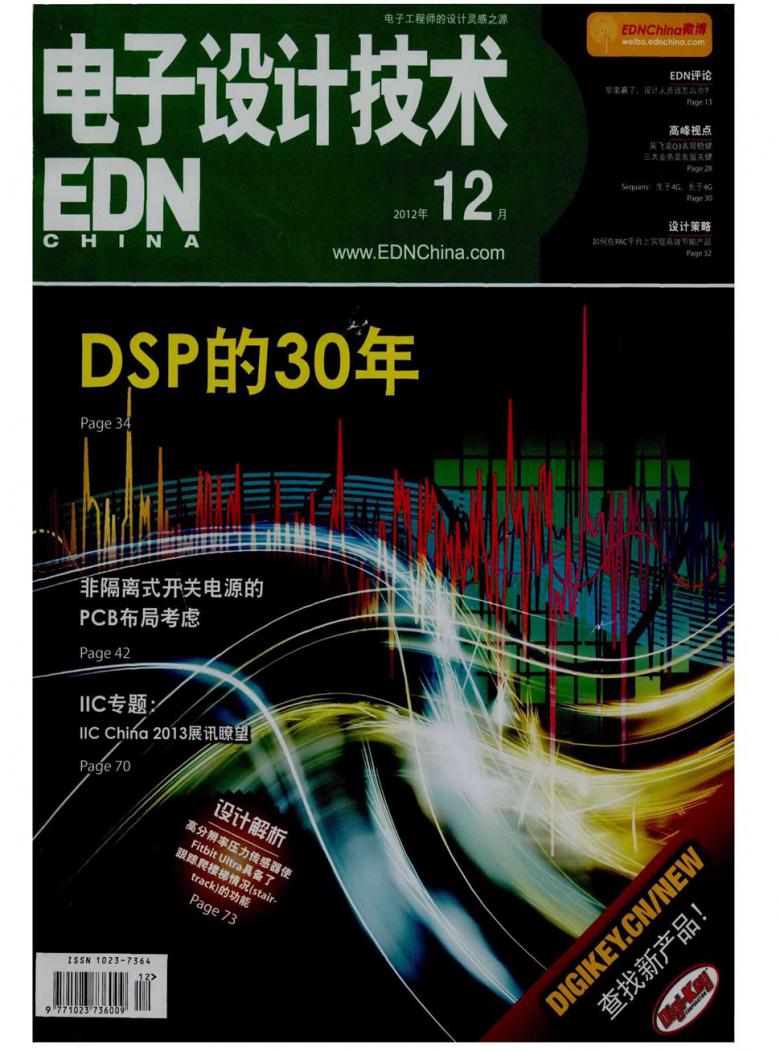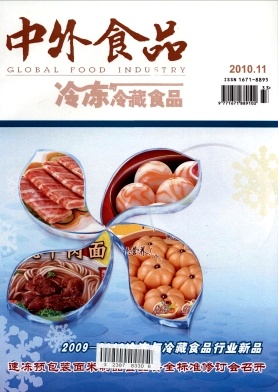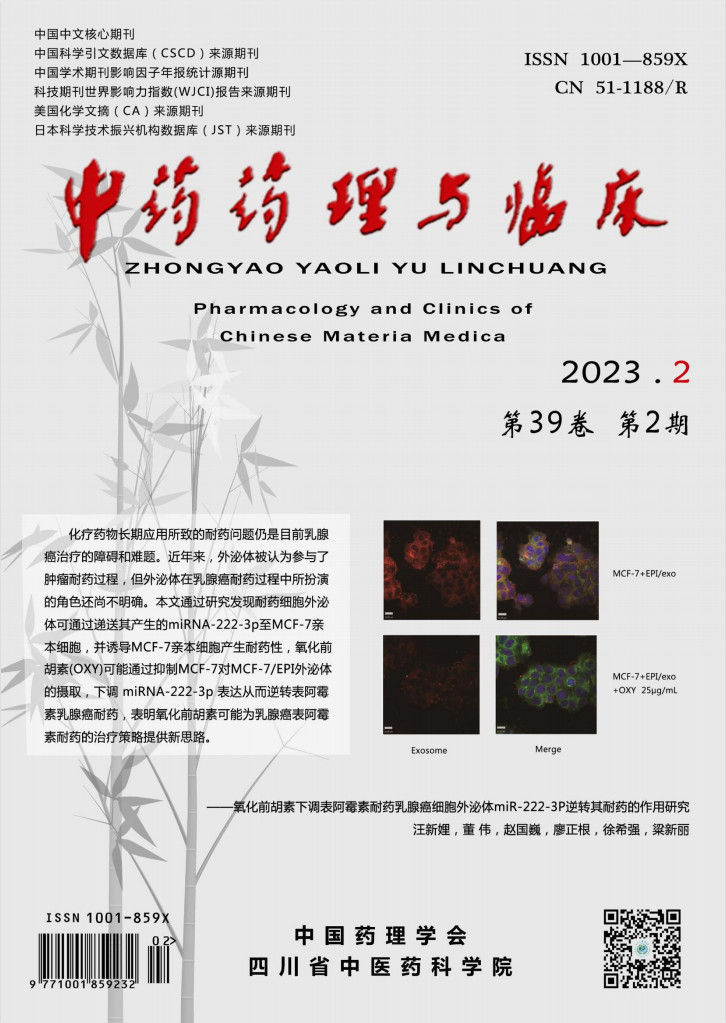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马 敏
【英文标题】The Study of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 and the Paradigm Change of New Historiography
【内容提要】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上,深入探讨了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
【摘 要 题】史家与史学
【英文摘要】The study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ttention in the recent 20 years,which also becomes one of the focuse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studies as well as promotes the progresses in city history,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modernized history to the great extent.Based on the relevant aspects constructed in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new historiography,this paper probes into research angle,history explanation,theoretical thinking,and paradigm breakthrough respects in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ctory study,which build the academic meaning of new historiography.On the basis of above studies,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n new historiography on facing the 21st century,is"general history"signed the new Society history.
【关 键 词】商会史/新史学/范式/总体史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new historiography/paradigm/general history
【 正 文】
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换言之,商会史研究的开展是与改革、开放后新史学的构建相同步的,商会史研究中的突破体现了新史学所取得的进展。
之所以认为商会史研究的进展与新史学的进展有着内在关联,乃是因为商会史研究能在不长的时间中异军突起,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首先便在于广大商会史研究者能够勇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地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从而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层次的提升。否则,“商会史研究只能是一种表象的陈述,而不能充分显示商会史研究应具有的特色”[1]。
新史学的建构其实也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拓展、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商会史研究亦如此。过去在理论架构上,商会史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中结构—功能理论,并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这种理论范式的支配下,比较注重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商会中的现代性因素,却相对忽略商会的复杂性和区域性特征,忽略其与传统相联系的一面。对引进的一些西方理论,如“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也多少有食洋不化之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史学建构中所存在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总之,本文拟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深入探讨商会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构建的学术意义,而重点又将放在商会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问题上。
一、缘起:范式与范式转换
究竟什么是“范式”(paradigm,或译规范、典范)?其实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库恩也从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从他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的阐释,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库恩认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科学工作者按同一规范组成的集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库恩有关“范式”的理论,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研究在内)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有的研究者提出,近现代史研究中所谓“革命”模式、“现代化”模式、“国家—社会”模式等分析框架,也就相当于库恩所说的“范式”。
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任何带有概括性质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要受某些理论的暗中制约,总是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思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的转换?究竟存不存在范式的转换?范式转换对史学研究究竟有何实在的意义?应该说,这些才是史学从业者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杨念群在评论德里克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史学取代革命史学的“范式转换”时,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还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2](p55)我想追问的是,如果真的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那么“范式”概念的运用对历史学究竟还有何实在的意义?库恩所强调的似乎恰恰是“范式转换”在科学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范式本身。他认为,“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3](p10)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似乎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的范式之间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而这种范式转换是否也恰是社会科学认识不断走向进步的机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作为“新史学”出现的新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4]这里明显地发生了范式的转换。同理,我们似乎也可以认同德里克的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也就是库恩似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否定先前的“革命”范式。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很难有如此彻底的完全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固然是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否定或扬弃,但这并不意味着牛顿的古典理论已毫无价值,在一定的层次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它仍有自身的解释意义。
我始终认为,在将库恩的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于“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这就是要认真去思考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深化历史思维的启迪作用。而“范式转换”对史学研究的启迪作用,首先就在于对某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
黄宗智曾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解释框架的危机归结为“规范认识”的危机,提出:“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他认为,这才是库恩“范式”一词的真正涵义。在黄氏看来,规范信念和规范认识比起任何明白表述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为广泛、更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但不幸的是恰恰是某些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似乎发生了危机,即规范认识的危机。危机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所揭露的一系列悖论现象。而悖论现象则是指那些现有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黄氏所列举的悖论现象包括: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同时存在;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的同步发展;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