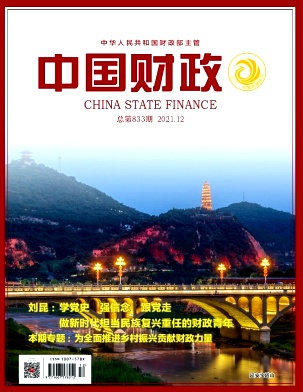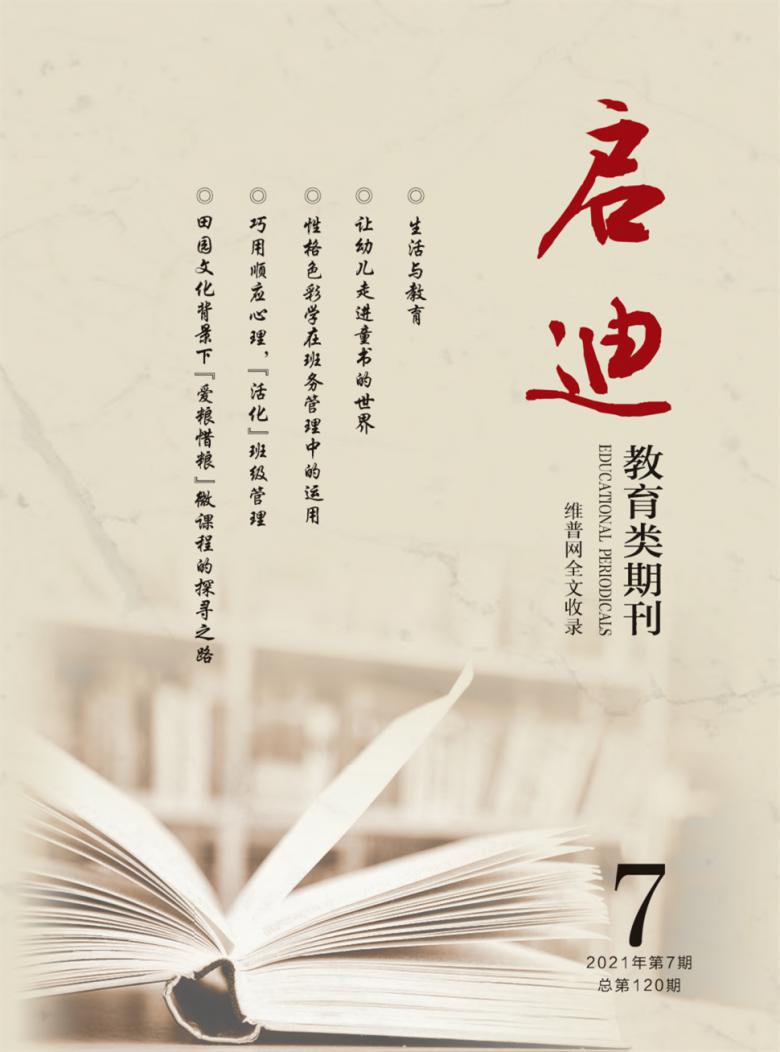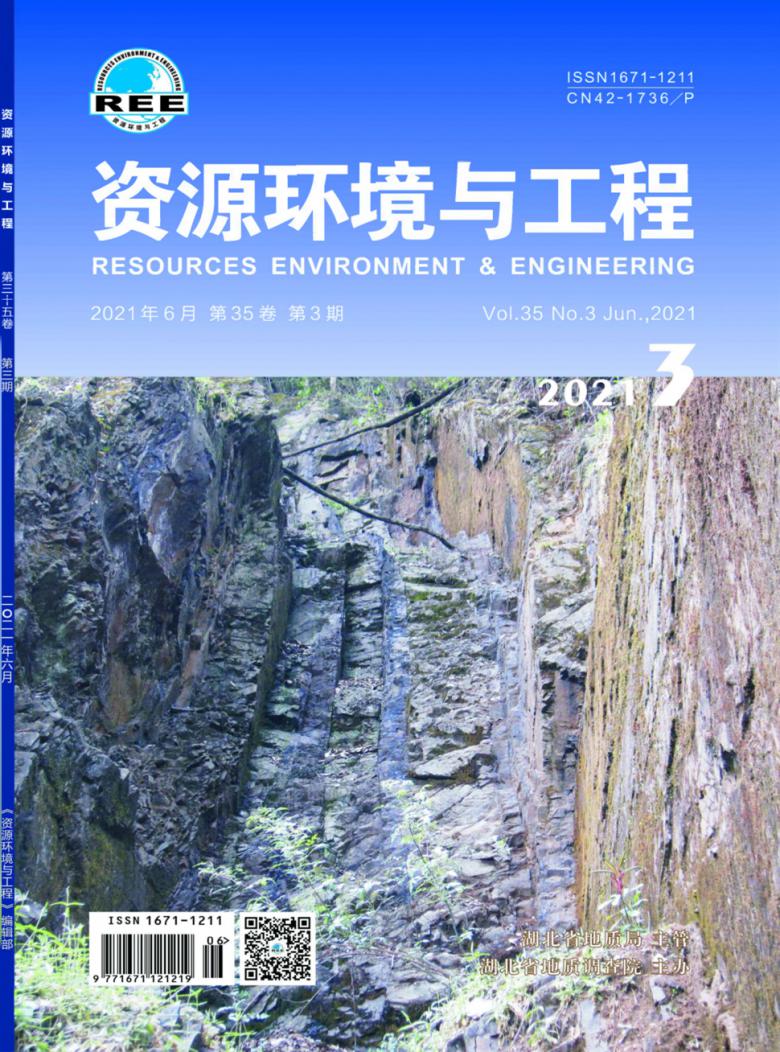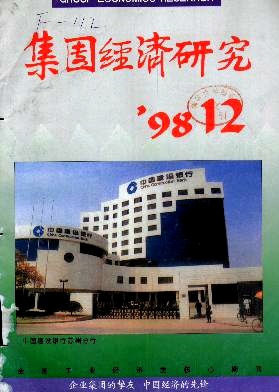文学权力:一个社会学的阐明
朱国华 2006-01-19
在西方,最迟从尼采开始,对权力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暂且不必说将权力普泛化的学术新贵福科,我们只要拈出两个著名思想家的两段话也许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罗素说:“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 吉登斯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 我们不妨由此可以推论,文艺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可以从权力的视点切入的。但令人多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无论是韦伯、罗素、帕森斯等学术巨擘,还是米尔斯、马丁、达尔、贝尔(Berle ,A.)、荣(Wrong,D.)、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J.)等著名学者,尽管在论述权力时或许偶尔提及文学, 但总的说来,专从权力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尚不多见。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福科虽然多次强调权力与话语或知识的共生关系,但一旦涉及到文学问题,他就有些犹豫不决了,尽管文学显然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文学只是一种休息,行路时的随想,一枚徽章,一面旗帜。” 他一面强调人们注意文学的“不及物性”,一面又建议我们研究文学与大学、作家与教授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
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 但在别的地方他又似乎强调了文学的自律性。他指出:文学是“处在一张纸的空白之上的语词沉默、谨慎的沉积,在这里它既不拥有声音,也不存在对话者;除了它喃喃自语外悄然无声,除了它彰显自身存在的光亮外寂然无为。” “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人不停的消亡并让位给语言的那个场所,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 事实上除了偶尔谈论前卫作家,以及“作者之死”外,福科对文学本身谈论得是非常稀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西方社会,文学很早就被赋予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神圣性:“早期诗人是教师、预言家、先知和传统的保存者。他们的神圣职责部分地就是将统治者和国民一视同仁的加以告诫和警告,并将过去积累的智慧坚持下去。” 对于文学宗教般的顶礼膜拜,雪莱的这一段话可以说表达得最为集中:“诗人们,抑即想象并且表现着万劫不毁的规则的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所谓宗教,这种对灵界神物只有一知半解的东西,多少接近于美与真。” 与黑格尔相反,当代哲学家们纷纷把对真理的热情从宗教等等转向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成了人类本真经验的避难所,甚至是拯救人类灵魂的一块净土。当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强加给荷尔德林的诗时,他并不是在对作品进行一种理性阐释,他只是在含蓄地证明,好的文学与好的哲学一样,是超越一切因而无法加以经验分析的。在《艺术的规则》一书的序言中,布迪厄指出,对艺术的这一态度是人性自恋的结果。从哥白尼、达尔文到弗洛依德以后,艺术之恋变成了人类保存自己虚荣心的最后一个自恋情结。在这样的语境下,把一般人认为是肮脏、卑鄙的权力和高尚、纯洁的文学相提并论,似乎的确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文学的确也缺乏人们所熟知的权力表现形式,她似乎远离刀枪剑戟的胁迫、黑衣法官的威严和金银珠玉的眩目,而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才被建构起来的关于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观念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并成功地掩盖了文学在历史上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对于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讨论权力时把注意力投向政治、经济和军事而非与权力似乎距离甚远的文学,显然要简便得多。大多数学者们,讨论权力时,往往首先是政治权力。但我们认为,文学和权力在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一种权力,尽管在现实语境中,是一种弱化的权力。但在我们论证这一点之前,先要阐明一下“权力”一词的涵义。
几乎每一个著名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都有关于权力的各种定义。其中一种观点倾向于把权力视之为一种普遍能力。例如霍布斯认为:“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但尽管这个经典的定义得到了不少社会学家的响应, 却在后来被命名为冲突论而受到批评。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功能主义主张:“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强抵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韦伯强调个人、冲突和主观意志,而帕森斯强调集体、一致性、合法性和系统的先在结构,但是,正如有的学人指出的:“‘冲突论’和‘一致论’这两种方法都一样有效,但都失之于偏颇,并且,它们绝无可能被整合起来。因为,围绕着每个模式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诸原则是互不相容的。” 本文不打算冒险重新下个定义以图超越两者的对立。这倒不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这个方面已有不少徒劳的尝试,主要是因为对某个大家熟知的术语下定义,除非像泰勒那样对“文化”进行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往往容易变成由既定思想体系出发的一种本质主义的应用或图解,并在突现自己片面的真理的同时,遮蔽了该术语本身所蕴含的多元性。因此,我们愿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需要,指出权力现象的两个主要(而非全部)特点。
第一,权力作为一种影响能力,其基础来源于对于不同资源的控制,即权力通常总是通过对某些资源的奖赏和剥夺来实现对别人行为的支配。柳存仁先生指出:“在先秦古籍中,权之一字涵义约可析为三义,即物质上之权,引申而为权轻重义。衍而为权势,再衍而为权谋。” 物质上之权即指秤或秤锤。先秦的衡器,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为衡杆,其二为砝码,即权。《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从汉字字源学上可以看出,“权”字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利益的裁决和分配的可能性。 吉登斯把构成权力基础的资源分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 布迪厄则将资源称之为资本,他认为在诸资本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最为重要。 后来又将合法化资本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 ,或译象征资本)。 本论文将吸纳布迪厄的这些术语。此外,一般认为,权力常常借助于体制而发生作用,由于体制说到底仍然属于资源的一种形式,因此,在本论文中,体制的概念也被整合到资本的范畴中。
第二,表现为诸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暴力形式或任何明显压迫性形式乃是权力的最后状态。汉娜·阿伦特指出:“权力是使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东西。这个词本身——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dynamis,就像拉丁语中的potentia或德语中的Macht ——表明了它‘潜在的’特征。” 荣也指出:“权力有时被说成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是‘所拥有的’而非‘所实施的’:别人实现了权力拥有者的希望或意图,而权力拥有者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发布命令,或甚至还没有与他们在传达自己的目的时交换意见。” 具体地说,权力的实现常常借助于权力支配者与被权力支配者的不自觉同谋。当权力拥有者将符合自身利益或少数集团利益的观念体制化的时候,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把这些观念视之为体制自身本当具有的内在逻辑而加以遵守,正像米尔斯在讨论权威的概念时所指出的,权力受众基于服从是其责任的信念而自愿服从当权者的意志, 在这种幻觉之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意志已经受到了压迫。布迪厄把这种信念称之为“符号暴力”. 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典型形式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福科所揭示的那样,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 话语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这是因为:“通过话语和话语结构是我们把握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此把握过程中,我们根据适用于我们的结构,对经验和事件进行分类和阐释,并且在阐释过程中,我们赋予这些结构以统一性和规范性:如果置身其外,我们就难以思考。” 权力的上述两大特征实际上迫使我们向自己发问:第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权力,那么,构成其权力基础的资本是什么?第二,文学是否构成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将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论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论证
中看到,一般说来,与政治、经济等能够发生直接作用的权力形式不同,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由于它可以构成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换言之,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来源于它可以通过体制的认同而成为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行动者。
那么,我们可以从资本的角度具体展开讨论。对文学的占有,即对文学才能、文学产品、文学知识、文学地位等等的占有,是否就是意味着对一定的文化资本的占有?这个问题在现象层面并不难回答。众所周知,在西方,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代表着文明史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最迟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二十四史中形形色色的《艺文志》或《文苑传》把文学家的英名永久地载入史册,仅仅是这些事实就足资证明文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意义。但使得文学的文化资本成为可能的究竟是什么呢?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文学文本的内部这一层面在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在文学文本的范围之内来寻找其文化资本的发生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询问:文学文本是否可能构成生产和实现权力的有效手段?文本与话语尽管在概念内涵上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例如有的学人指出话语可以被视为在言者和听者之间发生的语言交流,作为一项人际活动其形式受制于其社会效果,而文本作为语言交流则仅仅意味着被编码的信息。 保罗·利科甚至认为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 但我们不妨暂时忽视这些对于本文无关宏旨的区别,将它们在“包含具有可详细说明的交流功能的全部语言单位”的意义上视为同义词, 由此,我们可以说,讨论文学文本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讨论文学话语的权力。
文学话语是如何可能拥有权力的呢?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福科有关论述。福科曾经在《话语的秩序》中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他说:“我眼下以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在其产生的同时,就会依照一定数目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对付偶然事件,并规避其笨重的、令人敬畏的物质性。” 他继而具体论述了这些程序。其中包括“排斥程序”,即设置一些不能谈及的言语禁区,例如性与政治;对话语进行一些区分,例如确认一些话语是理性的,另一些是非理性的;以及所谓求真意志,即对话语作出真伪的划分。但福科认为这些只是影响话语的外部的程序系统,他还指出了从话语内部起区隔、限定或支配作用的另一组程序,即一,注解,这一实践力图不断把所谓原始意义强加到话语上,例如历代儒者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二,稀少性原则,通过“作者”这一功能性标签把一种虚构的统一性强加到话语上;三,学科性原则,即通过一些话语分类的规则来实施对话语的约束和控制。最后,福科还指出了进入话语的条件,例如言语的惯例或者说仪轨,创造或保存某种话语的话语社团,共同恪守某一话语信条的信仰群体,以及对话语的社会征用等等。
福科的上述观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并且在方法论上可以作为本论文的基本出发点。文学作为一种重要话语,它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组织、区分和解释我们的经验。因此,它也可以构成权力的媒介之一。但结合到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福科似乎还很难照单全收。这是因为,第一,当他提到话语的时候,他主要考虑的似乎是知识性话语,而文学显然不能被视之为一种知识性话语。最明显的情况是,作者作为一种功能性能指符号,在知识性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意义完全不同,十七世纪以来,谁是某个科学话语的作者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文学领域里刚好相反。 第二,福科有一种泛权力的倾向,话语的权力属性何时较强,何时较弱,以及,各种形式的话语如何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来构成权力的媒介,福科则明显语焉不详。要将其思想方法转化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的操作原则,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话语实践的有效性一方面固然受制于权力体制所强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不能在任何语境下简化为权力体制的图解,我们必须结合文学领域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其权力的特性。保罗·利科曾经描述了话语的两个特征。即一方面,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即话语不仅仅关涉一定的语境,关涉言者和读者或听者,而且,话语总是关于某物的,可以说客观上具有某种叙事性质。另一方面,全部话语又具有一定的意义。当话语作为一个事件来实现时,它同时就可以被理解为意义。 在话语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我们强加以意义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话语具有话语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被建基于一定的符号资本之上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符号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依赖于权力体制的认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符号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其实是同义词,使用这三个概念只是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角度的强调而已。 具体地分析文学话语的话语权力,也许可以从文学话语的叙事特征开始展开。热奈特指出了一般所说的叙事的三层含义:“叙事的第一层含义,如今通用的最明显、最中心的含义,指的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叙事的第二层含义不大普遍,但为今天叙述方面的分析家和理论家所常用,它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时间,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叙事的第三层含义看来最古老,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 热奈特分别用故事(所指或叙述内容)、叙事(能指或陈述、话语、叙述文本)、叙述(作为事件的叙事,即讲述行为)来指代“叙事”一词的这三种用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前两种。其中,作为所指的叙事为许多其他话语类型所共同拥有,例如,正像罗兰·巴特所说的:“叙事存在于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新闻中。而且,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 实际上,当代学人谈论起“叙事”一词的时候,已超出了罗兰·巴特的范围,在诸如利奥塔尔等人的论著中,科学、哲学等等作为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文本单位,也是一种叙事,甚至一切话语都被认为是叙事性的。另一方面,作为陈述的叙事,也就是热奈特更为关注的叙事话语,则规定着文学的文学性。我们认为,假如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较为完整的得出文学话语的权力的性质及其特点。
首先,作为所指的叙事,文学话语确定着所叙之事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功能。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伟大的小说里让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个人‘体验’作为它的内容。” 这就是说,文学叙事通过特定的叙事语态、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规则,通过对包含在叙事话语中的一些经验、事件和人物关系的选择、组织和书写,通过个人化或主观化的生命存在的体验,通过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信念和感觉,构建了一种对受众而言具有影响力的观物方式和体物方式。具体地说,在文学的阅读经验中,读者被强加以做出善/ 恶、真/ 伪、美/ 丑、理想/ 现实等区分,并在实际上在接受善、真、美、理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假定,换言之,接受了其话语权力的支配,但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必要强调指出,与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更多的隐蔽在真理的伪装下不同,文学叙事则遁迹于语言和故事的虚构性和想象性中,似乎摆脱了它与特定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注意它与一定话语权力的关系:因为当意识形态假装它不是如其所是的时候,符号权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顺便指出,正如有关学人所揭示的那样,文学话语的权力策略“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作为一种自觉的权力策略,它是叙述主体的权威性的体现;作为不自觉的话语,叙述主体被压倒了,叙述语式不过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种插入方式。” 从文学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的情况来看,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间接、越来越隐蔽了,而其权力策略的超主观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了,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到。
但作为能指的叙事则又似乎总是倾向于瓦解着种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通过将自身自然化为常识而不断的自我复制,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似乎失去了它与特殊观念或利益的联系,从而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封闭意义的多重指向。但文学所固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多义性,一言以蔽之,文学性,却有利于文学行动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独白陷阱。众所周知,文学的文学性是通过诉诸形式而得以实现的,正如马拉美所说的:“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句写成的。”当文学家沉醉于对叙事话语本身的迷恋之中时,文学话语常常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学家本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预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早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在那封著名的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其实正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提出“形式的专制”的概念:“一出剧,一部小说,只有借助能‘融合’和升华‘素材’的形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作品中,这个‘素材’已脱离了它的直接性,称为某种具有质的差异的东西……内容已被作品的整体改变了,它的原意,甚至会被转化成相反的意味。这就是‘形式的专制’. ” 形式的专制对抗意识形态的专制,艺术通过服从自身的规则而从意识形态的包围中突围而出,并申说自己的真实。马歇雷认为,与科学废弃、消除意识形态不同,“文学通过运用意识形态而挑战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文学文本谋求表征自由和叙事真实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开始偏离自己原先的出发点,文本的矛盾、混乱和不协调,暴露了能指与所指的裂缝,这样就导致了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沉默和不在场。用马歇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日常言说所绑架的‘生命’——这一‘生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其回声——以其自身的非现实性(借助于现实性效果的生产而出场)与日常言说相对峙;而完成了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加诸其上)揭示着意识形态的诸多裂缝。” 当然,解构主义者为了颠覆文学的在场权力,倾向于夸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所谓延异!猧fference),他们从解构策略的立场出发,忽视了在较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能指与所指、意识形态与文学性之间客观存在的同一性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两方面初步推论出文学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感知、体验和观念,一言以蔽之,通过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上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装置,成为一种符号权力。但另一方面,文学对于自己审美形式的追求又可能会使自己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离心力量,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可能会淘空、肢解和撕裂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具体性和连贯性,并导致它所由出发的符号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归于解体。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话语权力,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却远不是一种严密、稳定和完善的权力。 参考资料:
伯特兰·罗素著,吴有三译,《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 页。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0 页。
例如贝尔曾经说过:“历史地说,权力总是寻求艺术之助。”“权力结构的形式也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代文化——文学、艺术、交流。”一类的话。
参见Berle ,A.,Power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 1969 ),第10页、第57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例如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充分研究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构成了本论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必须指出,从权力角度出发与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仍有不小的区别。权力说突出了权力,即对人的控制。意识形态突出了观念的虚假性或非真理性。运用意识形态理论未必能够解决全部的文学社会学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意识形态,可称为边缘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例如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可能构成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对抗,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一种反意识形态。此点后文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二,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展开,必须建立一个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而通过研究诸资本的占有、流通、分配或转让就使这种微观分析成为可能。三,还要注意文学内部的游戏规则,即相关分析应该能够根据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当然,我们这里陈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福科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第90、91页。
Foucault,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Tavistock and New York:Pantheon,1970),第300 页。福科著,杜小真编选,《福科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参见第72页。Morton W.Bloomfield and Charles W.Dunn,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 ,(Cambridge :D.S.Brewer,1989) , 第4 页。
章安祺编订,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 页。
霍布斯著,黎思复等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页。类似的观点如罗素说:“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23页。)
荣参照罗素下定义说:“权力是一些人产生有意的和预期的、针对别人的结果的能力。”Dennis H.Wrong,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0),第2 页。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1页。
例如,布劳说:“它(按指权力)是个人或集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全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的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彼德·布劳著,孙非等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 页。)达尔说:“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在现代社会科学里,权力这一术语是指诸社会单位之中的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一定情势下依赖于另一些单位的行为。”见Shils , E.,(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Houndmills: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第407 页。
拉斯韦尔、卡普兰、达伦多夫等人也有类似见解。参见罗德里克·马丁著,丰子义等译,《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2、83页。
《权力社会学》,第85、86页。Holmwood,J.,et.al.,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roy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第119 页。
柳存仁著,《说权及儒之行权义》,载《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一期,台湾中央文史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印行,第127 页。
陈平的一段轶事颇可说明这一点:“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世家》,卷五十六。)
见《社会的构成》,第378 至383 页。
布迪厄著,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 至122 页。
参见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第123 至139 页。
当然,基于符号资本的权力即符号权力。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 页。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7 页。
转引自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23页。
布迪厄说:“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迪厄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 页。)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得更清楚:“任何符号支配都预先假定,在受制于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这种合谋关系既非被动的屈从于一种外在的约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价值……符号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要求那些承受符号支配的人具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自由和约束之间那种寻常的对立站不住脚。”(同上书,第320 页。)加尔布雷斯则将权力的这一性质称之为“调控权力”(Conditioned power ),他说:“调控权力是通过改变信念来运作的。说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适当和正确的社会准则,使个人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反映了一种心甘情愿的过程,但人们并不承认服从这个事实。”(加尔布雷斯著,刘北成译,《权力的剖析》,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 页。)福科著,张廷琛等译,《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99页。Mills ,S.,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第54页。
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4 页。
有的学人说得更明确:“文本可能是被书写出来的,而有的话语是被说出来的,文本可能是非互动的,而话语是互动的,……文本可能或长或短,而话语总意味着一定的长度,并且文本可能拥有表层的一致性,而话语则也许拥有一个更深层的一致性。”出处同上。保罗·利科尔著,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学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 页。
参见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3 页。换句话说,我们把文本的涵义扩大到口传领域。Foucault,M.,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Adams,H.& Searle,L.,(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第149 页。
以下的有关讨论均可参见此文。参见福科著,《作者是什么?》,载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91 页。
参见《解释学与人文学科》,第136 页。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 页。
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等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 页。
董学文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 页。
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684 页。马尔库塞著,《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5 页。
Macherey,P.,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Henley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