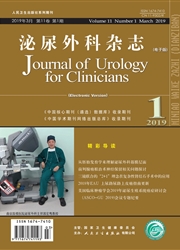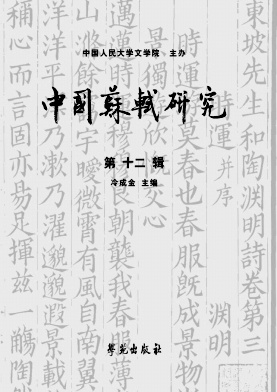明清之际松江幾社的文学命运与文学史意义
朱丽霞 2008-08-25
【内容提要】 在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视野中,晚明复社一直是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并将与之同时诞生的许多其他文学社团湮没了。事实上,明清之际与复社大致同时的松江幾社,无论其成立及活动时间、成员构成、文学思想还是文学创作、文学史地位等诸方面均独立于复社之外,它以迥异于复社的存在方式、生存特征、学术背景和文学史影响,体现出晚明文人社团丰富的精神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松江幾社不仅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而且是较复社具有更长久的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文学社团。
近年来,关于文人结社的问题日益成为晚明文学研究一大学术热点,而且多聚焦于晚明复社。由于复社人数众多的壮观“声势”和几欲摇动朝政的“权势”,使研究者步入了一种理解的“误区”,似乎晚明所有的文人社团皆可纳入复社的研究体系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松江幾社,就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并显示出长久的生命活力和独特的个性。本文拟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幾社的兴衰作一探讨,以期跳出晚明文学研究的“复社中心主义”,唤醒文学史“真实的记忆”。
一、幾社成立及活动时间
关于幾社的成立,历来文学和史学研究存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幾社为复社分支。如廖可斌认为,幾社是“从复社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社团”①。何宗美也将幾社视为复社旁支②。李圣华亦曰:“复社成立,幾社为其重要一支。”③ 由此将幾社纳入复社研究体系之内。其二,认为幾社为呼应复社的立社宗旨而成立,如杨钟羲《雪桥诗话》云:“云间幾社,李舒章与陈卧子承复社而起。”邓实《复社纪略跋》言复社“上继东林,而下开幾社”④。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言幾社“与复社相呼应”。此后,章培恒、郭预衡、袁行霈等所主编的文学史均承此说。上述观点产生的原因在于多数幾社成员同时又是复社名士,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但这种“两属”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幾社即是复社的分支,因为在明末社事纷纭的文学环境中,许多文士可同时参加几个社团而属于自由身份⑤。事实上,幾社与复社均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年)。两者的前身皆是崇祯元年(1628年)成立于北京的“燕台十子”社。从时间上说,幾社甚至早于复社。其后,因对于社事发展的构思两社不相统一,复社主广大,幾社主简严,两者分歧日渐显露。杜登春《社事始末》曰:“两社对峙,皆起于己巳(1629年)之岁。”是年,复社即有尹山大会,其后又有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以壮其声势,而幾社则悄无声息地在松江一地切磋古文时艺。凡此可见,幾社既非复社分支,亦非为呼应复社宗旨而成立,而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学社团。因而晚清朱彭年《论诗绝句》论吴梅村诗学渊源即曰:“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即将复社、幾社等量齐观。钱仲联为太仓县博物馆张溥故居题写楹联,其下联曰:“继东林,匹幾社,千秋山斗仰天如。”亦将复社与幾社并举。 从立社宗旨看,两社都旨在恢复“古学”。但复社意在广大,重视文章气节,以提拔奖掖后进为务。因此,关于恢复“古学”的立社宗旨自开始就没有严格贯彻和认真执行,而是热衷于“政治”问题。“古学”旗帜仅是复社人士进行“政治”谋略的一种诠释策略。甚至可以说,复社自开始集会便偏离了其“古学”的文学轨辙。复社,“以朝局为社局”⑥,以参预朝政作为结社终极,⑦ 以至于美国学者艾维泗也认为,复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与最灵活的政治组织”⑧。也正由于对政治的热衷,复社很快烟消云散。而幾社则在相当长时间内研习时艺,严格限定入社成员的身份,而且自开始即严格遵守立社宗旨。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幾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以声应气求之事,悉付之娄东、金沙两君子。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认为“政治”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疏离于政治问题。所以,谢国桢在《幾社始末》中说:“幾社虽然与复社合作,但是复社对外,幾社对内。复社整天的在外边开会活动,幾社的同志,却闭户埋首读书。”⑨ 崇祯末年,严峻的时事形势使幾社的文学主张也转向了对政治的热衷,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对政事和军事流露出极度的关切。如陈子龙《兵垣奏议》、《江南乡兵议》,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宋存标《秋士史疑》等,体现了幾社文士敏锐和成熟的军事思想及深广的历史意识。由此,当清兵下江南,“诸君子各以其身为故君死者忠节凛然,皆复社、幾社之领袖”⑩。尽管如此,读书科举却始终是幾社坚定不移的社事宗旨。所以阉党专权时,幾社能够幸免于难。而易代之后,幾社事业又得以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茁壮成长。 复社规模至巨,成员遍及十余省,“声气遍天下”(11)。但到南明弘光(1644年)时,阉党阮、马掌握朝柄,大量抓捕复社人士,“复社名流或死或亡,又值清兵南下,社事遂告中止”(12)。复社前后活动时间共十六七年。 而当复社事业已成过眼烟云之后,幾社事业正如火如荼。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复社之大局虽少衰,而吾松幾社之文则日以振。”复社首领张溥病卒的同年(1641年),幾社分裂为“求社”和“景风社”。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周茂源成立“雅似堂社”;彭宾成立“赠言社”;何我抑成立“昭能社”;盛邻汝成立“野腴楼社”;王玠右成立“小题东华会”。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杜登春与夏完淳成立“西南得朋会”。当复社的余火已成灰烬,幾社之爝火经短暂的间歇却很快恢复了往日的隆兴。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开科举,宋征璧等部分幾社文士应荐入仕。多数幾社文士继续在松江唱和揣摩以备应举。顺治四年(1647年),宋征舆、张安茂等进士中举。顺治五年、顺治六年,王广心、许缵曾等并举进士。松江幾社以“举业”为指归的创社理想并未因陈子龙、夏允彝诸子的殉国而改辙。所以,屡次为幾社社事提供集会场所的重要人物、幾社六子之一彭宾也毫不犹豫地做了“大清顺民”,其子彭师度本幾社名流,仕清后在京师周旋,努力汲汲于名人援引,其《上严灏亭书》表达了效忠新朝的意图和决心:“闻朝廷新令许三品以上官保举人才,而先生有荐贤为国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口俯听。……先生以盖代之鸿名,当邦宪之重地,其所保举者,当必有瑰异之行。奇特之才,久蓄于夹袋中,而某则愿有请者。”(13) 并反复表示,一旦被举,“苟得名位”,将“怀忠肝蓄义胆,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定不负所荐,以报所知。这个事实尽管不免令亡者灵魂难安于九泉,但却恰好提供了一个幾社始终以“科举”为归的有力佐证。 清顺治六年(1649年),“沧浪社”分为“慎交社”和“同声社”。二社均与“幾社”血脉相传,而“同声”皆为松江文士。 清顺治七年(1650年)松江王印周等成立“大召社”。同年,“惊隐诗社”亦在松江成立。 清顺治十年(1653年),十郡大社会于虎丘,盛况空前。松江彭师度参与虎丘集会,并以其《虎丘夜宴序言》而崭露头角。此前,松江社局由“武宣、孝力、冰修、古晋交主之,尚无歧途”(14),但当彭师度从虎丘归,松江社局很快便发生变化,彭师度网罗一郡之人,大会于“须友堂”中,开始广收门徒,扩张声势。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杜登春、张渊懿、施授樟等十人上绍“西南得朋会”而立松江“原社”,于是有《原社初集》之刻。是时,早已身仕清廷的宋征舆、李素心皆居家丁忧。宋征舆作为幾社元老,率子弟从游,宋楚鸿、宋泰渊、宋祖年等与原社诸子钱宝汾、张守来等坚持三六九讲艺不辍。因此,鼎革后的云间社(按:云间乃松江别称,又称华亭,故幾社又称云间社)实悉由直方、啬斋主坛坫。宋征舆仍然热衷于社事,成为新一代社事的首领。原社士子唱和之作结集为《振幾集》,取“重振幾社往日雄风”之义。不久,有《原社二集》之刻。其后,林古度等又从“原社”分化出“恒社”。后“原社”又再次分化出“春藻堂社”、“大雅堂社”。 松江社事的风起云涌激发起虞山钱谦益的参与热情,已经十六年足迹未至云间的钱翁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作云间之游,感慨曰:“近来南国兴文章,云间笔阵尤堂堂。”(15) 其所言“笔阵”即指松江社事的隆盛。“始信出门交有功,横眉竖目皆骏雄。”(16) 新一代的才俊正菁华烂漫,松江幾社后继有人。 清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科场案,江、浙文人涉及此案者不下百人。但由于宋氏兄弟等一部分松江士子已经仕清,幾社得到庇护,“江上之得免者,赖主盟皆在朝列”(17)。顺治十五年(1658年),松江“同声社”张友鸿辈又“渐入仕版”。顺治十六年(1659年),杜登春母舅叶方蔼高中探花。因此,尽管有科场案对江南文士的清扫,松江社事却依然盛如昔日。 松江幾社几经分化,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清康熙前期,幾社才逐渐消歇。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顺治九年(1652年)、十七年(1660年)两次禁社之诏,社事被迫消歇。二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奏销”一案,使松江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三是作为领袖的人物均过早离世而后继乏人。宋征舆既是原幾社的后起之秀,又是松江新社事的领袖,但他于康熙六年(1667年)便告别人世,终年方五十岁;其兄宋存标誓为不仕新朝的隐士,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即离别人世;宋存标子宋楚鸿,鼎革后“涉身戎马”(18) 而殒身于平乱之中。宋征舆的四个儿子均是幾社的活跃成员,但除了幼子宋舜纳外,其余三子长子宋泰渊、次子宋祖年、三子宋泰麓,均早于其父而夭亡。 尽管如此,幾社的文学活动持续时间几达“六十年”(《社事始末》),较之于复社十六七年的短暂生命可谓长久得多。清初,松江幾社诗文历数十年而流风未坠。
二、幾社成员构成与社集
松江幾社之所以能持续较长久的时间,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始终与科举紧密相联,并由家族作为社事活动的背景和支撑。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其人员多达数千,对于入社成员没有任何身份限制和规定。而幾社社员最多时也仅百余人,严格限定入社社员身份——“非师生不同社”。 成员构成方面,复社追求一种人气的旺盛,并一直为此而艰辛努力,力图扩大到全国各地,人数多达“三千二十五人”(19)。张溥在日,“称门下士从之游者几万余人”(《社事始末》)。收罗门徒不遗余力,终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噪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20)。人员庞杂,良莠不齐,这正是复社受到阉党镇压时不堪一击的重要缘由。幾社则力主简严——追求志同道合,非望扩大规模。因此,复社《国表》初刻,尽合海内名流,所入选者达七百余人。而《幾社会义》初刻,则只限于幾社六子。后扩至二十余人,到《幾社壬申合稿》所选亦只有李雯、彭宾、陈子龙等十一人的诗文。杜登春的原社,到《二集》之刻规模扩大,所收社事作者亦共五十二人,较之于复社《国表》所收相距甚远。幾社最多达百余人,亦仅占复社人数的百分之一。尽管幾社人数不及复社,但幾社成员构成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是幾社成员多以家族作为支撑:父子、兄弟,或师生或姻亲。松江宋氏家族,宋存标、宋征璧、宋征舆、宋辕生、宋祖年、宋楚鸿、宋汉鹭等一门父子兄弟子侄十余人皆为幾社成员,参与并多次主持幾社的社集集会;幾社六子之一杜麟征,其弟杜麒征、杜骏征,均幾社成员,他的三个儿子——杜端成、杜登春、杜恒春亦均幾社名人;徐孚远及其弟徐致远、徐凤彩,凤彩子徐丽冲均为幾社成员。当晚明弘光立朝,阉党掌权之日,一直操持《幾社会义》之选的领袖徐孚远谢事以避党魁之目,而以选事委之于徐丽冲。徐丽冲受任于危难之际,在国势艰难之日,使幾社选刻事业得以传承而不辍。 二是幾社成员还有不少属直系师生关系。王默公、陈正容为陈子龙之师,而陈子龙又是邵梅芬、张处中、王胜时、徐桓鉴诸子之师;夏允彝是侯玄涵、蔡嗣襄之师。“云间六子”之间也构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师生网络。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六子之昆弟、姻娅、及门之子弟竞起而上文坛”,“非游于周、徐、陈、夏之门,不得与也”。谢国桢《明清之季党社运动考》论幾社曰:“明季幾社的成立,他们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 另一方面,在幾社的文学活动中,科举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热衷于选文,将朋友唱酬的作品随时选刻出版。通过选集的传播,作为典范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指导士子的应举文章,最终有益于科考。复社由于对政治的过度热情和极力强调权力的重要,对选事意兴阑珊,《国表》共出版五辑便告终止。而《幾社会义》前后共刻七辑,其后所分化出的各个社团也均将“出版”作为社事要务。崇祯十四年(1641年),幾社分裂为求社和景风社,仍于刻印之事朝夕不倦。次年(1642年),谈叙、张子固有《求社会义》之刻,彭宾、顾震雉有《赠言初集》之刻,而李原焕、张子美则有《幾社景风初集》之刻。 即使在幾社倡导经世救国、社事由揣摩举业发展而为议论时政、其政治色彩日益浓重之日,幾社与复社的救国“策略”亦有区别。复社人员在千方百计“遥控”朝政,而幾社则力图以文学救国。为此,陈子龙、宋征璧等二十余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21),以此来体现幾社文士的国事关怀。 鼎革风云过后,清廷于下松江的同年诏开科举,汇征人才,南国文人,竞赴宾兴之会。结果,乙酉(1645年)、丙戌(1646年)两秋之闱,幾社诸君子联袂登选。中举者多为“明末孤贫失志之士”,如张九徵、周茂源、李延渠等“皆以复社、幾社名家中举上南宫”。到戊子(1648年)科,社中伏处草间的大批文士终于“尽出而应秋试”,松江王广心、杜登春、王印周、姚彦深等皆高中榜首。到松江原社,中举者日益增多,令社事元老宋征舆深为感慨,曰:“吾辈幾社文会十余年,困于诸生无一隽者,公(杜登春)等五年中中五人,又与明经选者,皆是社中人,可谓胜前辈远矣。”(《社事始末》)为此,杜登春曰:“前辈诸先生,时文外兼事古文,学不能专精举业。今日新进皆不事诗古文,殚心括帖。”诠释了幾社士子以举业为指归的结社动机。
应试科举尚不能完全满足幾社文士的内心渴求,他们认为,“括帖不足以逞志传世,遂倡为古学”(22)。他们将恢复古学作为社事宗旨,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自视为文学传统的传播者。因此,他们除对本朝诗文进行择优筛选外,也依据经典的标准进行创作,并将所作诗文结集为《幾社壬申合稿》,其中包括诗、文、词等各类作品。由于幾社文士的创作努力,不仅“一时文体、韵体靡不精研”(23),而且“高才辈出,大江南北争奋于大雅”(24)。其创作倾向,大抵可概括如下: 其一,词尚南唐北宋。 明兴以来,由于曲的盛行,词作为宋代独盛的一种诗体已经被“边缘化”了。鉴于词道式微,幾社文士倡为“小词”。他们回思词史的盛衰,认为,“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25)。南唐北宋词意辞并茂、高澹浑厚,实为词之极境。南渡以后,词道体格精神渐趋消歇。宋征璧《倡和诗余·序》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26) 他们认为,南唐北宋词已经树立了填词的美学规范,南宋词则失去了词体的独特风神和抒情活力。因此,他们将南宋以后的词全然“放弃”了。 幾社对南唐北宋词的扬帜表现于对词体的怨刺精神与社会价值的自觉认同。他们认为,词之传统乃风骚之旨,当曲折幽深,以寄托沉至之思。为此,幾社文士以诗人的巨大活力,首先在词体格调上进行追古,同时融入时代的声音,于是,消歇已久的南唐小令至此复活。从幾社文士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追寻古典的努力。如宋征舆《望江梅》:“无限意,花月自春秋。芳草半随游子梦,东风偏惹玉人愁,愁梦几时休。”(27) 词境纯净忧怨,以成功的小令体式抒写游子的羁旅愁怀。小令正是词体诞生之初的流行范式,无怪乎徐珂评其“不减冯、韦”(28)。李雯《浪淘沙·杨花》:“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偷弹。”语言清丽,寄托弘远,徐珂谓:“语多哀艳,逼近温、韦。”(29) 而从神韵和抒情技巧方面看,李雯词更似秦淮海。陈子龙词寄意深厚,胡允瑗评其《小重山·忆旧》曰:“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什。”(30) 况周颐言其“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31)。在上述文士的倡导下,幾社诸子几乎无人不染指词翰,相互唱和。填词,在幾社人士手中终于形成一场声势壮观的文学运动,并由此改变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命运——清代,不仅词体中兴,而且总体成就超越清诗。词,由明代的边缘文体转化为清代的主流文体。 词体在清初的全面复兴,幾社功不可没。吴绮《湘瑟词·序》云:“昔天下历三百载,此道几属荆榛,迨云间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说明云间派力辟榛莽、重振词体的贡献。云间词派上承南唐北宋词路,下开清词中兴之局,成为明清词运的转捩点。然尽管如此,幾社文士最大的文学成就仍在诗而非词。 其二,诗宗汉魏盛唐。 明末公安、竟陵诗风吹遍诗坛之时,幾社文士重扬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纛,以恢复诗歌审美和道德涵养的双重职能。宋征舆《酉春杂吟·序》曰:“夫风雅之泽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作者一二人患之而无以易之,于是一谢耳目之见而专求诸古。其始也,泛滥于三唐;其继也,盘桓于汉魏六季;其终也,推极原本,断之三百篇,既获所要归。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贤微言之后,且为天下唱率。”公然提出以《诗经》为规范。宋征璧自评己作“固风雅之翼”(32),并以“青莲后身”自誉(33)。几十年间,幾社文士负英雄之资,肆力著作,三百篇以外,二京六代以及三唐无不探源别派。他们认为,古诗的价值正在于托兴之深、性情之真,而《诗经》在深至的情感与雅丽的形式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于是,他们提出“情以独至为真”的作诗法则,主张情辞统一,而在此方面的典范之作即汉魏盛唐诗。竟陵、公安摒弃了汉魏、盛唐的主流传统。为此,宋征璧力排竟陵,认为“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陋,其自为主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后之人复踵事增陋取侏儒木强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犹齐人之待客……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34) 相对于明季的国运,竟陵诗风确实不合时宜,其清幽孤僻的诗境不能体现出盛大气象,尤不能振奋人心,以至于朱彝尊诋为“亡国之音”(35)。 由此,幾社文士倡导复古,古诗则蹑迹汉魏,近体则联镳开宝。其群体创作成为其诗学观点的“释证”:吴六益《长安清明》:“独上高原发浩歌,支离南北奈愁何。樽前病起清明过,客里花开夕照多。闽海羽书连紫塞,江淮归雁渡黄河。遥怜弹瑟三山外,细雨扁舟傍薜萝。”高音亮节,颇得少陵气骨。李雯《寒食》:“谁能寒食不思家,御柳纷纷欲作花。天下何曾接烟火,京师不解重龙蛇。伤春满目风尘异,作客深愁云雾遮。忆得故园归梦好,飞飞燕子向人斜。”格清气老,秀亮淡逸,杨际昌谓其“诗宗王弇州、李于鳞”(36)。宋征舆《七夕宴吴兴陈司理署楼同卧子及州守陆君》:“高座凉风百尺楼,乌程美酒客销愁。云霄月上天河澹,牛女星前花雾收。河朔主人能独醉,江南游子共伤秋。夜深玉漏无消息,五斗高谈四座留。”体格高浑,首句显然化用王昌龄《从军行》“烽火楼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之句,结响宏亮,得风雅之正则。陈子龙论宋征舆诗,“大而悼感世变,细而驰赏闺襟,莫不惜思微茫,俯仰深至,其情真矣。上自汉魏、下讫三唐,斟酌摹拟,皆供麾染,其文合矣”(37)。认为宋子之诗做到了性情与形式的统一,这正是古诗规范。 在遵唐的途辙中,幾社文士体现了主体精神的一致。陈卧子“文高两汉,诗轶三唐”(38);田茂遇“兼青莲、少陵之胜,而轶驾于北地、济南之上”(39);董苍水“究极于风雅正变之间,爰及汉魏,下讫三唐”(40)。所以,幾社名士彭宾言明季诗坛“诗亡之后,力砥狂澜,功在吾郡”(41)。由于迥异于竟陵诗风,至清初诗坛,“一时作者如繁星之向辰极,百川之赴沧海”(42)。故吴梅村亦称,松江幾社于明季诗坛深具“廓清摧陷之功”(43)。 在诗词复古的同时,幾社文士主张“文以范古为美”(44),“赋本相如,骚原屈子”(45)。他们认为,前代古文典范唯有两汉,陈卧子在《幾社文选·凡例》中昌言:“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确立了文规两汉的创作准则,并以此标准进行古文研摩。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时代风气迥异,显示出对二京之文的强烈爱好。杜麟征《壬申文选·序》:“文章起江南,号多通儒,我郡为冠。”宋存标主笔选刻《幾社壬申文选》“开史汉风气不趋时畦者”(46),所选古文皆异于竟陵时流,结果“海内争传,古学复兴”(47)。 幾社文士在创作方面的诸多努力,很快发展为一种趋势,朱鹤龄云:“文场建鼓,夙仰云间。大雅扶轮,群推海上。”(48) 明清之际,“称文章者,必称两社(复社与幾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49)。这说明,幾社的创作不仅已经广被认同,而且获得了普遍的感染力。至清初,终于使“天下无论知与不知,诗文一道皆推云间”(50)。
四、幾社文学史地位
在文学史上,对于晚明文人社团的研究多聚焦于复社,先后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梅村《复社纪事》、杨彝《复社事实》等,而专门记载幾社的只有杜登春《社事始末》,近人亦仅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于缺少相关文献记载和历史的误读,幾社的文学史地位几乎被忽略了。事实上,幾社作为一个严格的文学社团,以其长久的文学生命在文学史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重要席位,尤其在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朱培高曾云:“云间派诗、词不但在明末具有极大影响,在清初也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流派。”(51) 所言即云间派诗词文于清初的全面影响。 词的创作并非云间派主流,但恰是词为云间派赢得文学史上的至高声誉。“云间词派”既挽明词衰微之局,同时又直接开启清词中兴之势。清初词坛群宗晚唐的趋向即源于云间派的倡导。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言云间词派以晚唐、北宋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52)。以致清前期百余年的词坛都充斥着云间派的流音遗响,清初词坛纷纭的诸流派几乎无不遵循云间路径、沾溉云间词风,如浙中词坛的“西泠十子,皆云间派”(53);阳羡派宗主陈维崧早年学词即从“云间”入手,其所效法者“在云间陈、李贤门昆季”(54);主持康熙词坛近半个世纪的王渔洋词亦“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摩手追,半在《花间》”(55)。云间派被清初词坛普遍接受的事实说明,清词之“复兴”,云间派功劳卓异。近人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说,云间词派“开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云间词派作为词史上第一个深具典范意义的词派和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成为历来词学研究的主要立足点。 诗学方面,云间派首开清诗之特色,继承七子衣钵,倡导秦汉文章、盛唐诗歌,揭开了清代诗史宗唐的序幕,成为有清一代唐、宋诗之争的源头。凌凤翔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作序论明末诗派之衰有云:后七子之后,“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弘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号云间体”。顾景星《周宿来诗集序》曰:“当启、祯间,诗教楚人为政,学者争效之,于是黝色织响横被宇内。云间诸子晚出,掉臂其间,以大樽为眉目,追沧溟之揭调,振竟陵之衰音”(56),清扫了晚明诗坛的衰飒之气。云间派是“‘七子’诗风得以历晚明而入清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的中介”(57)。晚明,“钟、谭之名满天下”和“天下群趋于竟陵”致使“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七子之学已被挤向诗坛边缘而渐趋消歇之际,云间诗人挽救了七子诗学的危机。因此,全祖望评曰:“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齐盟,王、李之坛几于厄塞,华亭陈公人中出而振之。”(58) 从云间诗人对七子的捍卫和以七子自诩的层面看,汉魏风骨、盛唐精神经由云间的播扬而在诗史上保持了诗的激情,从而使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一脉得以延续。吴梅村《宋直方〈林屋诗草〉序》曰:“(清初)天下言诗者辄首云间”。直到近代的南社,其诗学宗旨仍以云间为鹄的。陈去病、柳亚子等20世纪的反清诗人皆推重云间,柳诗曰:“平生私淑云间派”(59)。当时,南社诗人多以云间派刚劲雄浑、英雄并美的诗风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过程中,云间派再次体现出导夫先路的生命价值。 吕留良《刻陈卧子稿记言》云:明季文坛“风气为之一变者,莫如云间之幾社,为极盛一时”。其所言即幾社古文在晚明清初的广泛影响。明清之际,散文被竟陵文风所统摄,但其“幽情单绪”的审美风格已不合时宜。云间文士率先“变当时虫鸟之音,而易以钟吕”(60),在审美范式和创作标准方面均构成对竟陵的反拨。在时人眼中,云间派的艺术追求几近完美地切合了儒学诗教典范——《诗经》“风”、“雅”道统。在云间群体的倡导下,明末诗文高华雄爽,“海内言文章者必归云间”(61)。 云间派致力于复古,清扫了竟陵之弊,然而也流露了自身的缺憾。宋琬在《周釜山诗·序》中言,云间派“持论过狭,泥于济南‘唐无古诗’之说,自杜少陵《无家》、《垂老》、《北征》诸作,皆弃而不录,以为非汉、魏之音也”。其批评到位,颇具服人之力。王渔洋《花草蒙拾》亦曰:“云间数公论诗拘于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在此。”所言亦切中其弊。尽管如此,缺点并不能掩盖其曾有的文学贡献。中国文学忠君忧世的大雅传统,正是经由幾社文士等一代代文学精英的坚持不懈才得到维系和光大的。 幾社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社团,在社团构成、活动创作等诸方面均与复社有很大差异,体现出明清之际社团的复杂性,其中亦折射出文士们微妙而丰富的内心价值取向。就文学成就而言,云间派作为明末影响最大又极具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学流派(复社终究是否可称得上一个文学流派,至今尚争论不已。而云间派的流派意识自其成立之日便已确立,并贯彻始终),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言”:明清之际,“海内翕然称云间之学”(62)。云间派诗文并未因复社的“影响”而消弭自己的光彩。在清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云间派所开创的阅读传统和审美原则将成为历史中永恒的声音。
注释: ①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3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绪论》,第1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④《东林始末》,第25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36年(1947)。 ⑤如钱光绣即一连参加了六个地方的八个社团,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钱蛰庵徵君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⑥⑩杜登春:《社事始末》,《昭代丛书》本。 ⑦黄宗羲:《南雷文定·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胡秋原:《复社及其人物》,台北,中华杂志社,1968。 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上海,国学保存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12)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第5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彭师度:《上严灏亭书》,见《彭省庐先生文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17)杜登春:《社事始末》。 (15)(16)钱谦益:《次韵答云间张洮侯投赠之作》,见《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8)陈维崧:《宋楚鸿古文诗歌·序》,见《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载,吴应箕《复社姓氏》二卷,吴应箕孙《补录》一卷,所收复社人数共三千二十五人。 (20)陆世仪:《复社纪略》。 (21)《陈子龙诗集》附录二《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一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2)(23)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所附彭士超评语,见《彭燕又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宋徵璧:《上吴骏公先生书》。见《抱真堂诗稿》,清顺治九年(1652年)刻本。 (25)陈子龙:《三子诗余·序》,见《陈子龙文集·安雅堂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影印本)。 (26)宋征璧:《倡和诗余·序》,见《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余》,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7)《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余》。 (28)(29)徐珂:《近词丛话》“词学名家之类聚”,《词话丛编》本。 (30)《陈忠裕全集》,卷二十附,见《陈子龙文集》。 (3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 (32)宋征舆:《酉春杂吟·序》所引,见《林屋文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宋征璧:《与周介生书》,宋存标《情种》所附,《四库未收辑刊》本。 (34)宋征璧:《与吴子论诗书》,见《抱真堂诗稿》。 (35)朱彝尊:《明诗综》“谭元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影印本)。 (36)杨际昌:《国朝诗话》,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37)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见《陈子龙文集》,卷上。 (38)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 (39)严沆:《水西近咏·序》,见田茂遇《水西近咏》,《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40)宋琬:《董苍水诗·序》,见《宋琬全集》,第34页,济南,齐鲁书社,2003。 (41)彭宾:《王崃文诗·序》,见《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 (42)吴梅村:《宋直方〈林屋诗草〉序》,见《吴梅村全集》,第67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3)宋琬:《周釜山诗·序》,见《宋琬全集》,第13页。 (44)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见《陈子龙文集》,卷上。 (45)张溥:《幾社壬申合稿·序》,见杜骐徵等辑《幾社壬申合稿》,明末小樊堂刻本。 (46)(47)杜登春:《社事始末》。 (48)朱鹤龄:《寄王玠右书》,见《愚庵小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9)《陈子龙诗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0)宋征璧:《抱真堂诗稿》所附张洮侯语。 (51)朱培高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辞典》,第28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5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本。 (53)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第220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二辑。 (54)陈维崧:《与宋尚木论诗书》,见《陈迦陵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55)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 (56)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7)严迪昌:《清诗史》,第4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8)全祖望:《张尚书集·序》,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210页。 (59)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第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0)董以宁:《顾天石诗集·序》,见《正谊堂文集》,《四库未收辑刊》本。 (61)宋琬:《尚木兄诗·序》,见《宋琬全集》,第18页。 (62)宋徵舆:《林屋文稿·云间李舒章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