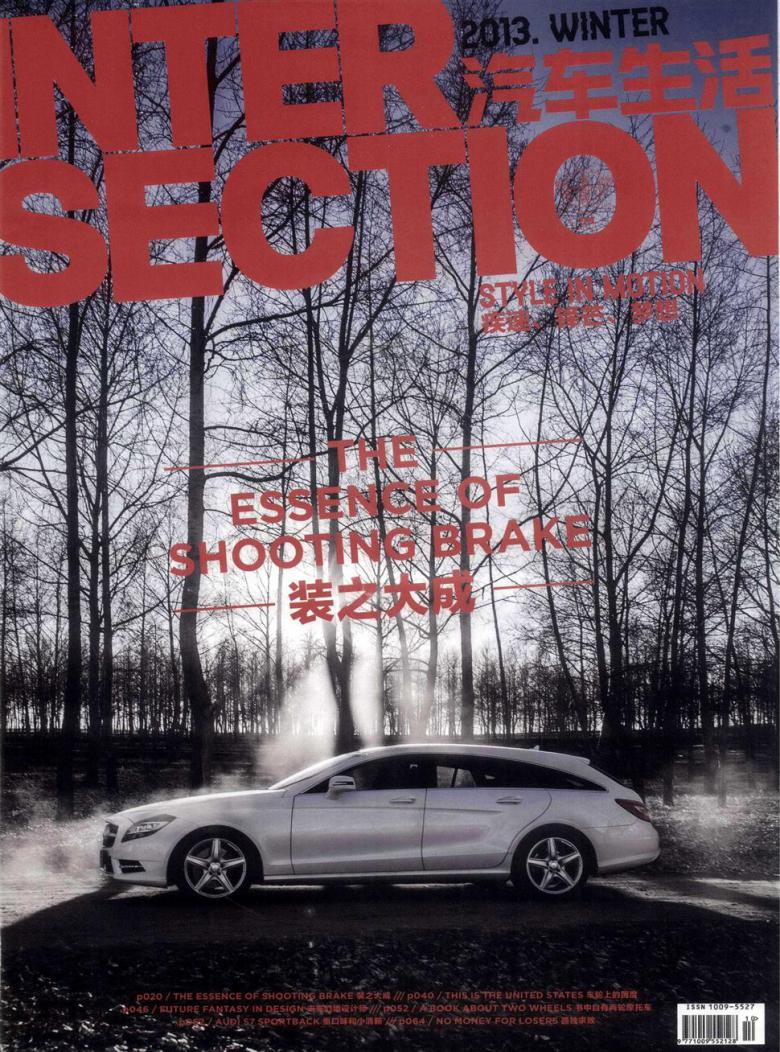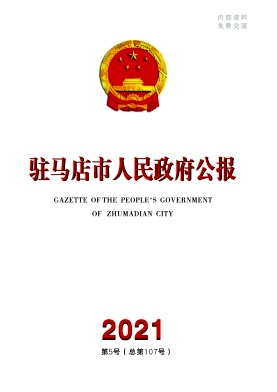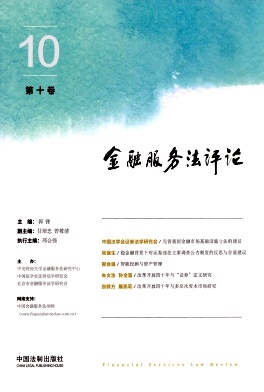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上帝意象
王本朝 2008-07-23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新诗在诗美和诗体上有着大胆的探索和创造。新诗的意象世界既传达了独特的现实经验,也呈现出丰富的价值想像。本文主要讨论现代诗歌关于上帝意象的想像与创造,认为现代诗人在设置和书写上帝意象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生成了祈祷、赞美的诗歌文体,并进一步追问建设现代神性诗学的可能性。
“上帝”是《诗经》里出现频率较高的文化意象,据统计,它在雅诗和颂诗了出现了15篇37处,与上帝有相同意义的还有“天”意象,也有80余处①。上帝也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一个关键性意象。现代诗歌不但创造了众多的指涉社会生活和民族命运的自然物化意象,而且也构建了上帝这个属于人的神性经验和终极情怀的精神意象。上帝虽说是人心所造的幻影,但它所关涉的不仅仅是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却是在日常生活和民族国家之上的价值情怀。因此,上帝意象有别于现代诗歌对一般自然意象的营造和书写,而从内部直接呈现了现代诗人的独特想像和价值经验。
一 关于上帝的诗歌想像
诗歌是最具有抒情性和个人性的文体,现代诗歌并没有陈述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事实,而是直接追问和表达上帝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相对而言,冰心、徐雉、陈梦家和穆旦等从人生意义角度肯定了上帝与人的价值关联,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石评梅和冯至等诗人则对上帝有着更多的质疑。冰心曾经相信世界有一个绝对者存在,它既是泛神论意义上的自然神,也是基督教充满着爱的上帝。她的《繁星》、《春水》和《圣诗》对上帝意象有着丰富的想像和展开②,如《圣诗?黄昏》称上帝掌握着人间智慧的奥秘,“上帝啊,/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奥秘,/谁能够知道呢?/是我们么?是他们么/都不是的。/除了你从光明中指示他,/上帝啊!/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也指示给宇宙里无量数的他。阿们。”徐雉的人生有很多不幸,但他在诗里却创造了一个“永生的上帝”③,认为“信上帝的人,虽不曾见过上帝,但他们心中有一个上帝的存在”④。“伏在黑暗里的人们,/老是摆摆手,/说上帝是没有的。/但我却从小孩子,/荡漾着微笑的浅涡里;/从花的香,/月的色,/鸟的清歌,/太阳的光,/人类的爱……里,/认识了一个永生的上帝。”⑤他与冰心一样,从自然和人类的相爱里感受到了上帝的永生。陈梦家是牧师的儿子,他的《我是谁》、《一朵野花》、《只是轻烟》、《摇船夜歌》等诗歌则传达了上帝的神秘与温馨。
徐志摩取材《圣经》的《人种的由来》表现了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的觉醒和对上帝的反叛。石评梅诗歌里的“上帝”是“虚无的神”,在《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中有这样的诗句:“欢乐的泉枯了/含笑的花萎了/生命中的花,已被摧残了/是上帝的玄虚?/是人类的错误?”她虚设了一个绝对者作为情感寄托和心理倾诉的对像,但并不相信它。冯至的《礼拜堂》借在“礼拜堂”前的“徘徊”,感受到“上帝”失去了“庄严”,“消散”了“荣华”。信仰已是“几百年前的情景”,如今却找到了另一个“真理”——“到田间耕地”。这样,“礼拜堂”就成了“无人过问的世界的一角”,“一片荒原”,孤单地发出“可怜的声息”。诗中的“徘徊”、“疑问”和“感叹”说明诗人的迷茫,也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意义。李金发对上帝的质疑却别有一番意义。上帝意象是李金发诗歌里的一个关键词。如《弃妇》中的“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故乡》中的“如兽群的人,悉执着上帝的使命”,《燕羽剪断春愁》中的“上帝正眼睁这等嘈切之音”,《希望与怜悯》中的“残忍之上帝/仅爱那红干之长松,绿野/灵儿往来之足迹”。《诗人凝视……》直接写道:“诗人凝视/上帝之游戏:/雨儿狂舞,/风儿散着发”,“游散的人,/现出一切平和,/各自在生命上徜徉,/同伫看残酷之神秘”。李金发诗歌里的上帝被看作世界的统治者,但它又是不负责任的旁观者和游戏者。“上帝”有它神圣的“使命”,但又播弄着人间的“残忍”和“游戏”。他在一首题为《上帝》的诗里写道:“上帝在胸膛里,/如四周之黑影。/不声响的指示,/遂屈我们两膝。”把上帝看作一团“黑影”,发出没有声音的“指示”,使人感到“屈膝”的恐惧。李金发是现代象征主义诗歌的开创者,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现代主义的反宗教、反理性思想显然也影响了他的上帝观念。他认为人生充满了荒诞和虚无,“多情之上帝全聋废了,/耶稣之木架长朽在寂聊之乡,/以青蓝之眼倪视行人。”(《生之疲乏》)上帝的“聋废”留下了荒诞的世界。
无论是冰心、徐雉和陈梦家对上帝的肯定性表达,还是徐志摩、石评梅和李金发对上帝的怀疑,他们诗中呈现的上帝意象和意义都相对单薄、琐碎,缺乏对上帝意象的丰富想像和独特领悟。穆旦诗歌对上帝的想像则展示了精神的丰富与挣扎。
穆旦诗歌创造了丰富的“上帝”意象,有时也称为“神”、“主”(《隐现》、《忆》、《奉献》)、“残酷”(《时感四首》)、“主人”(《荒村》、《三十诞辰有感》)、“主宰”(《不幸的人们》)、“你”(《发现》、《诗》)、“死神”(《在旷野上》)和“永恒的人”(《隐现》、《活下去》)等意象。“上帝”在穆旦那里拥有多种涵义,有的指世界不可知的统治者,如“在我们之间是永远的追寻:/你,一个不可知,横越我的里面/和外面,在那儿上帝统治着/呵,渺无踪迹的丛林的秘密。”(《诗》)有的也指“美的真实”(《我歌颂肉体》),生命的“打开”、创造和“生命的根”(《发现》)。同时,上帝也是历史和人生混乱的制造者,“告诉和平又必须杀戮,……/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穆旦并没有停留在上帝意象的直接传达,而是把生命的意义融入与上帝的关系中去追问和言说。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分裂、破碎和矛盾,“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生命有“诱惑”,也有“陷阱”,有希望,也有毁灭,“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在“时间的激流”里,积聚了太多的痛苦、绝望和沉重。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在绝望里看到了希望,“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时感四首》),他不再“固守着自己的孤岛”(《从空虚到充实》),“从虚无到虚无”,希望像“一条鞭子”,鞭打着自己,“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蛇的诱惑》),在“残酷”和“绝望”里“鞭打出信仰”。生命有了一个“深沉明晰的固定”,如同“一个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在“心的旷野里呼喊”出了一个“美丽的真理”。(《在旷野上》)。它如同“成熟的葵花”在“黑夜”里期盼“阳光”的“来临”(《智慧的来临》),他逐渐认识到,人类已有的“知识”、“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化学的原料”,“辩证的唯物世界”都无法“拼凑意义”,只有“上帝”才能把生命的“意义”“揉圆”(《黄昏》),才能显示“意义和荣耀”(《牺牲》)。在对自我和现实的双重否定和超越里,他发现了意义的“根”,确立了人与上帝的内在关联。于是,他开始了忏悔和“呼喊”:“主呵,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聪明的愚昧里,/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太多的不满,太多的生中之死,死中之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隐现》)他“赤裸”着身体,张开灵魂的“光,影,声,色”,“等待伸入新的组合”(《春》)走向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在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这条道路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祈神二章》)。
穆旦走向了与上帝的“结合”,他自己把这一过程形容为“忽然转身”发现了“隐现”的上帝,它的“秘密”和“真理”就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面对世界的“憎恶,狡猾,狠毒,虚伪”和“寒凛的地方”,他仍“要向世界笑”,并“闪着幸福的光”(《阻滞的路》)。人生的“痛苦”反而成了一种“幸福”,生命之外的“声音”如一条带血的“鞭子”,“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从空虚到充实》)于是,也就有了“人子”耶酥同样的悲剧感受,“人子呵,弃绝了一个又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二章》)。穆旦关于上帝的想像激发了他的生命感受,使他拥有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有了更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理性沉思。
二 诗歌文体:祈祷与赞美
上帝意象的设置和创造也带给现代诗歌独特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言说上帝有不同的语言选择和文体形式,明代的传教士用汉语的“天”表达“上帝”,现代的许地山认为“上帝”是一个既有人格又无人格和超人格的大精灵,“上帝”在汉语里古已有之,它是对“人间(过去或现在)帝王的一种变称,并没有神灵的意思包含在里头”,所以,他主张用“神”来称呼这“大精灵”⑥。现代诗歌对上帝的称呼五花八门,意义也各有不同,在前面我们已有所涉及。现代诗歌表达上帝的语言方式有祈祷、赞美的抒情和讽刺、幽默的叙事。对上帝的诗歌叙事因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展开,反而没有表达耶稣基督那样充分自由,如鲁迅的《复仇(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马槽》等。对上帝进行叙述的作品相对较少,就我们掌握的资料看,有徐志摩的《人种的由来》和《又一次试验》、冯至的《礼拜堂》和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等,它们以讽刺、嘲弄的口吻叙述了上帝的喜剧性和荒诞性,《罪恶的黑手》借工人修建教堂的辛苦和传教士的虚伪讽刺了上帝教义的欺骗性,其他几部作品在前面我们也有所提及。
对上帝的赞美和祈祷则成为现代诗歌的一种文体形式,可称之为“祈祷体”或“颂歌体”。祈祷被看作是“人关于上帝的谈话的唯一恰当的形式”⑦,也是宗教最基础的一种心理行为,蒂里希认为:“祈祷的本质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做工作并把我们的整个存在提升到上帝身旁的一种行动”⑧,祈祷和赞美是人对所敬仰对像的尊重和崇敬行为,在神学那里是人与上帝间的亲密互动,上帝的绝对存在,人的孤立无助,世界的怕和畏都在人的祈祷和赞美里实现了超越。人在祈祷里有了信心和希望,有了敬畏和崇敬心理,但人不能被紧紧拴在敬畏上而迷失自我。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就有祈祷的诗体特点,她这样写道:“我不会弹琴,/我只静默的听着,/我不会绘画,/我只沉寂地看着,/我不会表现完全的爱,/我只虔诚的祷告着。”(《春水?98》)她还写有著名的《晚祷》诗,如“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它/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永远在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灵。”这是典型的祈祷诗,她对上帝发出了呼告、赞美和盼望,把自己贡献在上帝的座前。冰心在20年代初所作的组诗《圣诗》的形式就是祈祷体,可以说,冰心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有祈祷和赞美诗风格的典型代表。祈祷常常与赞美和忏悔联系在一起,祈祷诗也是赞美诗。赫舍尔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秘密在于称赞的能力”,而“我们时代的人正在丧失赞美的能力。他寻求的不是赞美,而是逗乐得到快活。赞美是一种主动状态,是表达崇敬和欣赏的行为。得到快乐则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它是接受有趣的行为和风景所提供的欢娱。得到快乐是一种消遣,是把思想注意力从日常生活的事物中转移开去。赞美则是一种正视,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行为的超越性意义上。”“赞美就是乞求上帝从隐蔽处出场”⑨。冰心赞美“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人呢?——/上帝呵!我称谢你,/因你训诲我,阿门”(《圣诗?夜半》)。梁宗岱的《晚祷(二)》则有很浓的忏悔意识:“我独自地站在篱边。/主呵,在暮霭底茫昧中,/温软的影儿正开始他野蔷薇底幽梦。……/在黄昏里忏悔底温光中/完成我感恩底晚祷。”⑩
祈祷也是精神的献祭,如同“羔羊”对“牧者”的期待。王以仁的《读<祈祷>后的祈祷》是一首有着完整结构的祈祷诗,“我跪在主的前面,/深深叩拜——”“造物主啊:/我现在不再有什么要求,/只有深深的忏悔:/我不愿像那无依的浮云,/东西漂泊,朝暮变幻;/我不愿像那无赖的狂风,/扰乱这和平岑寂的空气;/我不愿像那无限的溪流,/凄凄潺潺地向着下方飞奔;/我不愿像那团团的明月,/寂寂地随着地球旋转。”“我要化为一只翠羽的飞禽,/带了我主的福音,/用婉转的歌喉——/去安慰劳苦的农民,/去解除工人们的烦懑,/去唤醒沉沉如梦的人生!”“我将披着静谧的衣服,/戴着月桂的冠儿,/胸中怀着——雪一般的洁白,星一般/的灿烂,火一般的热烈,电一般的/光华的心儿。/去遮没宇宙的污浊,/照耀着未来的光明,/融化了冰冷的人生,/打破层层障碍。”11他从呼唤“主”开始,接着就发出一连串的“忏悔”和祈祷,把自己如一本书那样向对方完全打开。
其他现代作家和诗人也写有大量的祈祷诗,如周作人的《对于小孩的祈祷》、梁宗岱的《晚祷》、陆志韦的《向晚》、闻一多的《祈祷》、冯至的《蝉与晚祷》、穆旦的《祈神二章》、郑敏的《最后的晚祷》和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它们都有祈祷的诗体风格。“祈祷”用来表达人的理想和愿望,有宗教性的祈祷,也有对理想的盼望。周作人的祈祷没有宗教意义,但有上帝意象的文体风格,他的倾诉对像是小孩而不是上帝,“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请赎我的罪吧。/还有我未能赎的先人的罪。/用了你们的笑,/你们的喜悦与幸福。/用了得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矜夸。/在你们的前面,有一个美的花园,/从我的上头跳过了。/平安地往那边去吧。/而且请赎我的罪罢—/我不能够到那边去了,/并且连那微茫的影子也容易望不见了。”(《对于小孩的祈祷》)闻一
多的《祈祷》则表达了对国人和民族的殷切希望,“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郑敏的《最后的晚祷》则相信“在心灵的泥土里布下种子,那总有长成绿苗的一日”12。艾青诗歌有颂歌模式,他的“颂歌体”并不完全是谈论上帝的方式,如《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复活的土地》等,他赞美、歌颂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和火焰,他是时代的预言者和理想的呼唤者。
对上帝的祈祷、赞美、呼告和忏悔也是《圣经》最基本的语言方式,它影响现代诗歌创造了祈祷颂歌体。相对而言,关于上帝想像的诗歌文体比它的思想价值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当然,现代诗歌的祈祷颂歌形式有着多种的艺术资源,传统的诗骚和大赋也有着潜存的影响,《圣经》不过是其中一个艺术资源。祈祷、赞美和忏悔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价值信仰崩溃之后寻求新信仰过程中的迷茫和期盼心理,他们寻找并期待着有一个绝对者能回答或解决自己面临的精神困境。
三 走向神性诗学的可能
上帝意象为中国诗歌创造了新的意象空间和美学意义。中国有“诗禅相通”的诗学传统,以禅入诗,以禅助诗,以禅喻诗,诗中有禅,禅里有诗,禅作为一种认知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立意、构思、风格和审美理论。禅来自佛学又融庄玄,与西方的上帝观截然不同,禅可以是人的一片心境和意趣,可以物化为自然和人事,上帝始终是超越的终极的力量。诗禅可以相通,上帝与文学却界限分明,有不同的意义层面,上帝观念追求终极的、超越的形而上世界,文学有审美的、日常的、形而下的追求,上帝没有审美性,但可以通过影响作家而改变文学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禅可以直接进入文学,它对人生的态度就带有审美艺术的眼光,禅意、禅境、禅味是一种高妙的艺术境界,上帝观念则是审美的超越,是人的终极目标。所以说,禅和上帝具有完全不同的认知理念和话语方式,也产生了不同的审美风格,诗禅相通带给了中国传统诗歌冲淡空灵、优美闲适、隐秀神韵的美学意蕴,上帝意象则使现代诗歌有了精神的转向和紧张,形成了明净而反讽的语言风格。
但是,现代诗人对上帝的想像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神性经验和终极情怀,如同西方诗歌中的艾略特和荷尔德林那样,成为神性世界的守护人,不断追问人与神之间的紧密联系。现代解释学认为,人类的意义解释活动是不同视域的碰撞和相遇。解释需要以自我经验为前提,一定的社会条件构成的“历史视域”都会参与到人的各种解释活动。现代诗歌对上帝的想像也可看作是以诗歌形式进行的一种意义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以及诗人的生存方式都进入了对上帝的想像。也如同麦奎利所说:“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同时谈到了自己。‘上帝’这个词不仅表示存在,而且包括一种对存在的评价,对作为神圣存在即仁慈公正的存在的献身。”13对于现代诗人,甚至是中国诗歌而言,对上帝的想像和意象设置都是一场精神的考验和灵魂的冒险。他们非常熟识自然与历史、社会与时代发生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由此也可自由发挥个人的想像,但对属于超验的上帝的代表则显得力不从心,认知的隔膜和表达的简单使他们无法创造自由而丰富的想像,不由自主地被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经验所缠绕和困守。他们把上帝看作神秘之物,或是当作现实生活的解救者或者是社会救世者,可以帮助人们直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现代诗人急迫需要得到幸福和自由,但想要爱就有爱,要自由就有自由,人生价值被功利化和现实化了,同时也把生命功利化和简化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眼光有着传统实用理性和比兴思维,也有着急促的现代工具理性的渗透,更有现代社会历史客观力量的挤压。现代西方依然把上帝看作意义的创造源泉,是生活的根基和支柱,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启示作用。现代诗歌对属于绝对精神的上帝意象并没有展开自由想像,没有向灵魂深处开掘,穆旦诗歌是相对成功的例证,其美学意义和文化精神不容忽视和低估。
于是,现代诗歌的意义和形式就有了神性意义的诉求和择取,有了上帝意象的创造和想像。从20年代的冰心到40年代的穆旦,现代诗歌从没有间断对上帝的想像,延伸到80、90年代的海子,他试图探索汉语诗歌写作的神性立场,创建现代诗歌的神性诗学。
80、90年代的顾城、舒婷、西川和北村等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丰富的上帝意象。可以说关于上帝的想像逐渐成为汉语诗歌的一种基本意象。具有神性特征的上帝意象在传统诗歌中面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思想板结出现了相当的松动和裂痕,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上帝观念引起了现代诗人的浓厚兴趣,并展开着独特的诗歌想像和表达。
注释:
①张立新:《简论诗经中的上帝》,《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②参见拙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4--112页。
③唐:《徐雉的诗和小说?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④徐雉:《我的母亲》,《徐雉的诗和小说》,第7页。
⑤徐雉:《上帝》,《徐雉的诗和小说》,第47页。⑥许地山:《中国经典上的“上帝”》,《生命》第1卷第9、10期合刊,1921年5月。
⑦海因利希?奥特:《上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⑧蒂里希:《祈祷的悖论》,《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599页。
⑨赫舍尔:《人是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⑩梁宗岱:《晚祷(二)》,《晚祷》,商务印书馆,1924年。
11王以仁:《读〈祈祷〉后的祈祷》,《王以仁选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7页。
12郑敏:《最后的晚祷》,《九叶之树长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13约翰?麦奎利:《谈论上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