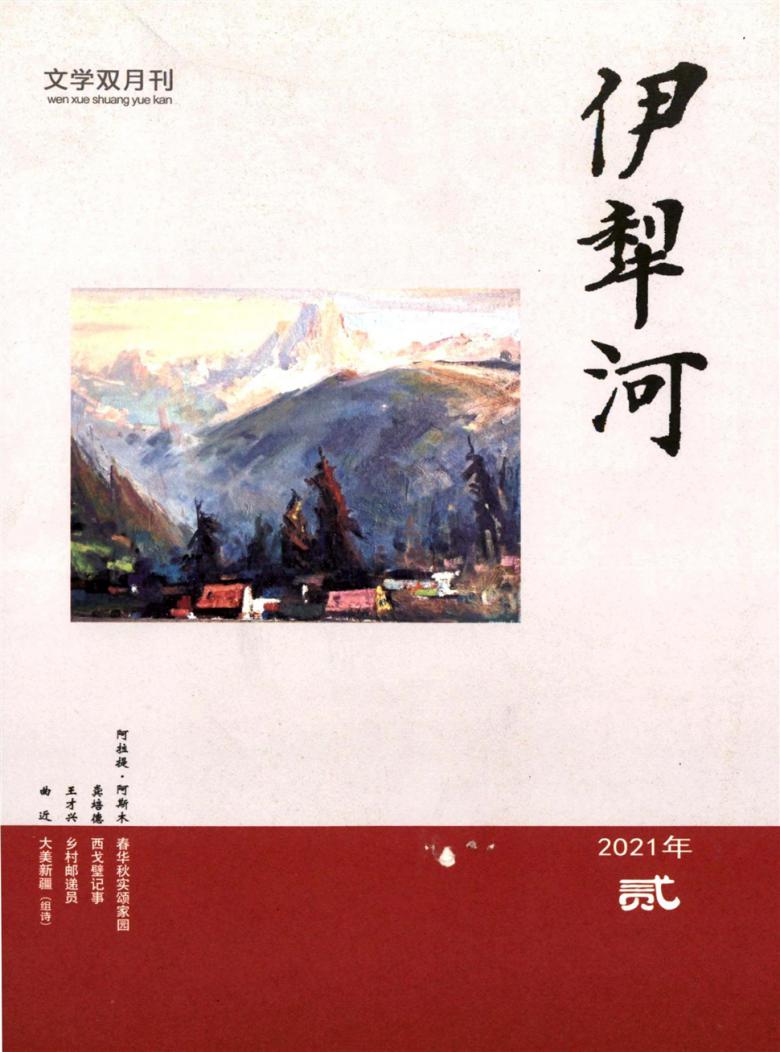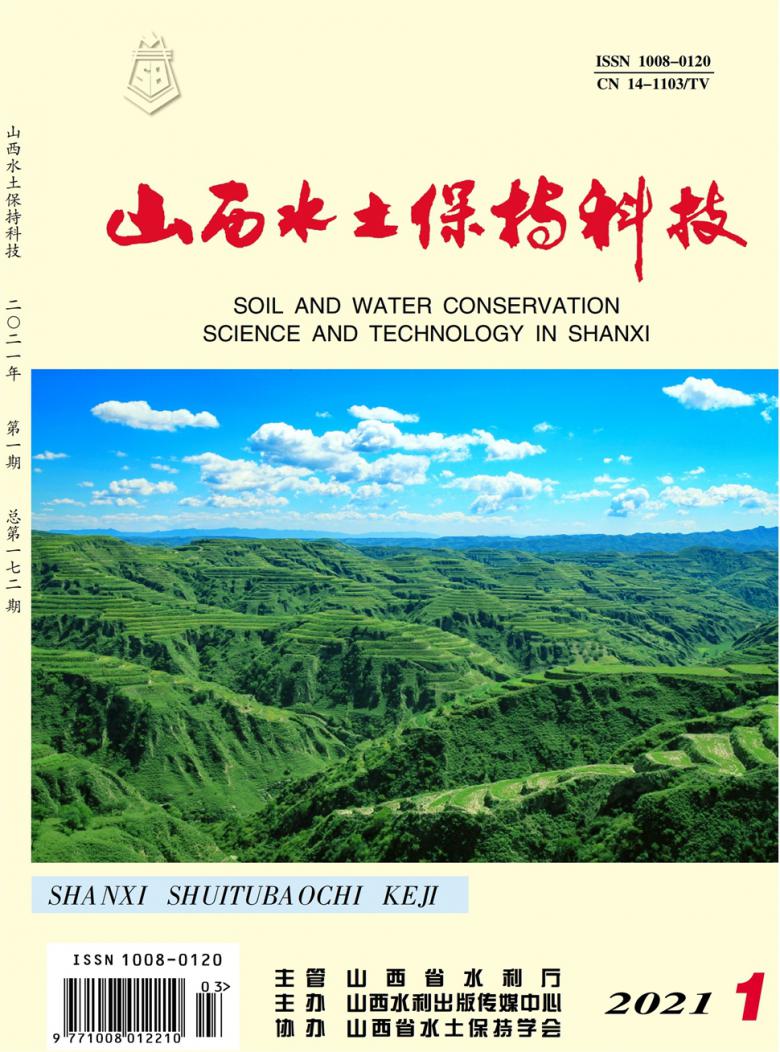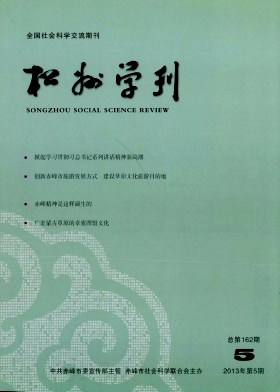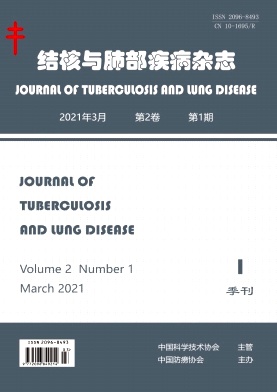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
龙泉明 赵小琪 2008-08-13
当我们回望中国现代诗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时,总能看到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的紧密联系。西方和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现代诗学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建构的重要知识背景。中国现代诗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每向前行进一步都笼罩着西方话语的巨大影响。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影响下,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方法和范畴大都是以西方诗学的观念、方法和范畴等为主干的。不妨这样说,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它的基本指向,就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学话语,实现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在这种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话语不仅作为一种体现了某种先在的强势理论话语形态成为中国现代诗学颠覆古典诗学的内在动力,而且随着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的逐渐深入,这种强势话语也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学自觉建构的体系化结构中的躯体和血肉。我们认为,如果要探寻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未来发展的内在理路,就不能不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而在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诗学几十年的影响中,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尤显重要和深刻,即:诗学观念、诗学思维和诗学风格。就此而论,我们所谈的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既涉及西方话语是如何被中国现代诗学转述与置入的,又涉及西方话语怎样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并在何种意义上使它发生了现代性的转换。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诗学观念的转换。是否承认、尊重诗歌本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持审美的工具论还是目的论,是判别诗学观念现代性或古典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古典诗学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倡导和坚持“文以载道”的诗学观念。在这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诗人心中的内在激情和生命欲求被无所不在的道德律令日趋分割为几无生气的碎片,诗人创造的作品也日趋远离诗人内心的呼唤而成为了虚假、平庸的装饰。与之相反,西方现代诗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诗的独特性和非功利性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从波德莱尔到魏尔仑、韩波,再到马拉美、瓦雷里,都以对“纯诗”的倡导来强调诗的独立性。波德莱尔指出:“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 ① 瓦雷里也认为:“纯诗是一点散文也不包括的作品”,“在一切艺术中,诗也许是要使最多的独立部分或因素相协调的艺术” ② 。波德莱尔、瓦雷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倡导纯诗论的意图,是要为诗的领域划定界限,确立诗学领域的有效原则,正是这种划界和对纯诗的强调,使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学显现出一种奇异的梦幻般的魔力,它点燃了中国现代诗人那渴慕突破“载道”诗学观念的思想火花,激发了他们建构现代诗学观念的生命激情,他们陶醉于对波德莱尔等人描绘的纯诗的那种自由、独立的梦幻般的图景的想象之中,如同在漫漫的黑夜的煎熬中终于盼来了希望的曙光。他们从波德莱尔等西方播火者手中接过纯诗论的火种,开始走上了一条通过纯诗的倡导与古典诗学“载道”观告别的艰难旅程。他们相信,只有在波德莱尔等人构建的这种纯诗王国里,诗的本体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敞开。为此,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对新诗运动初期对诗的独立性地位注意不够的倾向极为不满,发出了“艺术独立”的呐喊,要求改变诗对政治、道德的依附状况和地位,他宣称:“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 ③ 。穆木天则在《谭诗》中,依据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观,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纯粹诗歌”的理论主张。他指出:“我们要求的是纯粹的诗歌(The pure poert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分界。”30年代,纯诗论到了梁宗岱那里有了新的阐释。梁宗岱指出:“所谓纯诗,便是将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绪,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元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纯诗是一个“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④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观照视点首先来自瓦雷里纯诗论的启迪,瓦雷里推崇的诗的纯粹性理论通过梁宗岱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既从文体层面揭示了诗不为他物决定的秉赋与特性,又从艺术层面和哲学层面揭示诗作为存在的构成方式以及存在之为存在的最高境界。40年代,以袁可嘉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派诗人既反对将诗当做与现实绝缘的孤立体,又反对将诗看成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中指出:“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等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如果说梁宗岱对诗的地位的纯粹性的阐述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那么,袁可嘉对诗的地位或特性的阐述就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他对诗歌地位的纯粹性的追求并未单纯着眼于文本层面,而是将诗返回本体与诗人的主体精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论述。
上述不同的诗人和诗论家,当他们接受和转述西方纯诗论话语时,尽管其偏重程度有所差异,然而,他们都坚守了一个波德莱尔、瓦雷里等倡导的现代诗学的基本原则、立场,即以纯粹和审美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强调诗歌对人生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诗歌自身特性的充分敞开上。这样,中国现代诗人和诗论家就在将诗的问题牢牢地系于“纯诗”的基础上时,也在尝试着回答诗是什么命题的努力中赋予了中国现代诗学浓厚的学理色彩。基于 对流行了几千年的“载道”观的反拨,纯诗不仅能突出地折射出他们内在心灵绝对真实的光辉,而且还承担着使他们被现实摧残得晦暗如漆的生命上升到澄明、理想之境的使命。这样,纯诗论就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诗学观,而且是一种哲学化了的诗学观。作为一种诗学理想,它已植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之中,促成了中国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化。
其次,是诗学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转换。我们知道,导致不同诗学之间相异的根本性的要素不只在具体的诗学观念之上,也在把这些具体的观念或成分组合起来的思维之上。在西方话语的影响的实际发生过程之中,最深刻、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往往来自诗学思维层面上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学只有注重从诗学思维层面去转述西方话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才会是真正持久的、有效的。因而,总结中国现代诗学接受西方话语的影响,不但要注重中国现代诗学如何转述西方的诗学观,也要分析现代诗学以何种层面来选择、转述西方话语,由此把握西方话语给中国现代诗学带来的思维的结构性嬗变。
一般来说,诗的本体的确立总是要求建立起一种与之相应的诗化哲学。在西方现代诗人眼中,诗和哲学是相互贯通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同是人类精神的器官,同是认知世界的有效方式,因而,诗不仅不应拒斥理性和普遍性的概括,反而应在自己的大地上搭起一架神秘的云梯,接通理性的天国。于是,西方诗人、诗论家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冲动。从波德莱尔开始,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大都较为重视理念等知性内涵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波德莱尔在《异教派》中强调指出:“任何拒绝和科学及哲学亲密同行的文学,都是杀人和自杀的文学。”艾略特对那种只会唤起读者情感的浪漫主义诗极为不满。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所以他特别强调诗歌“非个人化”,即注重诗歌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知性表现。在艾略特看来,诗人在创作中“知性越强就越好,知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 ⑤ 。当我们在解读艾略特等现代西方诗人的这些对知性强调的论述时,我们一方面深深感到了知性对于诗与诗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思维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超出西方传统诗学那根深蒂固的逻辑思维模式的制约。西方人那种喜欢按一种理性思辨方法去进行思维的意识已经化入了波德莱尔等人的骨髓里,使他们总想通过逻辑推理从杂乱的世界中把握出它的发展规律。理性就像上帝和灵魂一样,盘旋在西方的思维上空,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科学的认知精神的光芒,它照亮的是诸如知性、理念、理智等诗学概念和范畴。
与西方诗学重抽象的逻辑和系统的演绎推理不同,中国古典诗学以直观、领悟、体验为基本的思维方法。客观地说,中国古典诗学中不是没有形而上哲理,但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诗学家孜孜以求的对象。如道家的“道”,指涉的本是宇宙和生命的本体,但道家却并不对这个本体存在为何存在的形而上学理进行富有思辨性的考察。从根本上说,中国诗学感悟思维关心的不是某种终极价值的根据,或理性的认识结果,而是自我的内在情感体验。“诗言志”、“诗缘情”论就充分地显现了这一诗学思维的非理性特色。
随着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影响的逐渐深入,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审美思维方式引起了诗人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好诗不只要在情感上打动人,它还要能带给人知性层面的触动和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于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诗学以一种较为自觉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对于诗的知性和思维方法的现代性追求。
现代主知诗学的源头,可追溯到“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哲理小诗。但这类诗虽表现了一些琐碎的哲理意绪,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诗哲品格。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现代诗学对知性的自觉认同和追求,是从30年代的诗人那里开始的。30年代较早介绍西方知性理论的是高明。他在翻译日人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中对英美现代派的主知理论这样阐述道:“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智(inte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这种主知的方法论”“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随后,英美现代派的知性理论,尤其是艾略特的玄学思辩为特征的知性诗学获得了30年代现代派诗论家、诗人叶公超、金克木、卞之琳等人的高度重视。
对于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诗论家来说,引入和转述西方的知性理论话语,其意义不仅在于对 传统的感悟思维模式的突破,而且也在于对从“五四”以来坦白奔放的浪漫主义诗学话语的反拨。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一文中,金克木就借鉴了艾略特的经验论和瑞恰慈的综感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智诗”的主张。他强调指出,主知诗与主情诗不同,它以智为主,“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沉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但金克木又反对将主知诗完全等同于旧的说理诗或哲理诗。在他看来,主知诗必须是情智合一的。这种情与理统一的观点,与艾略特、瑞恰慈的情感理性平衡说极为切合。在其根本上把握住了西方知性话语最本真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金克木在转述西方知性话语时,还努力从更为深入的层面去理解知性诗产生的根源:“近二三十年来新科学的突飞发展,将使人类思想起巨变,现代政治经济等的混乱与矛盾影响到文化的急剧变化与驳杂,使现代人的心理与人生观有了极大歧义与动摇”,这样,“新诗人若要表现新人生就不能漠视其所处的环境,不能不对周围的人事有分析的认识和笼括的概观”。金克木在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到中国现代诗学为何在30年代注重知性的背景事实。它提示我们,对于3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学来说,重要的其实不仅是西方知性话语进入中国诗人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使西方知性话语进入视野的同时也使视野本身得以显露。西方知性话语之所以在30年代对中国现代诗学构成实质性影响,一方面缘于这种知性话语与情感话语等相比,自有其可取之处和优势基础;而另一方面,则又缘于此时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40年代,西方知性话语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转述和阐释。这一时期,西方的知性话语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内涵上都获得了充分的展开。我们既能在袁可嘉、穆旦的主知诗论和诗作中看到艾略特玄学思辩论的深刻影响,又可在冯至、郑敏等人的主知诗论和诗作中发现里尔克主知论的影响。这其中,尤以袁可嘉对艾略特、瑞恰慈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的主知话语的转述和阐释最为突出。之所以是突出的,是由于它已融入了袁可嘉对主知这一理论问题进行追问的独创性意识。当袁可嘉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理论时 ⑥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中“玄学”一词在基本意义上与艾略特推崇的玄学派中的“玄学”含义的一致性,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对新的诗学思维和体系的寻求与建构的冲动。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创造性冲动,围绕着“现实、玄学、象征”这一理论圆心,袁可嘉构建了一个以张力、机智、悖论、辩证性等概念和范畴为经纬的诗学系统。至此,西方知性话语在不断的被转述中才消除了西方话语陌生的他性,真正化为了中国现代诗学架构中的血肉 ⑦ 。
再次,是诗学风格的转换。风格是诗体呈现的最高范畴,是诗歌文体形式趋于成熟的标志。但诗学风格关涉的又不仅仅是文体问题,它又与意象、象征暗示、通感等诗学法则以及诗人的诗学观、诗学思维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对中国诗学由“朦胧”向“晦涩”诗风的转换的考察,又必然要从对意象、象征暗示等诗学法则的变化的分析入手。
不可否认,意象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核心性范畴。意象意境化,则被中国古典诗学视为诗歌意象的最高品格和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典诗学这里,诗歌表现的意境不管怎样朦胧,它都是建构在人与自然和谐圆融基础之上的。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构成了中国古典意象意境化的诗学风格的本质特性。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观和意象体系受到了西方话语和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冲击。象征性意象取代意境化意象成为了现代诗学中意象的最高品格,与此相关,矛盾性、动态性、审丑性的意象也取代了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意象而成为了现代诗学中的主要审美构成和结构方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诗学风格由朦胧向晦涩的转换。
这种由追求意象的意境化到追求意象的象征化导致的诗学风格的晦涩,从更为宏阔的背景上看,一方面源于现代诗人立足在一切都裂变成了碎片的现代沙漠中,已经不再相信古典诗学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乌托邦之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话语的影响有关。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和自然世界都是不真实和丑恶的,唯一真实的只有人的内在世界。而要表现人的隐秘的内在世界,就不能不用隐秘、晦涩的象征和暗示。因为只有隐秘、晦涩的象征才具有一种暗示的神力,才能最为深刻地表现人的内心深处那些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情绪波动和千回百转、转瞬即逝的欲望。波德莱尔反对诗意的直白浅显,认为诗应该 “有一点模糊不清,能引起人的揣摸猜想” ⑧ ,为此,他主张诗歌大量采用象征与通感。马拉美在《关于文学的发展》中说,“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应该有某种隐秘的东西,我断然相信某种晦涩的东西,其意义是密封的、隐藏的”,而要表现这种隐藏、晦涩的东西,就不能不用晦涩、隐秘的象征和暗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马拉美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对晦涩、象征等的强调,是建构在对现实主义摹仿自然和浪漫主义歌颂自然诗学观的反拨基础上的。在他们这里,晦涩以及与此相关的象征、暗示等问题不仅可以突出地折射个体生命的内在世界的隐秘的悸动,而且实际上还引导着个体生命在最为本源意义上对宇宙奥秘的把握。这无疑是一种哲学化了的晦涩观。这种哲学化了的晦涩观,总是对那些被现实压抑、折磨而企求解脱的诗人充满着诱惑。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派的晦涩诗风就十分推崇。他认为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 ⑨ ,他看来,诗“多少是带有贵族气息的”,并非人人能懂,“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 ⑩ 。穆木天认为诗歌关注的焦点不在外在世界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而要表现这个“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11 的。30年代,朱光潜更是依据心理学知识公开为晦涩的诗风辩护。他以法国象征派诗歌为阐释对象,将晦涩与诗歌的特殊想象力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进而认为,晦涩是一种“不能用理智捉摸的飘忽渺茫的意境和情调”12 。梁宗岱在阐释他的纯诗系统论时,以融合中西诗学的广博知识,跨越了中西诗学话语的鸿沟,将诗的晦涩与象征、想象力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对晦涩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在他看来,象征不是一种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比”相似的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可以使我们“渐渐沉入一种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这样,当梁宗岱将象征看作一种文学的存在方式时,象征导致的晦涩就已经不仅仅是语言表现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诗学观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我们认同象征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力这样一种界定,我们就无法否定晦涩在诗歌中的重要审美功能。
40年代,袁可嘉对晦涩的系统阐述,更是标志着晦涩作为一种诗学风格的价值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真正确立。在《诗与晦涩》一文中,袁可嘉不仅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肯定了晦涩是一种现代诗人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的特殊法则,又从思维层面上否定了晦涩等同于思维不畅的观点,指出,“晦涩是西洋诗核心性质之一”,同时,是“现代诗人的一种偏爱”。当晦涩被袁可嘉由修辞上升到诗人的审美趣味,再由诗人的审美趣味上升到诗学观时,我们已经明白,尽管晦涩为阅读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但它却在坚持了诗的本位立场的同时,保持了诗歌的一种非常纯粹的品格和极为高雅的姿态。从整体的视野上看,仅仅只是修辞或是审美趣味的晦涩,它所唤起的只能是陌生的神秘感,只有这些要素整合成一个系统显现的诗学风格的晦涩,它才能使我们面对一种近似于空旷渺远的诗的空间,此时,我们体验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神秘感,而且,也可能是一种渗入天地宇宙的大神秘。这,便是晦涩的诗学魅力和晦涩诗学风格的价值所在。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在回顾中国现代诗学这段历史,目睹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学发生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换时,他都不能不承认,这段诗学发展史不仅不是被西方话语逐渐淹没、自我话语完全丧失的历史,而且是一段由聆听、转述西方话语再到主动发问的历史。我们认为,对历史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是容易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理解现代诗人、诗学家们当时选择的历史合理性。上个世纪之交,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衰竭双重力量的挤压下,中国诗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自身诗学话语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而除了借西方现代形态的话语来实现自身诗学的变革以外,别无其它选择。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得力于对西方话语的聆听和转述,中国现代诗学才能创造性地发展自身。如果没有西方话语的引入和创造性接受,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立发展与建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诗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也近乎痴人说梦。历史已经进入到新世纪,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接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历程之后,中国诗 学与西方诗学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为中西诗学的交流、互补与独创提供了可能。双方尽管仍存在着落差和不平等,但只要中西诗学能以开放的心态坚持互为主体、互为补充的长期对话,在对话中不断探讨一种能够跨越双方诗学的新视域,寻找双方面临的共同的诗学话题,那么,中国诗学就会在双方对共同诗学问题追问的视界的互动、转让活动中,在坚持了独立、自由精神的同时,扩展自己的诗学视野,强化自身的现代性特质和品格,开创世界性与民族性为一体的诗学体系与格局。
注释
①波德莱尔;《论泰奥菲尔·戈蒂耶》,《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瓦雷里:《诗》,《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③李金发:《烈火》,《美育》1928年第1期。
④梁宗岱:《谈诗》,《人间世》1934年第15期。
⑤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页。
⑥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⑦此部分观点,可参见龙泉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四十年代的调整与转化》,《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
⑧波德莱尔:《随笔·美的定义》,《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
⑨李金发:《艺术之本质与其命运》,《美育》1929年第3期。
⑩李金发:《卢森著〈疗〉》,引自《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1穆木天:《谭诗》,《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12朱光潜:《心理学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大公报》193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