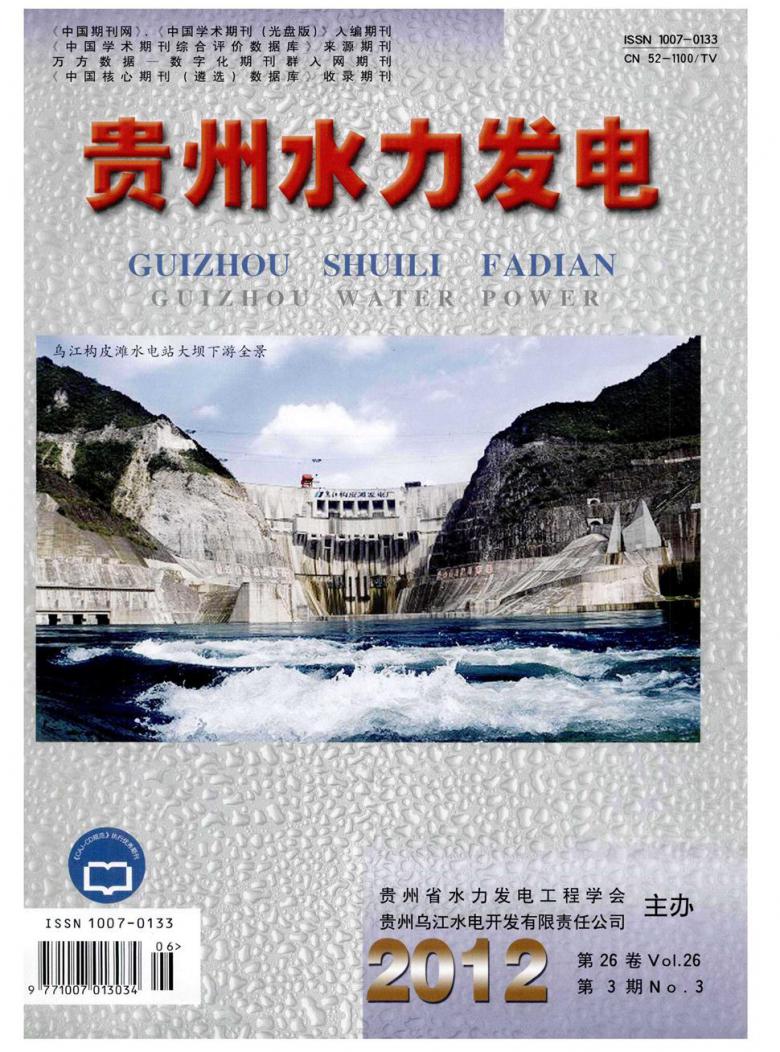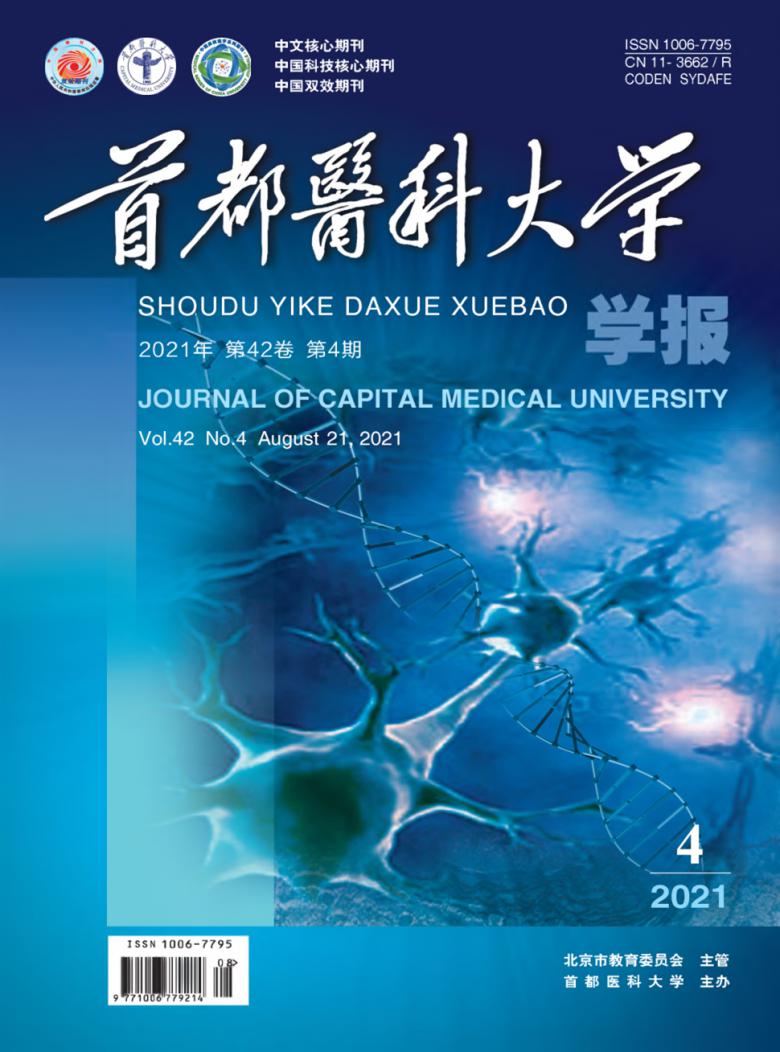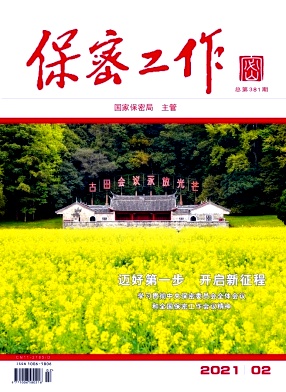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施蛰存——为纪念施蛰存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杨迎平 2008-07-09
【内容提要】施蛰存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世纪的历程,施蛰存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他的“独辟蹊径”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创造了一支中国的现代派,使中国现代文学走出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蛰存长达六十年、近一千万字的外国文学翻译,不仅仅使他的现代主义创作有了广泛借鉴和参照,更重要的是,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借鉴和参照,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因为它的兼收并蓄和开放现代而成为中国现代杂志之最。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正 文】 今年12月3日是施蛰存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施蛰存在诞辰98年的时候匆匆的离我们而去。留下整整一年的时间给我们思考。施蛰存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世纪的历程,施蛰存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他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对现代派文学的推崇,创造了一支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使中国现代文学走出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蛰存长达六十年、近一千万字的外国文学翻译,不仅仅使他自己的创作有了广泛的借鉴和参照,更重要的是,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借鉴和参照,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因为它的兼收并蓄和开放现代而成为中国现代杂志之最。
一
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创造并培植了一个中国的现代派。这一方面指他在创作上“独辟蹊径”的运用了心理分析创作方法,一方面则是他通过主编的杂志培植了中国的现代派文学。 施蛰存在1933年5月总结他近十年的创作历程时写道:“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注: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在左翼文学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施蛰存的“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和创作实践算是一个异端,施蛰存的可贵之处,是他的求新求异、不随大流的性格特征,和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独辟蹊径的执着精神。施蛰存对文学的追求,注重艺术的探索,重视文体的尝试,他说:“倒也不成为一种主义,不过一个小说家都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注:施蛰存《一人一书(下)》,《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他不同意把文学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他认为“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是不免把文学当作一种专门学问了。有这种倾向的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说。”(注:施蛰存《“文”而不“学”》《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382页。) 所以当人们在作品中表现“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时,施蛰存却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情有独钟,施蛰存最初是看施尼茨勒的小说,“看了显尼志勒的小说后,我便加重对小说人物心理的描写。后来才知道,心理治疗方法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我便去看弗洛伊德的书。”(注: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第175页,第17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之后是将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性变态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施蛰存在与我的通信中谈了当时的创作情形:“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注:施蛰存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信。) 这种“不宁静情绪”就是潜意识的外在体现,是“创伤的执着”(弗洛伊德语)而形成的幻觉。受潜意识的支配,主人公的举止就不是常态而是变态。施蛰存说:“我经常感觉到,一个人往往因为一种心理,或一种潜在意识,把眼前的,近的东西看成远的东西,把一个静的东西看成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很多,但是一般人没有注重到。”(注:施蛰存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信) 施蛰存是努力发掘潜意识的隐秘。
对性变态的描写,施蛰存与弗洛伊德也有相通的地方,弗洛伊德认为性变态的人数多寡虽难估计,却绝不会太少。施蛰存也说:“都市的人,现代的人,你知道,一个青年一定是好色的。”(注:施蛰存《花梦》,《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施蛰存不仅历史小说如《现代》杂志的《书评》所说:“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而且他的绝大多数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同样是写色欲,并且多是变态的色欲。 这样,就有人说施蛰存的小说“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注:《现代》杂志一卷五期的《书评“将军底头”》。) 其实也不尽然。施蛰存与弗洛伊德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是有着本质分歧的。如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泛性论”便是施蛰存不能认同的。施蛰存的小说中绝没有“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唯心理论的体现,施蛰存小说中的性变态源于灵与肉的分离,与社会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否认理性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和地位,中国三十年代缺乏西方社会那发达的近代理性哲学和现代反理性哲学的文化传统。中国当时各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使人们普遍感到惶惑和不安,人们渴求理性而不是拒绝理性,施蛰存不仅自己在创作中布满着理性,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受到理性的制约。不论是古代高僧鸠摩罗什,还是现代女性卓佩珊夫人,虽然他们的内心有着翻江倒海的性需求、性欲望,但他们受到理性的克制,一个个都是谨慎小心的痴情人,传统的道德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施蛰存对现代主义的运用,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谨慎、保守,适可而止的姿态。这便使他与刘呐鸥、穆时英的放纵抒写有了区别。再者,西方现代主义具有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烈拒绝和反叛的特征。施蛰存却始终没有拒绝和反叛现实主义,他其实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注: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施蛰存的现实主义特征首先表现为对真实的推崇。他很欣赏梅里美的一句话:“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注:施蛰存《乙夜偶谈·真实和美》《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施蛰存说:“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注:施蛰存《乙夜偶谈·真实和美》《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当然,施蛰存力求表现人物心灵状态的真实。其次,施蛰存的现实主义特征还表现为崇尚写实主义精神。他尽量避免西方现代派小说那种捉摸不定的飘忽感和煞费周折的晦涩感,“能够很熟练地运用中国所有的笔致,保存其简洁明净,而无其单纯和幼稚”(注:《现代》杂志一卷五期的《书评“将军底头”》。),力求通俗易懂、明白畅晓。施蛰存说:“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注:施蛰存《关于〈黄心大师〉》《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当然,施蛰存追求的写实主义与传统的写实主义还是有所区别,施蛰存是将幻想与写实相辅相承地融汇在一起的。施蛰存曾于1932年9月在《现代》一卷五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华的评论文章《茹连·格林》,极力推崇格林的幻想写实主义,说:“在他的著作中的情节,都是从他的想像中得来,而凭了他底心智结构成功的。但是,这里不能忽略的,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写实主义者。”施蛰存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还表现为他不在小说中编故事,他是在小说中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个人格。以一种极艺术、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心理的现象。
施蛰存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左翼作家的批评。楼适夷说他的作品“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注: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33期1931年10月。),钱杏邨说其作品“是证实了曾经向新的方向开拓的作者的‘没落’”。(注:钱杏邨《1931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2卷1期1930.) 其次是读者阅读需求的制约。大革命后,大众中产生了一种忧虑情绪,左翼文学的出现,使他们有了精神的依托,他们在左翼文学中找到了思想共鸣和生存的出路,有很多人是看了蒋光慈的小说而参加革命的。这些读者,在思想内容上,热衷左翼的革命小说,而不关注施蛰存的小说。鲁迅当时就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1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是一种民心所向。这种趋势使左翼文学必然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导致读者排斥一切非革命、非左翼的文学。在艺术表现上,当时的大众读者习惯了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对施蛰存的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时空颠倒,怪诞魔幻的手法或者看不懂,或者不适应,非凡是当他们将文学的政治内容放在首位时,便不关心其艺术创新,施蛰存说:“他们看这种文学书,似乎永远不会觉察到故事之不近人情,人物描写之枯燥呆滞,风土叙述不符事实,……这种种一般小说读者所以为最不可恕的缺点,他们只要能够从这小说中得到一种实际上是很肤浅的意思就引为满足了。这里所谓意思,对于这一派读者大概恒是一种政治性的指导。”(注:施蛰存《“文”而不“学”》《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382页。) 读者的这种阅读需求造成施蛰存内心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各方面的阻力,没能改变施蛰存“独辟蹊径”的决心,他说:“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注: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正是施蛰存的这种执着精神,使现代派文学在1930年代已初具规模。 施蛰存的意义,不仅仅是他身体力行地创造现代派小说,而是利用他的编辑身份积极推崇、热情培植现代派文学。施蛰存与朋友一起办了“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和“东华书店”等书店以及《兰友》、《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文艺风景》、《文饭小品》等多种刊物,因为是同人杂志,当然主要刊登现代派作品。《现代》是综合性刊物,在此培植和推崇现代派,影响就大多了。如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就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包装出来的。在《现代》之前,戴望舒的诗都是散发在不同的刊物上,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重。后来由他们自己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一个诗集《我的记忆》,有点强行推出的意味,施蛰存说:“也是硬挤上诗坛”(注:施蛰存:《〈戴望舒诗全编〉引言》、《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现代》杂志创办后,施蛰存从创刊号起就集中、连续将戴望舒的诗刊发。在此之前,文坛流行的是“新月派”的诗,具有音韵美,形式建筑美和单纯易懂的特征。可以说,施蛰存通过《现代》杂志,发动了一场诗歌革命。因为当《现代》集中推出戴望舒的诗后,很多读者来信说《现代》的诗是“谜诗”,看不懂,于是,施蛰存在《现代》第三卷第四期为《望舒草》做了一个广告,广告词阐明了戴望舒诗的独特性:“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非凡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独白》栏内又发表了一篇《又关于本刊的诗》,指出“《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是一篇关于现代派诗歌的宣言书,从而说明戴望舒的诗是不同于“新月派诗”的具有现代品格的现代诗。《现代》还刊发杜衡的《望舒草序》,进一步说明戴望舒现代诗是对当时流行的明白如话的诗的反叛:“当时通过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心里反抗着。”戴望舒的诗由此引起文坛哗然,情形正如施蛰存给戴望舒的信中所说:“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大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注:施蛰存:《致戴望舒》、《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施蛰存这一次诗歌革命的运作,不仅成就了中国的现代派诗歌,而且奠定了他自己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对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虽然没有像包装戴望舒那样包装他们,但在他们探索新感觉派小说的道路上,施蛰存是起到了要害性的作用的。刘呐鸥与施蛰存是朋友,在创作上他们互有影响,但刘呐鸥是个花花公子,看电影、上舞厅是他的主要生活,写小说是这个花花公子所追求的时尚。施蛰存以他对文学的执着精神,影响着刘呐鸥,不断地将刘呐鸥从交谊场拉回书斋。他们一起办刊物,也是施蛰存做主编,刘呐鸥的小说是在他的策划下形成气候的。穆时英是小字辈,他是在施蛰存、刘呐鸥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也是施蛰存从众多的投稿中发现了穆时英,施蛰存不仅在他们办的同人杂志上大量发表穆时英的小说,而且在《现代》上集中推出了穆时英的十一篇小说,使穆时英一举成名。施蛰存在《现代》二卷一期的《社中日记》中说: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论技巧,论语法,也已是一篇很可看的东西了。”“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可贵的。”
二
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外国文学引进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翻译外国文学,第二、以编辑的身份有计划的大量刊发外国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坛信息。 20世纪初,世界各民族文学在逐渐交流和融合中,外部交流取代了内部交流,世界文学意识日益觉醒。“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最集中,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注: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导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引进而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进程中走向现代化的。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创作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得着一些新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施蛰存的翻译工作几乎与他的文学创作同时开始,施蛰存清楚的熟悉到:“大量外国文学的译本,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地传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应该取鉴于西方文化,来拯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注: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0页,第1329页,第1204页,第1224页。) 大量外国文学的输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一个思想开放、学贯中西的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郑振铎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注:郑振铎《翻译与创作》,《文学旬刊》78期·1923—7—2.) 施蛰存的意义是他终生从事翻译工作,并且是以超前意识和现代眼光搜寻世界文坛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他一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1927年开始翻译《十日谈》,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以及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直到二十世纪末,从事翻译出版工作六十多年。即使是施蛰存被错划右派下放劳动的1950年代,他也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翻译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施蛰存将翻译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挑战。通过翻译,他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距离拉近了。施蛰存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一是引进世界文学的各种文体: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日记、回忆录等等,从而改造和充实中国的文学体裁;二是引进各种创作方法的作品,从而丰富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三是从内容上注重引进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目的在于引进一种斗争精神,从而增强中国文学、中国人民的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