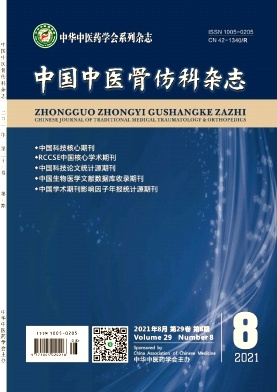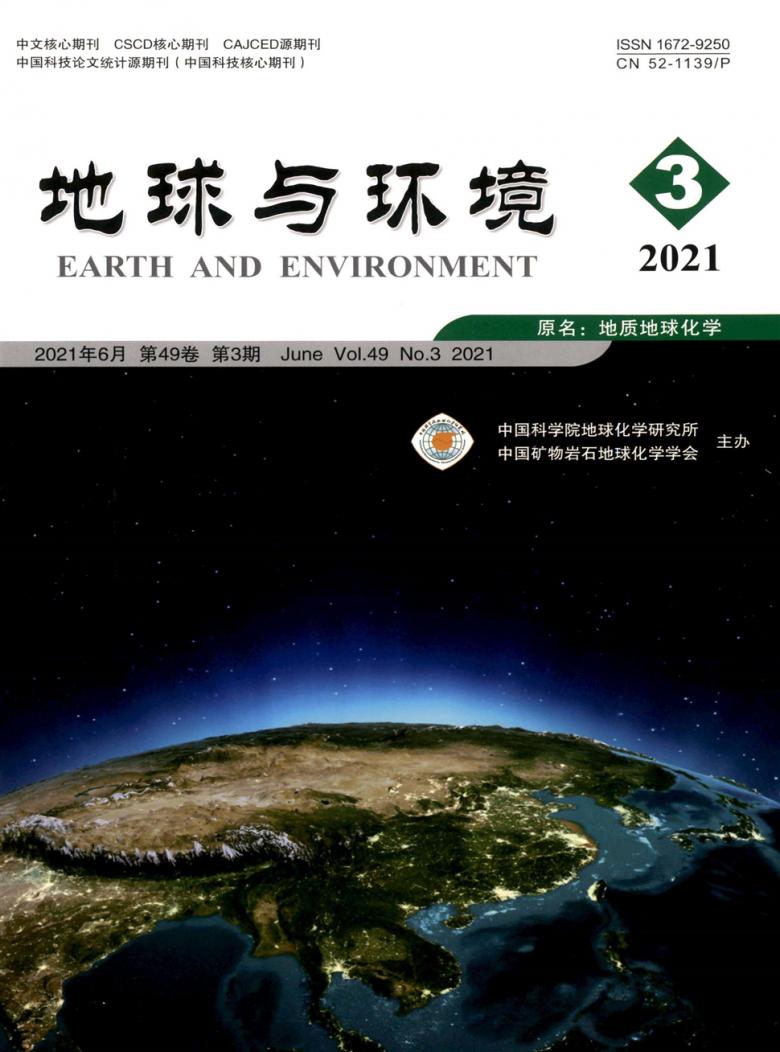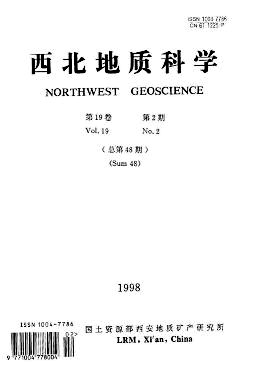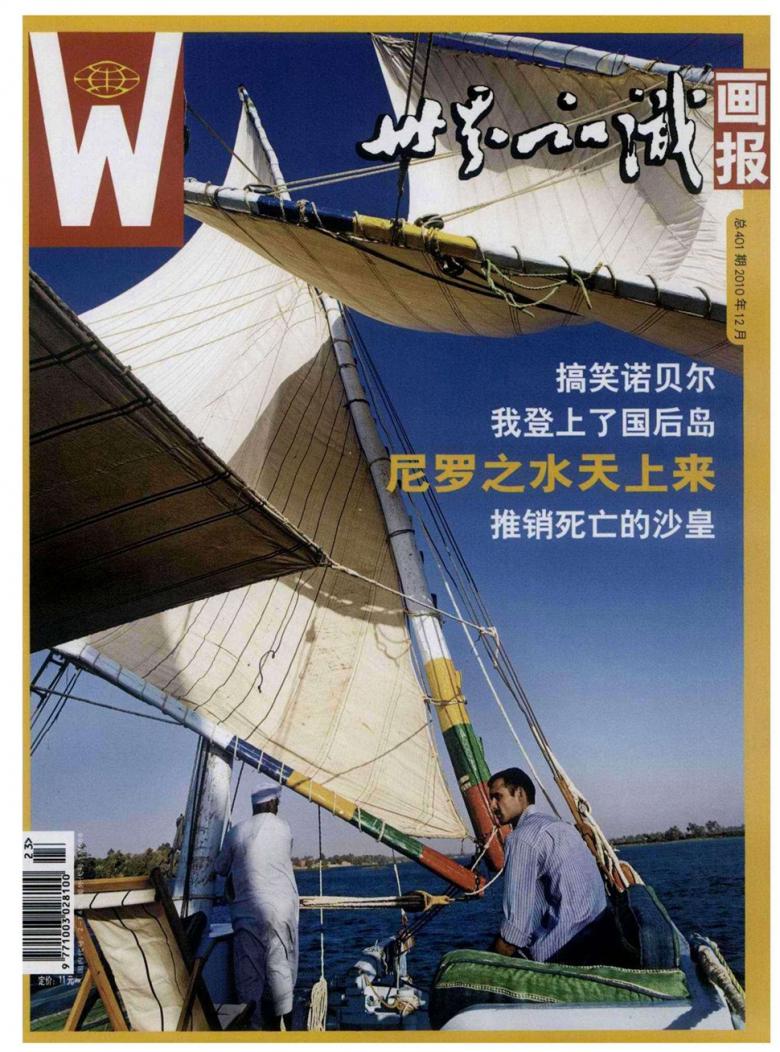中国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佚名 2013-01-12
中国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一、学术研究者的主体性定位 所谓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也就是学术研究应有个“我”在,即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这是听钱理群先生关于《与鲁迅相遇》的讲演之后“进一步”认识的。鲁迅关于“伪士”的论述,非常深刻。鲁迅讲:“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其实就是表达了鲁迅这样一种思想:就算你的那些新说都是正确的,可是因为没有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没有从个人最深切的体验出发,不过是唯顺大势而发声,所以是靠不住的;而且正因为那些思想是正确的、新颖的,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所以,这样的随波逐流者应该称之“伪士”。
对于鲁迅的这一思想,我深受触动。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较为模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疑问,即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作为研究者主体性的问题。虽然说从哲学的意义上,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来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念已经刷新了以“客观”、“真实”为鹄的传统历史学写作,但真正具体到个人的学术研究中,仍然不能很好地端正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似乎已成的“经典”或“定论”来讲。 因此现在重新回过头来阅读鲁迅先生的《破恶声论》,领会鲁迅对“伪士”、对“唯顺大势而发声”、对“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批判,指出“伪士”们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强调“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感触甚深。面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实在也是创造。我们面对研究与思考的对象时,最根本的是要有个人的深切体悟,将心比心,甚至站在对方立场上去体会、理解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时兴的理论、观点,“唯顺大势而发声”。这样从个人切身感受表达的观点,也许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偏颇的;但即使有一点点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所谓“三分学问,七分人品”吧。这在深处的某个点上应该和艺术创作是相通的,正如歌德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我认为是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挥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是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像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给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周作人所谓越是个人的,越是全人类的;正因为是个人的,所以更是全人类的。如果真是能够把学术研究和写作当作是表达自我,寄托个人精神的一种事情,而非其他,那么学术之与人生,也算差强人意了。 二、客观、历史、科学地对待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学术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学术研究都几经曲折,而尤其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有许许多多非学术性因素和影响渗入其中。 针对文革以及文革以前就已存在的极端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及其研究构成的一种困境,80年代的研究者为了打破文学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实,注重和强调纯文学,强调“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等等。老一辈的学者如唐?也呼吁:“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因此才有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现代性”的强调、“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勃起。所有这些在当时是有着非常积极意义的问题,它策略性地表达了那种对政治性压倒一切的反抗,对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自律性的重申和诉求。 但是,我们看到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恢复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同样也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自由主义文学”逐渐凸显成为文学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学则不断受到贬低和排斥,且大有被放逐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之势。80年代这一姿态事实上已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同样的,“20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者钱理群也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当年纯文学概念的鼓励者,为什么现在率先反过来对此进行反思。这是因为它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儿呢?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派,包括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主流派,甚至进入教科书,通过文学它影响了下一代,但这个影响不一定好。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遮蔽、忽略的东西可能给年轻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即是本来“决绝”政治而义无反顾地自愿走上“纯文学”道路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后面对“权力、资本、新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对文学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作用”反而束手无策,这批80年代的弄潮儿和始作俑者突然有了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反思走过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么处理它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当今社会生活的关系?以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是为是,“唯顺大势而发声”,实在和学术自身求真的原旨相违。正如30年代的沈从文当时文坛“差不多”现象所说:“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枝笔,不幸这枝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销,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从60年后的今天看,这段也是“沉痛恳切”的论述,真同谶语无异,因为60余年前的沈从文不仅回顾了过去,阐明了现实,而且竟能预言数十年后的将来,怎不令人叹服!怎不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