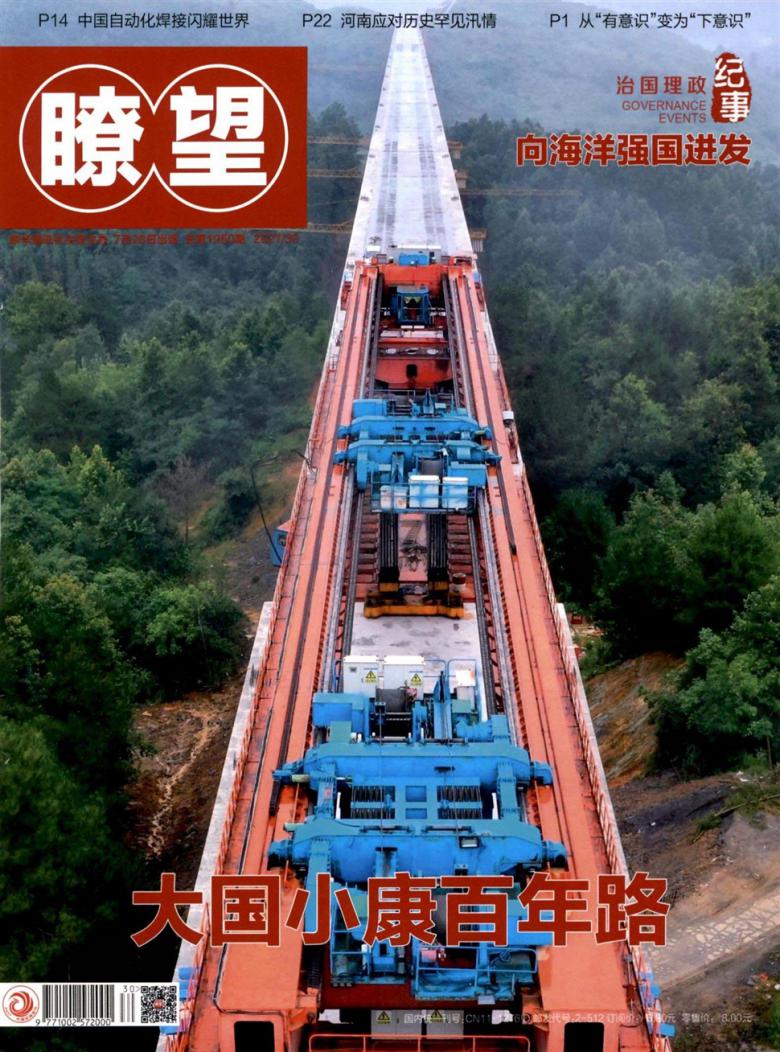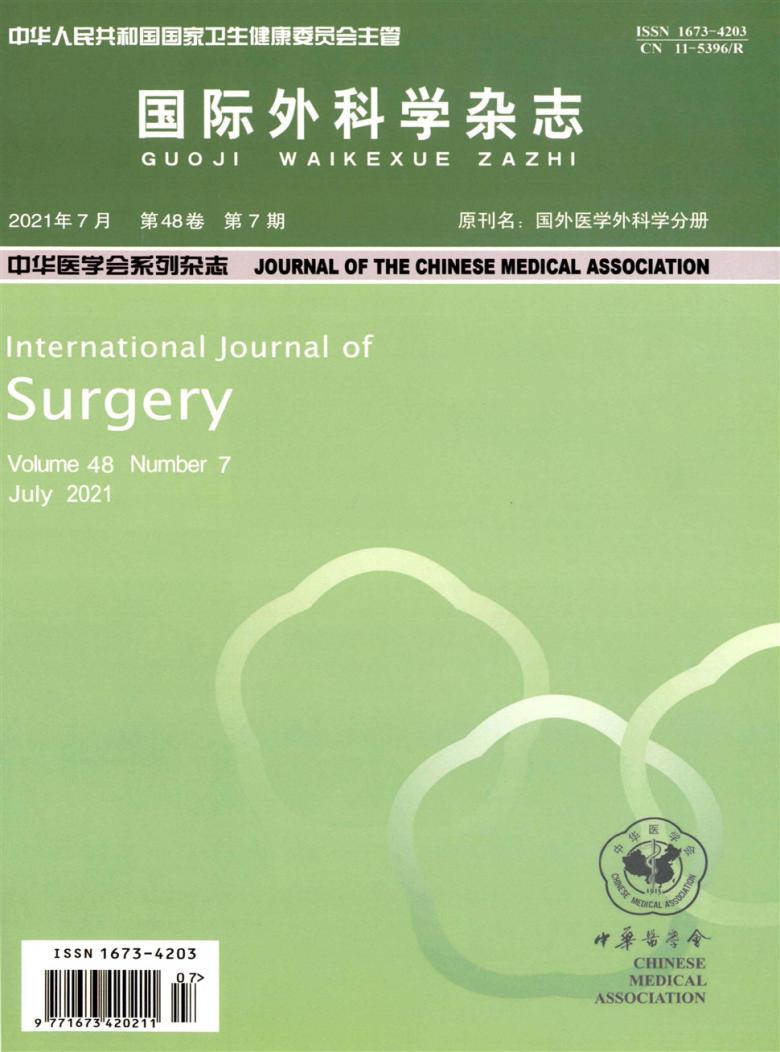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
周晓风
【内容提要】 一
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所谓科学方法的追求早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目标。这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是否有自己适当的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广泛吸收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中国现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的反思势在必行。
有关“现代”(modern)的话语来自西方。因此,要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问题,也应当从西方文学研究说起。按照韦勒克在《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和《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两文中的说法,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的发生,始于19世纪初德国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讲演录》、史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歌德的《谈话录》,以及英国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版序言》和雪莱的《诗辩》等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论文。在这些文论中,对于文学的理解从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再现转移到对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实际上预示着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开始。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发生,则是从现实主义开始的,包括法国作家尚夫勒里185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论文集,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和左拉的《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而且左拉该文算得上现实主义方法的一个典范描写:“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到自然;科学家们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工作的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时候他们的手法便意味着自然主义。相应地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①概括地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实证的方法,而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开始。
此外,韦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还提到,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是科学批评的创建者。这主要是因为圣伯夫的思想深受孔德实证论的影响,着重于对文学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的考察,主张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发掘和研究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可以实证的事实。圣伯夫还在他评论泰勒《英国文学史》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文学研究应该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这些主张在文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按照各自的局限,来应用这个方法;我们这些同一门科学的工作者和服务者,都在争取使这门科学尽可能的准确,因此就让我们继续拒绝那些模糊概念、空泛言词的诱惑,观察、学习和检验那些以不同理由而著称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种情况,以及天才所表现的无限变化的形式。”②除圣伯夫外,西方19世纪文学研究中自觉追求科学方法的代表人物大多都集中在法国,其中最重要的有泰勒和左拉。泰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著有《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泰勒确信这些要素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因果关联,而且人是可以发现和揭示这些关联的。这正是对于文学的一种实证研究。所以,泰勒在西方批评史上实际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他是某种社会学文学论的创建者,二是他也是实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较为自觉的实践者。左拉与泰勒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但也许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左拉在追求所谓科学批评方面比泰勒走得更远。左拉的批评著作最重要的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左拉在《实验小说》中把小说比作医学,并借此表达了一种追求“科学真理的严密性”的理想。左拉试图证明:如果实验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这只是同一道路上的程度问题,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实验小说就是目标。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左拉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类似实验报告之类的东西。上述西方文论对于所谓科学性的追求,反映出近代以来的一种倾向。西方现代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标志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二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印象式的评点方法,也有考据和注释的方法。前者可以说是典型的传统人文主义方法,后者则具有科学方法的某些特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传统的印象式的评点方法发展为现代的科学的批评方法,是一个值得特别加以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致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大约在16世纪,中国学者开始把英文“science”翻译成汉语中的“格物致知”,简称“格致”。直到1885年,康有为在翻译介绍日本文献时,才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中国③。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自觉始于梁启超和王国维。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之所以可以影响人和支配人,在于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他还认为,“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梁启超于是得出结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这些论点不仅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小说提出了要求,而且较为深刻触及到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大大提升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直接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四种力连同其境界说,立足于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说了小说艺术魅力的深刻根源。其理论形态已明显有异于传统文论惯常的感受、思维和表达方式,而偏向于理性的推论与演绎”,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④。
王国维是一位堪与梁启超比肩的现代文学批评大师。按照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说法,王国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王国维在1905年所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还特别提到方法问题。王国维指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1911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还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别。王国维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的特点是情感和想象,因此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看,王国维的方法还掺杂了许多传统的非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后来所作的《人间词话》则进一步回到传统的印象式评点方法。而且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也还不被多数人所了解和理解。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要到稍后的“五四”时期才得到更为自觉的发展。此后,鲁迅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均表现出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逐渐形成。特别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立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大声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别求新声于异邦”,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眼光和现代性视野,成为中国现代早期具有现代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作之一。到了“五四”前后,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蔚为大观,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新的范式得以正式确立,并产生广泛影响。
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追求科学方法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他的《〈红楼梦〉考证》。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的“结束语”中还明确提到他在科学方法上的追求: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据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上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胡适当时所理解的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主要就是指的考据的方法。而且他比较注意把这种考据的方法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方法。但实际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并不限于考据的方法,而是还包括具有考据精神但比考据范围更大也更有宏观性的现实主义实证方法、统计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自觉。一方面,传统的印象批评所采用的体验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仍然被普遍使用,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科学思维的内涵。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更突出的现象是考据的、实证的和系统分析的方法以科学的名义得到大力发展。但这些方法为什么是科学的以及它们对于文学研究的适宜性问题却并未得到认真思考。
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谓科学是与非科学的思想观念相对的。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在古希腊文献中,还没有“科学”这个概念,只有“知识”的说法。大约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来,科学(当时主要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并且率先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实行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于是,所谓精确的科学分析取代了无知的谵语,空洞的玄学变而为实证和推理的方法。有关“科学”的思想和“理性”一起得到张扬,追求科学成为新的时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及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标志,则是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任何门类和方面的知识,其是否发展及其发展的水平如何,均要看其是否符合科学化的方向及其所达到的科学度水平。”⑤这里所说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本来只是就自然科学而言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说法,因此也就自然成为了包括后来新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研究的共通准则。
但是,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事实上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对于自然科学的“独尊”实际上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首先,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在适应的范围上坚持一体化立场,即认为只有一种科学方法,那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和自然现象在形式上尽管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外,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同样的有效性;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这就完全忽视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忽视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特殊关联性,进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性。其次,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在目标的设定上坚持所谓客观性和精确性标准,认为科学方法追求对事物的客观的、完全不受主体影响的认识。但文学及人文学科的特点就在于它属于感受的世界,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精确性作为标准。
因此,近代的哲学家康德提出科学的“划界问题”(即试图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康德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所谓“科学”(自然科学)思想的强势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因此需要给所谓“科学”思想划定一个适当的边界,以确定其有效范围。与之相关,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则提出了所谓“新科学”(即区别于原来的自然科学的科学,也就是人文科学)。维柯把世界分为自然世界、民族世界(即人类世界)和心灵世界(又叫天神世界),认为伽里略和牛顿的数学和物理学都仅仅只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还够不上是完善的科学,只有凭我们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得到科学的认识,只是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内涵与此前的有所不同。维柯所找到的新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是所谓“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象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⑥用传统的科学观来看,这种“诗性的智慧”显然是非科学的。但在我们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有具有自己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虽然具有科学性,却并不等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天然就是科学的,更不可以把特称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等同于全称意义上的所有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应该破除对于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的迷信。相应地,也应该打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科学性的无知和偏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中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方法(如实证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只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如体验的方法)。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和自然学科的思想方法其实都可以是科学的方法,它们是科学思想方法的两个方面,但它们同时也不一定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科学性。如果说自然学科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话,人文学科思想方法的特征则是感受性和可解释性。上述自然学科的和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交错出现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研究变得既新鲜,又复杂。
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追求除前面提到的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实证方法外,现实主义方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关注现实,但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方法有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回到实证主义,用实证主义方法证明作品中的社会问题;一种是在感悟和体验中感受社会问题,同时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两种情况都较为常见。前者可以陈涌的鲁迅研究为代表。后者则可以胡风的现实主义批评为代表。陈涌对鲁迅的研究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研究对鲁迅的基本认识,那就是认为鲁迅的作品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作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提高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认识。这种认识自然有其意义,但多半是文学以外的意义。这种方法有科学方法基础,问题是缺乏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难以更有效地揭示有关文学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方法运用得非常普遍,茅盾、周扬等大都采用这样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相比较而言,胡风的文学批评虽然也是现实主义的,却更具有文学的体验性。例如他的《田间底诗》一文,一开始写他对田间的印象,写他读田间诗作的印象:“我读了以后,不禁吃惊了:这些充满了战争气息的,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底新鲜和印象底泛滥的诗,是那个十七八岁的眼色温顺的少年人写出的么?”⑦胡风进而以诗的笔触描述了田间的诗歌创作歌唱“战争下的田野,田野上的战争”,“他歌唱了黑色的大地,兰色的森林,血腥的空气,战斗的春天的路,也歌唱了甜蜜的玉蜀黍,青青的油菜,以及忧郁而无光的河……。在此基础上胡风得出明确的判断:民族革命战争需要这样的“战斗的小伙伴”!这显然是一种建立在感受基础上的理性剖析。这既是现实主义方法,也是人文学科的科学方法,也正是胡风现实主义思想方法的特点所在。此外,现代文学批评中李健吾和唐等人的理论批评,都不同程度具有这样一种特点。
相对而言,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较难以立足。但袁可嘉写于1946年的《诗与晦涩》一文却是一个例外。袁可嘉本人是诗人,但这却是一篇对于现代诗歌进行科学的语言分析的论文,又是借鉴西方理论分析中国诗歌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该文似乎是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对现代诗歌中的晦涩现象进行系统的辩护。我们在此关心的不只是该文的诗歌立场,更主要的还有该文所表现出的思想方法,即语言分析的方法。无独有偶,另一位90年代诗人臧棣也写了一篇题为《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的文章。该文显然比袁文视野更为开阔,论述也更为深入、全面,所谓科学的分析方法体现得也更为充分。这之中肯定有着某种并非偶然的原因。而在经过80—90年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洗礼之后,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者已经可以把这样的科学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而且不仅是诗歌,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一文从原型结构的角度分析张贤亮的《绿化树》,认为其中的情节和意识都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的“公子落难”的模式,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文学解读。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解读50篇文革小说,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谓科学方法的运用在今天事实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以外,比较的方法、解释的方法等,也都具有明显的科学方法特征。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表现出的非文学性问题也愈益明显,并早已引起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方现代学者加达默尔、韦勒克等早就对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诸多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既缺乏对于科学方法的追求,也缺乏对于科学方法的反思。可喜的是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展开批判性思考。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②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47、20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⑤参见欧阳康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第108、2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第13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⑥维柯《新科学》,[375],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⑦胡风《胡风评论集》,上册,第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