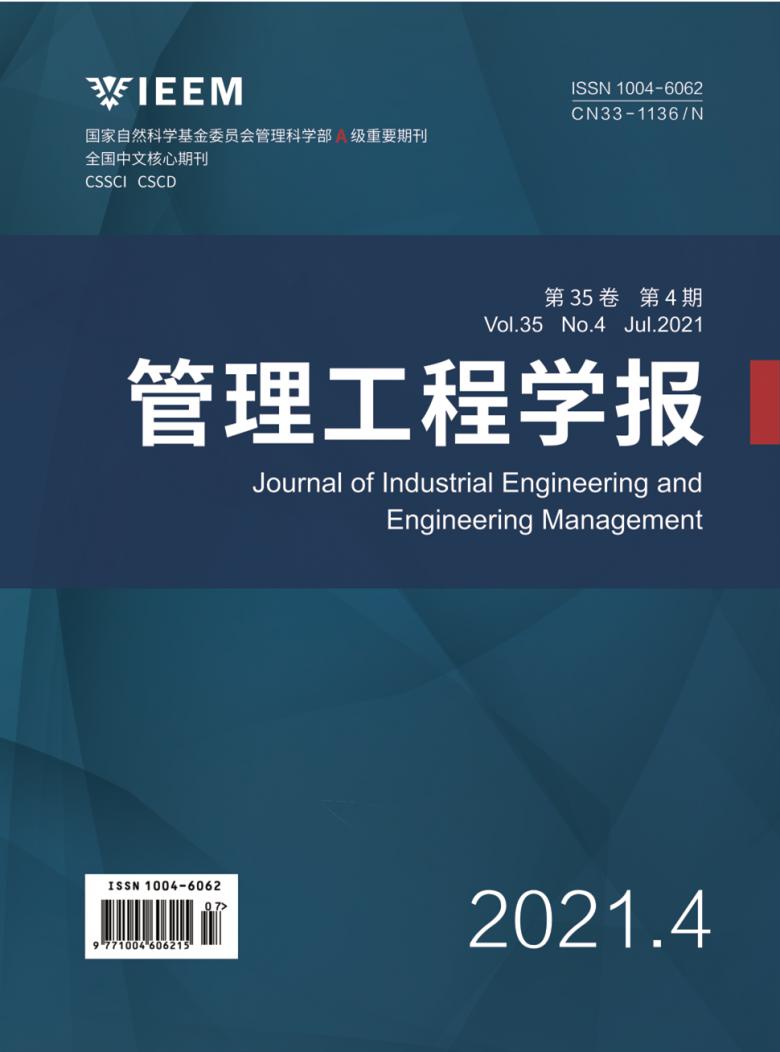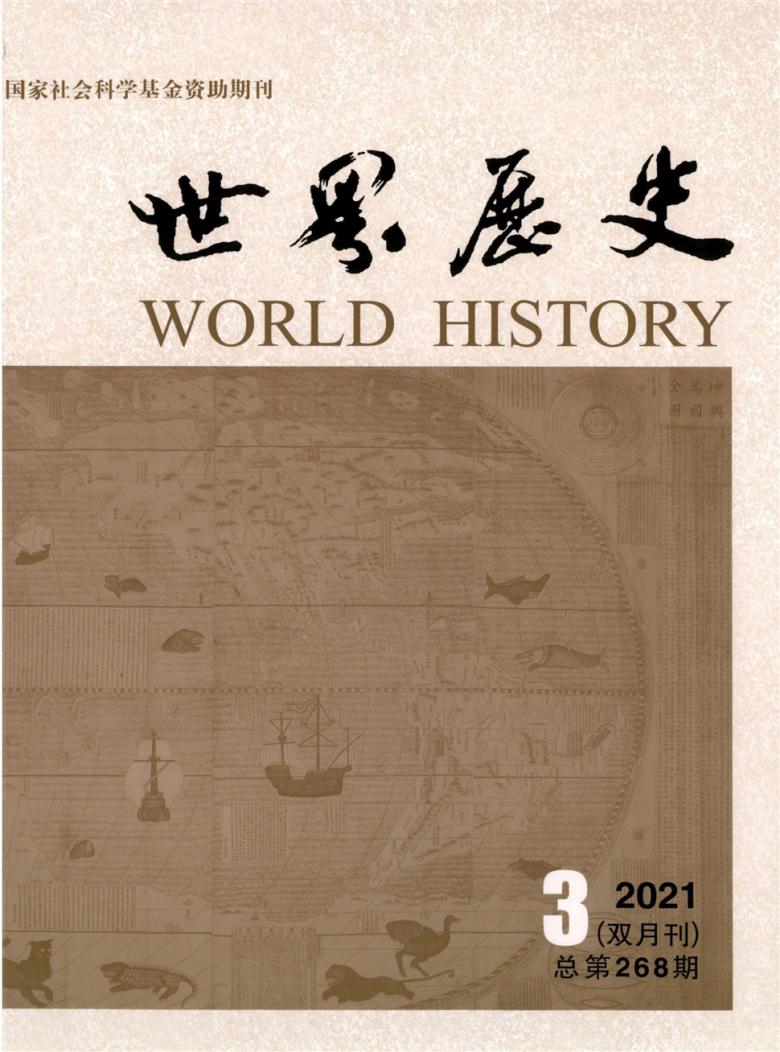审美乌托邦的缺失——试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
米学军 2010-11-17
论文摘要:乌托邦承载着人们的理想、希望,是人们的_一种精神寄托。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普遍缺少的就是这种乌托邦精神,而是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玩弄文本游戏。这种情况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
论文关键词:文学创作;乌托邦;消费主义
“乌托邦”这一概念来自于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发表的名著《乌托邦》(Utopia)。作为一种对美好的社会形态的期望,乌托邦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它是人们的一种希望,一种精神寄托。乌托邦精神表现了人们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是人存在的重要维度。正冈为此,法国启蒙主义学者狄德罗才说:“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美。”英国作家王尔德才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普遍所缺少的正是这种乌托邦精神。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一、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思潮:痞子文学、新写实主义、个人写作、下半身写作、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梨花体……这些现象和思潮的一个共性就是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现在我们看看一些作品的题目,这些作品的题目也许多少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绝对隐私》、《不谈爱情》、《就那么回事》、《曾经堕落》、《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明星那事儿》、《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天亮以后说分手》、《丰乳肥臀》、《妻妾成群》、《非常猎艳》、《上海宝贝》、《暖昧》、《女人床》……正像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文学从展示自己‘裙子’的花哨而殚精竭虑地做着‘媚俗’、‘低俗’的‘擦边球’游戏,继而在众声喧哗中拉开了热闹不休的脱衣秀的风流大幕。从卫慧、几丹到木子美都是脸不红心不跳地做着脱‘裙子’的比赛……这些‘宝贝’在糟蹋文学的‘无’(无境界、无思想、无文笔)的文字碎片中表演着‘什么叫无耻’,并向着人的承受底线发起挑战和冲击。”木子美在《遗情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很久以前,还在大学年级,我就经常为了能冲个舒服的热水澡,在一个男人家过夜,我用了很多他的煤气,还穿他的睡衣吃他的饭,还一夜三次做爱,还不需要跟他恋爱,幸福死了。”对这种放荡的生活,作者在叙述的时候,语气中充满着炫耀、骄傲和自豪,道德、理想甚至尊严在这里都荡然无存了。正如著名文艺批评家陶东风所讲的:在这类作品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不仅无关乎民族国家、党派政治、意识形态(革命文艺),不仅放逐了启蒙,不仅摆脱了历史与文化,不仅与灵魂没有牵连,不仅不通向私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经验,而且遮羞布也彻底撕掉了。”
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时尚。这种倾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出来。1983年,韩东发表了著名诗歌《大雁塔》。韩东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在这里,诗人以冷漠的口吻消解、剥落了大雁塔的文化、历史意义,表现了诗人对宏大历史、对崇高的拒绝心态,诗人所表达的仅仅是个体本身的庸常体验。其后,伊沙的《车过黄河》等作品表现了类似的情感和心态:“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远去/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远去”。
二、玩弄文本游戏
在放弃了崇高、理想和希望之后,游戏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作家追求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了。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玩弄文本游戏、追求写作快感就成了很多作家的创作追求。
从内容方面来看,玩弄文本游戏主要表现在: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描述历史、社会、人生;以游戏、戏虐的态度颠覆传统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游戏、戏虐的态度解构经典名著。从形式方面来看,玩弄文本游戏主要表现在: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拼贴文字,追求所谓的语言狂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说”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和时尚。他们不仅戏说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戏说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正像有的文章所说的:“近年来,国内荧屏戏说成风。明明是残忍的封建君王,却被打扮成消灭战争屠戮、解民于倒悬的‘英雄’;明明是荒淫无度、滥杀无辜的暴君,却以慈祥父亲的面目现;明明是暴虐成性的独裁者,却要给人以勤政为民甚至鞠躬尽瘁的印象…… 近段时间来,戏说之风愈刮愈烈,让人大感惊愕的同时,悲愤感也油然而生。最新的一个恶劣典型是新编小说《沙家浜》,作者将阿庆嫂这个地下交通员描写成既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胡司令睡觉,又做了‘泰山顶上一青松’郭建光的情妇的轻佻下流之辈。在某地所拍的新编电视剧《杨子荣》里,我们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子座山雕‘共用’一个情人,而且还利用这个女人传递情报,最终制伏了众匪徒。某地上演的新编话剧《红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不仅把江姐和许云峰弄成了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人,尤其可恨的是叛徒甫志高,竟神气活现地在舞台上用极为下流的语言调戏被捕的江雪琴。在这种心态之下,传统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颠覆和解构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形式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拼贴文字,追求所谓的语言狂欢也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时尚,这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赵丽华的《紧》:“喜欢的紧/紧紧的喜欢/一阵紧似一阵/这么紧啊/紧锣密鼓/紧紧张张的/紧凑/紧密/紧着点/有些紧/太紧了/紧死你/最后一句/是杀人犯小M/在用带子/勒他老婆的/脖子时/咬牙切齿地说的”。这些作品彻底地打破了传统诗歌语言的内在规律性,作者玩弄文字游戏的心态表露无疑。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家的“‘文字冒险’,固然有实验和追求先锋姿态(创新)的倾向,但也极易演变为玩笑和游戏,刻意追求写作(本文)快感,往往造成语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一旦丧失了语言本身具有的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便极易构成一种对自我的伤害。”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这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渐渐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有关。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它首先出现于20世纪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日本等国扩散,随后便逐渐地向全球蔓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不断浸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消费主义渐渐在我国出现并开始对我国的经济、道德、文艺、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把物质财富的多少、物质生活的享受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联系了起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才是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这种片面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重物质、重金钱、重感官刺激,轻精神、轻灵魂、轻理想、轻人文关怀。这种思潮影响到文学创作,必然导致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娱乐化和日常生活化。
但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文学真地可以不要理想,不要希望,不要精神寄托吗?有的学者讲得很好:“文学说到底,是用来滋养灵魂和守护心灵的,是飘扬在心灵上空的旗帜。除非人真地完全物化而不再有灵魂,否则,在市场中我们固然可以买来物欲的满足,精神的按摩,感官的快感和‘灯红酒绿’,却无法买来心灵的宁静和渴望。恰恰在无关乎金钱或‘资本运作’无能为力的时刻,文学才能驻足心灵深处,使我们感动不已,激情澎湃,精神震颤和灵魂净化。即便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被各种‘复制’和‘生产’的‘审美幻象’所包围并沉醉于其中,人们的心灵被物质欲望和感官欲求所填满,被到处都是的文化商品所淹没,而放逐、荒芜了心灵,使纯文学日益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和‘多余的话’文学也不应被那些所谓的‘码字匠’、‘网络写手’和‘身体写作者’所糟蹋,所贱卖。我们诚然不必固守‘纯文学’的衣钵而自我僵化、固步自封,但文学作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其不可解构的底线。文学有其商品化和引领时尚的一面,但不能像‘裙子’那样为时尚而时尚,一味地追求花样的翻新和做着脱衣秀的竞赛,甚至以牺牲底线为代价。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生活中那永不逝去的风景线,永远追求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没有乌托邦精神。因为,“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