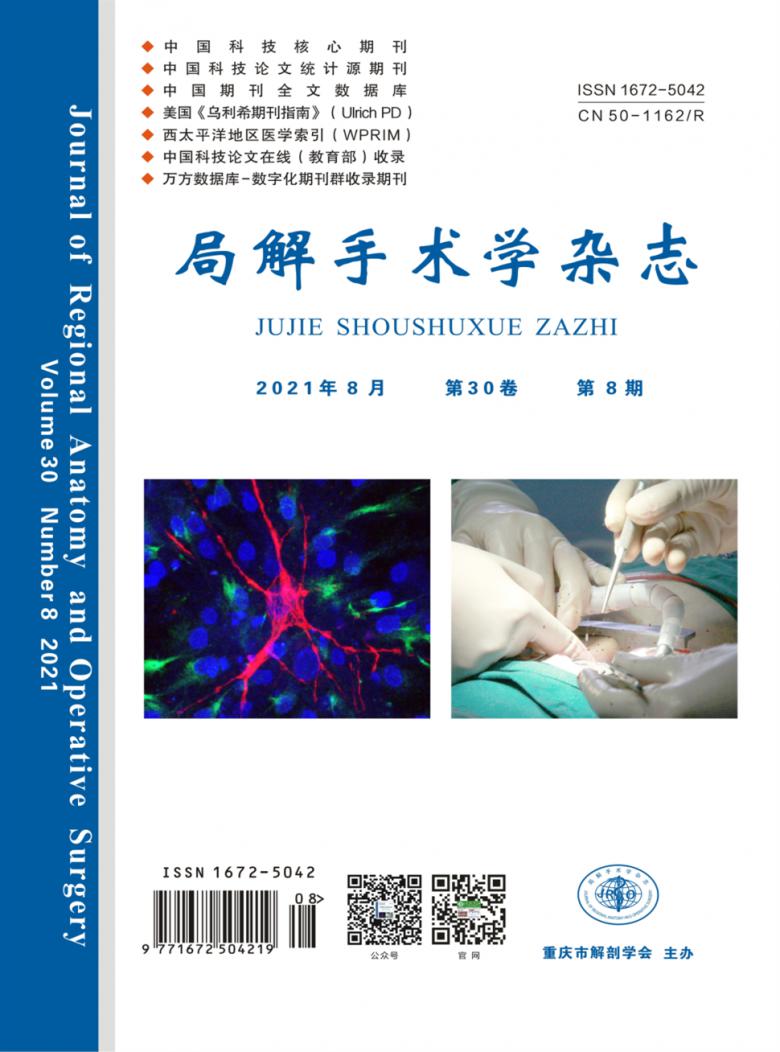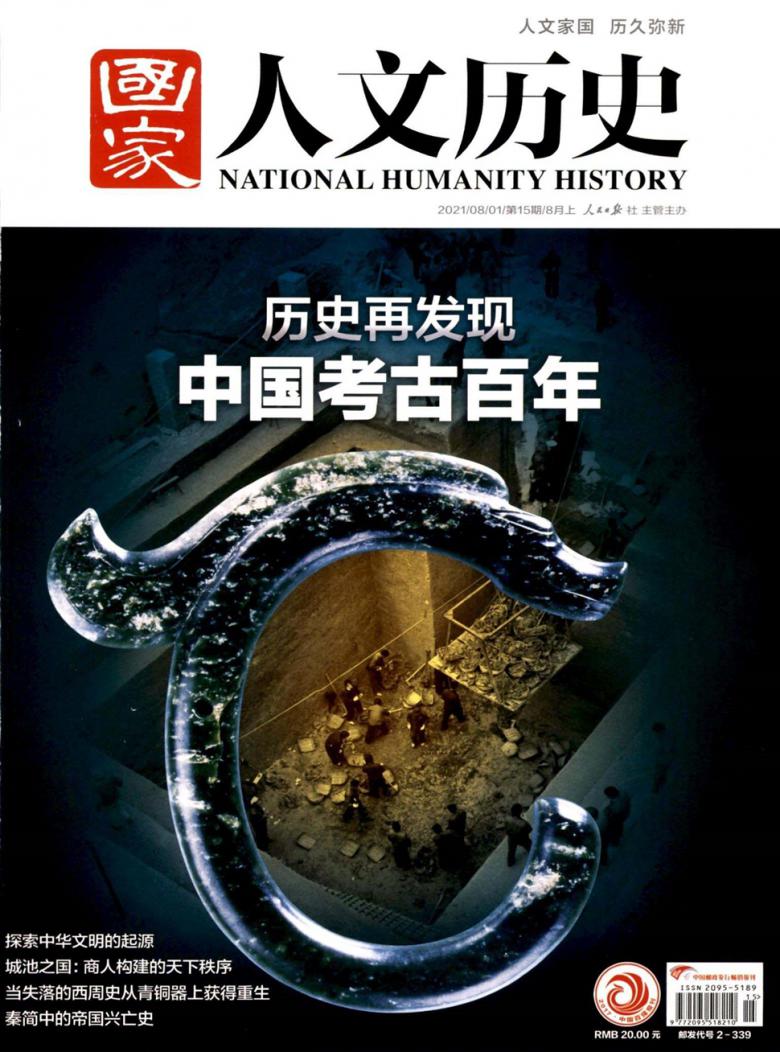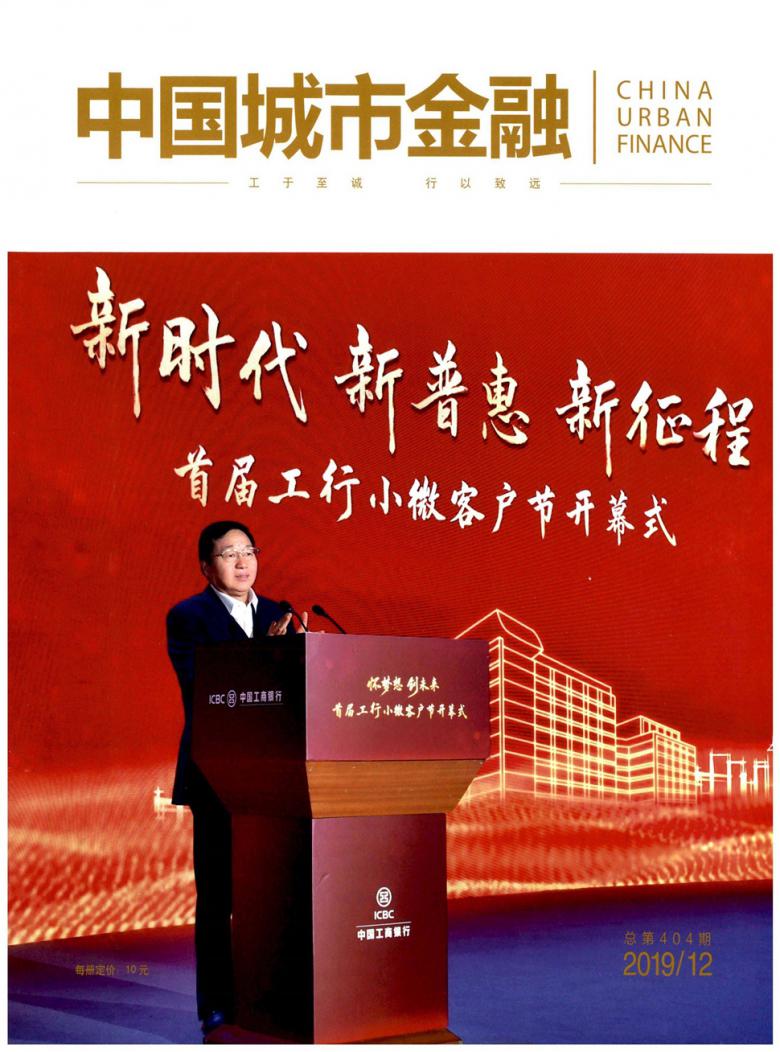浅谈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模仿音乐的基本方式
曾锋
论文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音乐一文学关系;文学的音乐化
论文摘要: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多种途径在文学中表现音乐,如声音、结构、主题(以及将三者综合起来的意象)和语义,等等。他们的音乐化创作表明:各门艺术是可以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文学可以成功地模仿和表现音乐,因而丰富表现技巧,创造新的文学风格和类型。
中国现代作家和诗人模仿音乐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的方法有:模仿声乐,如刘半农、刘大白等;从声音上模仿音乐的效果,大部分诗人都曾作过尝试,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沈尹默的《三弦》;从主题上暗示音乐,如穆木天、郭沫若等;从形式结构上模仿音乐乐思发展的手法,比较突出的如郭沫若、徐志摩等。此外,也有许多诗人深信通感的作用,企图在色彩描写中表现声音。实际上,这些手段经常是综合在一起的。而到了上世纪30年代之后,许多诗人如戴望舒、现代派诗人、九叶派诗人等,他们厌倦了前期诗人们“有形”的音乐化技巧,便更多地从语义、情绪、意象、心灵等“无形”的音乐上努力,而这类音乐化体验最终又总是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所有这些方式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三个途径:声音、结构、主题,如反复再现的意象就综合了这三个方面的成分。
一、模仿声乐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有一类歌诗体作品,是在声乐影响下创作的,这种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作为歌词而创作的,其外形、音节和情调都是为了便于歌唱,从黄遵宪到田汉、光未然等人的大部分歌词均是这种体制。再如刘半农的《瓦釜集》里的“四句头山歌”,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和“新禽言”这类作品,这样的作品即使尚未被谱曲,也使人觉得其本身就是歌,可以选择已有的合适的曲调将它唱出来。另一类则并未想到谱曲和歌唱,只是模仿歌诗的体式和风格而已,所以虽然外形上像是歌,实际上其表现法、内涵和意境都富有诗的意味和深度,这种诗现代诗人几乎都写过,以便实验诗的音节的表现力,或者以歌的外形和诗的内质相互作用而呈现出新的风格。以西方现代派诗歌为主要艺术资源的九叶派诗人也写过这种诗,如陈敬容的《出发》便是二段体的形式,以“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为副歌。这一类的作品总能使人在心头唤起歌声来,从而极大扩展了诗歌的审美容量。
二、从声音上模仿音乐的效果
这一类型最早的名作是初期白话诗人沈尹默的《三弦》,这首散文诗模仿,再现了三弦的演奏。“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几行,“旁、墙、挡、荡、浪” 是响亮的ang韵,“边、段、弹、三、弦、断”是比较响亮的an韵,“一、低”、“土、住”、“了、个”分别为细微的i,u,e韵,在响度和音色上形成呼应和对比。“旁、边、不”是双唇塞音,“段、低、的、挡、断、荡、土、弹”是舌尖塞音,“个、隔、鼓”是舌根塞音,以模仿三弦拨弦的音色。“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平声的双唇塞音加ang,an韵仿佛三弦明亮圆润的中音,平声的ang韵则仿佛其余音;“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上声的舌尖塞音加ang韵以及一连串的轻声和阳平,仿佛三弦低沉浑厚的低音;“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仄声的舌尖塞音加。ng,an韵,则颇肖三弦坚实清脆的高音,“声浪”也的确模拟出了和“土墙”不同的袅袅余音。
现代诗人模拟音乐的声音效果的作品很多,中国古典诗歌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深厚传统。国外的影响则主要来自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如ReneGhil“并且他把子音同母音关联在一起,而发现出来他们是与乐器相交响的。如A等于风琴,O等于维欧林。据他说某种子音放置在某种母音之前时即暗示出来某种颜色,等于乐器中的某种声音,唤起某种的观念。中国的象征派诗人受其影响,最为热衷于尝试这种技巧。如冯乃超的《酒歌》:“啊一一酒青色的字酉青色的愁盈盈地满盅挠烂我心胸。”诗中各行在开始和收束的关键位置,基本上都安排了舌面音以表现苦不堪言的声情。九叶诗人辛笛的《月光》企图表现聆听“贝多芬的手指和琴键”的“独白”时的印象,“你照着笑着沉默着抚拭着多情激发着永恒地感化着”,多少表现了《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神韵:连绵不断的三连音。
文学对音乐元素和技巧的借用,必须注意到两者的根本差异。以节奏为例,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存在都具有一种节奏,人的血液循环、呼吸等都是具有节奏的,因此音乐、文学都必须具有匀整而又变化的节奏才能与生命呼应,才能与生命的期待、运行的规律以及情感的宣泄起伏相契合。其实大自然一切的存在也都带有均衡感、节奏性,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昼夜的交替,等等。因此,人类的语言和文学必定具有节奏。
语句的起讫、语词的排布、语气的起伏,都具有一定的节奏性,都会趋向比较整齐的安排,在时间的周期性、强弱起伏的呼应配合上,与音乐节奏是相同的,这是源自内在的生命节奏的要求。
但文学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有根本的差异,文学的节奏若要像音乐那样整齐,会破坏语言表达的习惯,会扰乱语义表达所带来的自然起伏;因为句子、语词的音节有长有短,要符合音乐式的整齐,势必将自然言语中的长短人为地拉长或压缩,其自然的强弱势必会被人为地破坏,若照这种音乐节奏来朗读或默读,会带来极其不和谐和怪异的感觉。
古典格律诗做到了近似于音乐节奏那样的整齐,但又变得过于机械划一,而且缺少变化。如唐诗当时在演唱中若不重新加以处理,而完全遵照诗歌的节奏,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就正是因为这种整齐的格律与音乐难以配合,才使得长短句体的词出现了。而词的节奏则不是文学独立的节奏,只是音乐的附庸,它是配合音乐而产生的结果;如果没有当时的音乐,词单纯的文字节奏没有充分的独立价值,也没有足够的审美意味。
文学语言的音节之间的停顿太长,若要取得音乐节奏的效果,便必须拉长,但这会破坏语义的自然表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也可以或者增加各句的音节,或者加快说话的速度,但同样也不符合自然语言和阅读的习惯,因此纯粹的语音的音乐,如嘻哈、饶舌音乐,都必须比正常的语言表达快许多,它们只能是一些简单词句的不断重复、愤怒的宣泄,而不能表达书面文本以及正常口头文本所包含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如果要表达比较复杂的意义,便要结合阅读,不能单凭听觉,这时便产生了一种视听结合的混合文本。
单纯的节奏而没有其他音乐要素的配合,很难产生较好的审美效果。单纯的音乐节奏也常常必须和舞蹈等结合在一起,否则表现力将受到影响。而文学的节奏若单独存在,又要顾及语义表达,则其美感将是很有限的。因此尽管曲艺、说唱更接近声乐表演形式,已非眼看、思想的纸面上的文学,也仍然需要乐器的辅助,以调剂语言节奏的单调感,弥补单纯的人声表演所导致的单薄。接近于歌唱的语音尚且不能单靠声音的节奏和旋律,那么纸面上的诗歌便更不能单凭自身的语音效果而获得足够的审美价值了。
三、从主题上描写和暗示音乐
从穆木天、梁宗岱到戴望舒、卞之琳,法国象征派诗人既启示他们注重诗歌的声音,又提示他们有些音乐效果只有通过主题内容才能暗示,如魏尔伦便告诉他们像音乐的调性就只能以氛围和颜色的描写来触发:“在这一点他很对:低沉调( minor key)只有用间接的方法才能传达,要惆怅,第一就得恍惚。“正如贝多芬所说,b小调是黑色的;因此小调常用来表现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而大调通常被认为是明亮愉悦的。作家要再现小调音乐所生发的听觉感受和审美印象,自然也可以通过悲伤的情调、低沉的色调、低回的节奏、暗淡的声韵大致模仿出来。
现代文人特别是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创作社作家,特别喜欢描写感情冲动奔放的艺术家和美妙的艺术氛围,在这类题材和描写中,通常要唤起音乐的听觉审美体验,音乐性的意象也会融人整部作品的情调和结构中。曹禺的《雷雨》也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在序幕和尾声中,用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张爱玲的作品也渗透着非常丰富的音乐感受和音响意象,并很自然地构建起乐曲式的结构来。其中给人印象极深的有《金锁记》中"Long, Long-Ago”的音乐,还有《倾城之恋》中“晰唯呀呀”的胡琴,就像电影中的音乐,用以表现人物的内心、营造故事的氛围,使读者烯嘘叹息,久久不能释怀。当长安退学、退婚时,"Long Long-Ago”的琴声便响起,可怜的女孩在凄凉灰暗中告别了明媚快乐的青春,这种手法也如同作曲家们对已有的音乐素材和旋律的借用。《倾城之恋》中,“胡琴晰咯呀呀地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则如同音乐的主题旋律,在作品首尾出现,构成具有ABA’意味的结构。若有作曲家要将这部小说改编为音乐,主题旋律大概就要以此为想像的出发点了。如徐志摩和刘大白一样,作家以舌面音y和舌尖边音1来模仿胡琴运弓触弦的效果,表内心的郁积,a韵则发而为慨叹,语音的音乐效果也非常突出。表休止的破折号之前是苍凉深沉的叙说和慨叹,节奏悠长、旋律沉郁,临近曲终时破折号暂停后一转,“弱十强”的两音一满弓,两个无奈而又断然收束的仄声,运弓时则应是由轻到重的几次起伏、由弱到强的数番循环,-满腹的感慨,欲说还休的顿挫—小说家对二胡的音乐效果作了奇妙的再现,同时也由此抒发出文字所不能表现的无尽感慨。
四、从形式结构上模仿音乐的乐思发展和曲式结构的方法
结构的音乐化是模仿音乐最有效的手段,这一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作家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启发,本来各大文化的音乐艺术中,也只有西方古典音乐才最突出地拥有宏富庞大而严整的结构,从徐志摩到沈从文、卞之琳、萧乾,大都曾取法于此。作家可以模仿乐思发展的手法如重复、模进、变奏、再现等,可以模仿曲式结构如三部曲式、回旋曲、变奏曲、奏鸣曲、赋格等。穆木天在《法国文学史》里介绍了瓦雷里著名的音乐诗《木马》,此诗是“专为韵律(Melodie)的试验而作的”,运用了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也不会失去其新鲜感的音乐的重复手法:
回转吧,回转吧,好的木马,
回转百遍吧,回转千遍吧,
常常回转吧,永远回转吧,
回转吧,回转,应和着木苗之声。
现代文学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曲式”形式,如回旋体,徐志摩所译哈代的《多么深我的苦》便是典范之作,再如:徐志摩的《地中海中梦埃及魂人梦》、《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黄自作曲的《旗正飘飘》,刘大白《霞的讴歌》,傅雷的“汁梁的姑娘”,朱湘等人引进的“圈兜儿”体,等等;刘半农的《卖萝卜人》则作了回旋性的安排。
五、通感
也有许多诗人深信通感的作用,企图在对其他感觉的描写中唤起音乐和声音。郭沫若称赞王实甫能在音响之中听出色彩来,徐志摩希望构筑起人类各个感官的联系;梁宗岱认为声、色、香、味可以一齐重现于感官,这种通感是神圣的艺术和人生的出发点。象征派诗人王独清也狂热地追寻“色的听觉”,企图让“色”“音”的感觉交错打通,在作品里描写出“音画”来:
在这水绿色的灯下,我痴看着她,
我痴看着她淡黄的头发,
她深蓝的眼睛,她苍白的面颊,
啊,这迷人的水绿色的灯下!
前文所引的Rene Ghil欲将元音与乐器联系起来,兰波也将A,E,I,R,O五个元音与不同的色彩、音响、气味和形象关联起来,王独清从这些诗人受到启发(中国古代诗人的通感也是很敏锐的),他诗中的音节和所描写的颜色便都与某种乐器相关,读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和直觉,召唤相应的乐音。
而在梁宗岱的《晚祷》中,音乐更是具有.了气味:
不弹也罢,
虽然这清婉潺浚
微咫荡着的
兰香一般缥缈的琴儿。
六、语义、情绪、意象、心灵等“无形”的音乐
厌倦于诗歌外在的音乐形式,或者感觉到外在形式所提供的音乐感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所以特别强调内在的无形的音乐,如情绪等,这不是后来的诗人发现的,早期音乐化写作的行家们,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一开始就痛感到了诗歌音乐化手段和效果的不够,所以反复强调情绪、诗情、内容、想象的重要。如穆木天便强调“内生活”,心情的流动的内生活是动转的,而它们的流动动转是有秩序的,是有持续的,所以它们的象征也应有持续的。一首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这种“持续”和“秩序”的“律动”便是音乐的,但它将自然表现为诗歌外在的形式与结构。 在早期,外在形式上音乐化的新鲜感、“第一次”的实验和游戏的兴致都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到了30年代,戴望舒写出了融郭沫若和徐志摩的音乐形式、徐志摩的秀丽轻倩和象征派的朦胧颓唐于一体的《雨巷》,但他很快就不满意了,因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之前的诗人们,仍旧只是他们早已唱得有点儿滥了的旧调,—叶圣陶说他开了新诗音节的新纪元,其实是夸大之辞。所以自戴望舒开始,诗人们纷纷开始开辟新的诗歌音乐化的领域。他们或者反对诗歌的音乐化,或者淡化外在的音乐形式,或者干脆创造偏于晦涩嘈杂的风格。但他们的作品最终都脱离不了诗歌的音乐性,无论是怎样的题材、想象的方式和抒情的风格,总是要体现为一定的外在的音乐形式。诗人们强调内在的体验、想象、沉思或语言本体的存在,其诗歌便染上了各自的心灵、人格和艺术世界独有的音乐色彩。
穆旦是郭沫若之后真正创造了新诗的新风格的诗人,他在诗歌的内向性、诗语的本体性、诗思的深度和复杂性、诗歌音乐的独特风格上,都超越了前期的诗人。他有粗莽雄放的高歌,但不用借助惠特曼式的反复咏唱的排比长句,—艾青便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调子的牵引;他也有柔媚欢快的轻唱,却不需要模仿整齐划一、晰唯呀呀的歌谣体,—后期新月派诗歌中仍然鸣响着徐志摩的歌调的回声。他的诗歌是意象的、深层体验和思索的音乐,内在音乐的鲜明和充沛超过了外在的音乐形式。试看他的《暴力》一诗
从一个民族的勃起
到一片土地的灰烬,
从历史的不公平的开始
到它反覆无终的终极:
每一步都是你的火焰。
从真理的赤裸的生命
到人们憎恨它是谎骗,
从爱情的微笑的花朵
到它的果实的宣言:
每一开口都露出你的牙齿。
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
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
从我们生命价值的推翻
到建立和再建立:
最值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
从我们今日的梦魔
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
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直到他的不甘心的死亡:
一切遗传你的形象。
这是一首变奏曲,继承了鲁迅悲观的历史观主题,从历史的苦难、理想的被扼杀、专制权力的建制、被注定的命运前途,四次变奏,咬牙诅咒和愤慈不平于专制暴力在民族历史和命运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是令人感觉不到其外在音乐存在的内在音乐,外在的排句的形式感和力量来源于内在的意象和感情,而此前的诗歌中被优先明确感觉到的是外在的形式,这里则以内在的意象、情感和思索占第一位,首先被感受到的是内在诗思的冲击力及其所带来的节奏和旋律。
或许更能体现穆旦诗歌音乐性的独特性的,是《幻想的乘客》这样的作品,前两节如下:
从幻想底航线却下的乘客,
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
而他,这个铁掌下的栖牲者,
当他意外地投进别人的愿望,
多么迅速他底光辉的概念
已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纤缓,
是巨轮的一环他渐渐旋进了
一个奴隶制度附带一个理想,
“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出现主题“幻想的航线”,这是指进行欺骗性宣传的腐败政治,从这个航线卸下是指被欺骗的人为统治者所愚弄,听信其欺骗。“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一站”呼应“航线”,“错误”是“幻想”的延展,不切实际的幻想、信从腐败政治的宣传必然导致错误的选择。“而他,这个铁掌下的牺牲者,”“铁掌”呼应“航线”,“牺牲者”呼应“错误”,这两行是指人们受政治所制造的幻想的欺骗和操纵,而成了腐败政治的牺牲品,这都是第一行主题的展开。
“多么迅速他底光辉的概念”,“光辉的概念”即“幻想”的变奏。“已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纤缓,”这两行呼应“幻想”的“错误”,被愚弄和操纵的人从“光辉”的幻想陷人了实际的泥潭。“是巨轮的一环他渐渐旋进了”,“巨轮”即“航线”的变奏。“一个奴隶制度附带一个理想,”“理想”是“幻想”的变奏,这条幻想的航线实际上是一个奴隶制度。
显然,这里外在的音乐性虽然没有彻底消除,但内在的音乐完全盖过了它。这是内在的意象和语义的奇妙乐曲,它是奥登之外,另一位穆旦诗歌创作的导师—T.S.艾略特的诗歌音乐的回响,一是语义的音乐:“一个词的音乐性存在于某个交错点上:它首先产生于这个词同前后紧接着的词的联系,以及同上下文中其他词的不确定的联系中;它还产生于另外一种联系中,即这个词在这一上下文中的直接含义同它在其他上下文中的其他含义,以及同它或大或小的关联力的联系中。自然,还有结构和意象的音乐:“但是我相信在音乐的各种特点中和诗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节奏感和结构感。……诗中主题的回复运用和在音乐中一样自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诗,它像是用几组不同的乐器来发展主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过渡,它与交响乐或四重奏中的乐章发展相似;也有可能用对位法来安排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