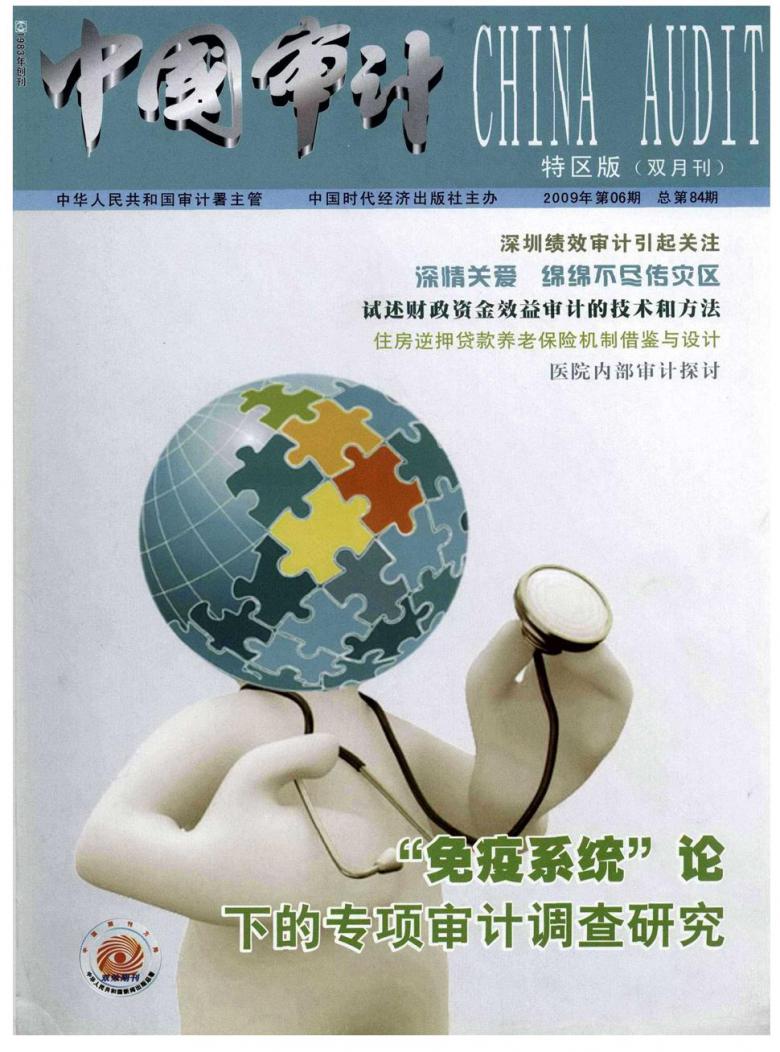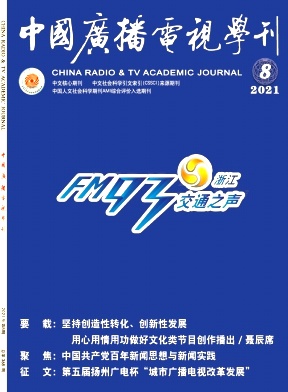“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童庆炳 2007-11-14
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属于什么?是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文学?这是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经常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的看法迥异。历史学家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历史,既然你要以历史题材为创作的资源,那么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起码的要求。文学批评家则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文学,文学创作是可以虚构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只要大体符合历史框架和时间断限,就达到了历史真实了。由于观点的分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批评,几乎都是挑剔历史题材创作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病,而文学批评家则在历史真实问题上相对则放得宽松一些,更多地去批评作品的艺术力量是否足以动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探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问题,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很重要的。
历史1和历史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已故著名教授朱光潜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甲-物乙”的命题。对于朱光潜先生的这个命题的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1”和“历史2”的理解。朱光潜先生在反驳蔡仪先生的批评时说:“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1]如何我们把朱先生观点无疑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观点运用于对历史上面,那么很显然,原本的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完全不带主观成分的客观存在,就是“物甲”,也就是我这里说的“历史1”。“历史1”――原本的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存在,由于它不能夹带主观成分,是历史现场的真实,因而几乎是不可完全复原的。特别是后人去写前人的历史,要写到与本真的历史原貌一模一样,把历史现场还原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例如,大家都一致推崇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他生活于公元前145年到公元前90年。他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所写的是中国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公社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具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也许有二千年左右之久,他不过是把《尚书》中及其简略的记载敷衍成篇,他怎么能写出五帝的原本的真实的历史原貌呢?再以《史记》第四篇《周本纪》来说,当时虽然有文字记载了,但那是大约是公元前1066?-前771年,距离他生活的年代也大约早900年到500年的历史,他怎能把那个时期的本真历史原貌叙述出来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退一步说,就以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来说,他写汉武帝,写李广,写卫青等,但他并非始终在朝,他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汉武帝贬责,受到了宫刑,几乎成为一个废人,在卫青、霍去病掌握兵权,征讨凶奴时期,他在自己的家乡专心编撰《史记》,消息闭塞,像汉武帝和卫青的对话,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当时获罪在身,大家避他唯恐不及,谁会把朝廷上的谈话告诉他呢?所以他在《史记》中写得那样具体,完全是司马迁自己的推测之辞,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史记》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不是历史本身,仅仅是历史的“知识形式”而已。大家都欣赏司马迁所写的“鸿门宴”故事,这个故事可谓高潮迭起,真是扣人心弦。无论是人物的出场、退场,还是人物的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十分讲究。这段故事不知被多少戏剧家改写成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在这一类描写中,为了突出戏剧性,为了取得逼真的文学效果,为了展现矛盾冲突,为了刻划人物性格,如果不根据史实做必要的虚构,根本是不可能写成这样的。《史记》虽然以“实录”著称,大家一致认为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作品的感染力,他动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司马迁自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代宗师的治史名言,二千年来脍炙人口,这说明一个史学大家必然有他的评价历史的理想的,有他的主观成分。他的《史记》不是完整的本真的历史原貌的记载,是他提供的历史“知识形式”。
所以我们说,那已经无法完全知道的本真的历史原貌是“历史1”,而历史学家记载的史书,那里面的历史事实,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他褒杨他认为好的,贬抑他认为坏的,鼓吹他想鼓吹的,遗漏他想遗漏的,甚至其中也有起码也有细节和情节的虚构等等,这就是“历史2”。司马迁给我们提供的是“历史2”,不是“历史1”。如果说,“历史1”是原本的历史真实的原貌的话,那么“历史2”是经过历史学家主观评价过的历史知识形式。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有些历史学家要求从“历史1”开始,这是对历史题材创作的一种苛求,其实是做不到的。历史题材创作一般只能从史书开始,也就是从“历史2”开始。
从历史2到历史3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从“历史2”――史书开始,但不是重复史书。史书作为“历史2”是属于历史学,不属于文学。真正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历史2”――史书开始,加工成文学作品。如前所述“历史2”已经有了加工,文学家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在加工上面的再次加工。这后面的作家的加工属于文学加工,所产生的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2”,而是“历史3”了。
那么,“历史3”与“历史2”有什么不同呢?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的呢?
毫无疑问,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只能从历史2开始,即从史书所提供的事实开始。因为作为历史2的史书是创作家首先要熟读的,因为不论史书如何夹带着主观成分,它总是提供了大致的历史线索、历史框架和时空断限。如何一个创作家连这些都一无所知,创作也就不可能。但是如何只是停留史书记载的具体描写上面,也还是不行的。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来说,最重要的一环是“艺术加工”。
“艺术加工”涉及的范围很宽,几乎就是再谈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这篇小文里无法展开来讲。只能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来谈点看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是随意的,它的形成和产生都有其必然性。因此,在把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如何尽可能做到“合理合情”就变得十分重要。所谓“合理”,就是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有它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性,他的形成和产生都受历史背景和条件的影响,创作家最重要的艺术加工就是要摸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这种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运动规律,一旦摸透了,就不能随意地打断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运动逻辑,而要始终紧跟这种逻辑。所谓“合情”,就是指历史人物的情感活动也是有内在的运动的轨迹的,他或她欢笑还是痛苦,是喜还是悲,是愤怒还是兴悦,是希望还是失望,等等,都不是随意的,也是有它自身的规定的。创作家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运动轨迹,只能遵从,而不能随意违背。
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学家,他曾说:“不要按照自己意志随便打断和歪曲小说的情节,自己反要跟在它后头,不管它把您引向何方。”[2]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中国古代文论里面,也有“事体情理”的说法,即所描写要符合对象的运动轨迹,不可胡来。曹雪芹是大家都佩服的小说家,他说:“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事体情理罢了……至若离合悲欢与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3]这里所说的“事体情理”,所说的“追踪蹑迹”,就是讲要把握住描写对象的活动的轨迹、性格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要自然,要天然,不要为了搞笑,为了增加噱头,而离开、歪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内在的必然的运动逻辑。当然,编写历史小说、历史剧,为了增加读点和看点,增加艺术情趣,增加艺术效果,有时插科打诨是不可免的,但正如明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所说:“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某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4]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内在的必然的运动的逻辑呢?这里就要关注中古代文论提出的另外一个命题,即“设身处地”。创作家一定要调查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的背景的条件下,通过“设身处地”的反复体验,做到与自己所写的历史人物情感同步的状态,与小说或剧本中的人物同甘苦共欢乐,喜怒哀乐也达到相与共。这个时候,不是创作家指挥自己笔下的人物,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当傀儡,而是跟着人物的性格走,跟着人物的心理活动走,宁可压抑自己的欲望,也要满足人物的要求。应该知道自己笔下人物的复杂性,也许他会做出出人意表的事情来。《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写曹操抓获关云长,关云长不肯投降,本该杀掉,已取心头之患,偏偏曹操就不杀关云长,者是何道理?这就需要作者有理解曹操的心。毛宗岗评道:“曹操一生奸诈,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似折服曹操耳。虽然,吾奇关公,亦奇曹操。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以奸雄敬爱豪杰则奇。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又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好奸雄。”[5]毛宗岗这段评语,揭示了罗贯中对于自己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细微曲折的之处有及其深刻的了解,若不是这样来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三国演义》的深微之处,也就散失殆尽了。
作为历史2的史书所记载的材料经过如上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区别于史书上的材料,这就是历史3了。这历史3才是属于历史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所要追求的艺术形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小说或历史剧的种种“不符合历史真实”、“不尊重历史真实”、“不符合历史原貌”等一类批评,常常只是对于历史2的迷恋,对于史书的迷恋,并非要小说家或剧作家真的尊重历史1――历史原貌,因为历史本真原貌基本上是不可追寻的。
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把历史1(历史原貌)与历史2(史书)区别开来,当我们要求艺术加工让历史2前进到历史3(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中的历史真实)的时候,仍不能抹煞历史1、历史2和历史3之间的关系。
对于历史1对于历史小说家或剧作家来说,往往是不可追寻的。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真正的生活源泉,正是历史1。唯有历史1是才是活水源头。因此真正严肃的历史小说家或剧作家,为了历史真实,总是要通过查阅正史以外的其他历史资料,亦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曾经发生过某个历史事件的地点环境的勘探,考古的实物发现,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以增加创作历史真实性。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地势、地貌,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况,尽管今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其中一定还有不变的成分可供创作时参考。特别是某地的民风民情民俗,从衣食住行到住家细节,都有参考价值,决不可忽略过去。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小说、历史剧,从地理环境到语言到生活细节,都现代化了,这就不能不影响作品的历史真实。如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其中的语言过分现代化了,有一些后人才说出的名言,少数民族才有的谚语,今天人刚刚才说了几年的话(如“底线”之类),都出现在剧中,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另外据有的历史学家说,《汉武大帝》中关于“精钢”的情节,也完全是失真的。西汉时代,汉朝人的炼铁和炼钢技术都是周围国家无法比拟的。不是匈奴人掌握“精钢”技术封锁汉朝,而是汉朝的炼铁、炼钢技术更高,不得不对匈奴人封锁。造成此种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完全忽略了历史1。我反复说过,历史1作为历史的本真原貌是不可整地追寻的,但其中可能还有若干历史的碎片,也许还残留民间,或残留在考古的发现中,艰苦的实地考察和勘探,对考古文物的重视,仍然是必要的,对于文学这种十分注重细节的艺术种类说,如何真实地再现某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貌,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说历史1的考察对于历史3的创造,仍然是创作的源泉与基础之一,丝毫也不能忽视。
在从历史2到历史3的过程中,即根据史书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对于史书的记载,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如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史书不完全是客观的,里面夹带了主观成分。因此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面对史书必须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辨析的工作。就历史的框架和时间断限来说,可能史书是很有用的,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观点,就有可能存在许多历史局限。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总是歌颂帝王将相,而批判农民起义及其英雄,把农民起义称为“造反”,把农民起义的代表人物称为“贼”,这完全是历史的颠倒,应该颠倒过来。历史典籍无疑都是历史小说家、历史剧作家十分重视的,但的确存在一个如何阅读的问题,用什么观点去阅读的问题。
另外既然历史3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它属于文学范畴,那么如何超越历史典籍,让所描写的内容具有想象性、诗意性,就是很自然的。他们无疑要重视历史典籍,但又不能照搬历史典籍。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是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历史典籍是干枯的记载的话,那么文学家笔下的历史就必须赋予这干枯的记载以鲜活的血和肉,赋予以深邃的灵魂,把某种意义上的死文字变成正在演变着的活的故事。从历史2到历史3的想象就就成为真正的考验。以《三国演义》为例,其中的诸葛亮设计的“空城计”,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这情节完全是“想象”、“虚构”。《三国演义》长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想象。在这里,小说家和编导何等生动地写出了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沉着、勇气和才能,作者简直对他倾注了无限的赞美之情,但历史的事实如何呢?你查一下《三国志》那个历史书就知道,历史上一些没有的事情,被说得真实可信,甚至绘声绘色。譬如,诸葛亮一生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诸葛屯兵陕西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是湖北担任荆州都督,根本没有机会与诸葛亮对阵。“空城计”情节完全是作家想象的产物。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虽然它往往不可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还是要尽力去寻觅,即或只能获得一些碎片,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典籍作为历史2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当然是重要的,需要十分熟悉,也需要加以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有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深度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后,我们才会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