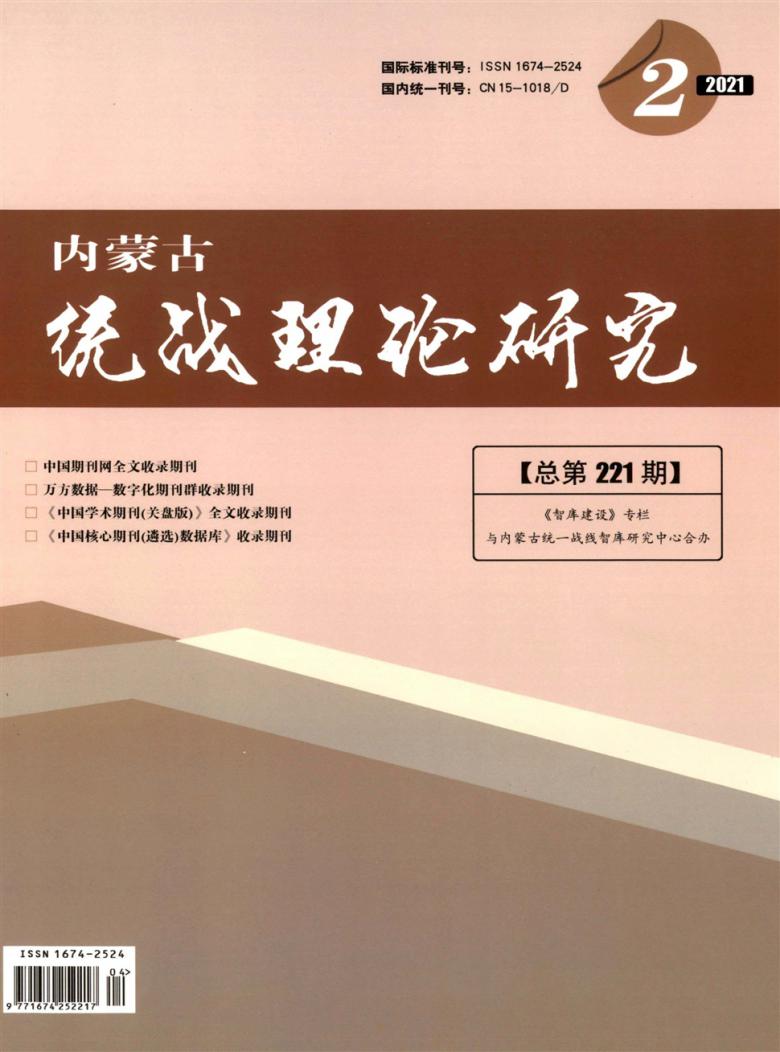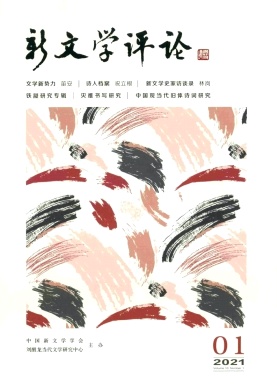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
吴泽霖
内容提要 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诟病,而如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就能洞解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真谛。他认为,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体现,思想只有转化为情感才能沟通人、联合人,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关键词 列夫·托尔斯泰 艺术情感说 中国古典文化 音乐 心灵融合 尽管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但是他对艺术的定义却屡遭诸多学者诟病——托尔斯泰把艺术定义为:“一个人有意识地利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① 苏联文艺学家奥夫相尼科夫指出:“托尔斯泰的定义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他的定义里,艺术被限制在了人们的感情领域。”不过奥夫相尼科夫又替托尔斯泰辩护说:“如果以为这位‘思想的艺术家’会把艺术的作用归结为仅仅传达感情,那就太天真了”。② 普列汉诺夫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托尔斯泰对艺术的定义“不对”,说是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思想③。 刘宁等著的《俄苏文学批评史》也指出,托尔斯泰“在一定程度上把艺术中的情和理割裂和对立起来,认为艺术只表现人们的感情,而不表现他们的思想”④。 我以为,这些非议都忽略了在托尔斯泰那里,感情和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把感情和思想分离开来;它们更没有注意到,在托尔斯泰看来,思想和情感不仅是一体的,而且他把情感视为比思想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东西。思想只有转化为情感才能沟通人、联合人,而这里才正是发挥艺术独特功能的地方。 实际上,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真义而不会一味指责了。 一、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体现 中国人认为:情,正是人的心理、思想品性的最本真、最深切的表现。喜怒哀乐,情也;而其未发之时,谓之中,也就是性。《中庸》说它是“天下之大本也”。正如朱熹说的,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道之体也”。因此,情和性是表和里的一致关系。中国人一直将性情相并:“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⑤或谓“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时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⑥。 正由于中国人深刻认识到,情感与人性、与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情感活动不仅是理性活动的基础,而且在生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因此把陶情和冶性、修身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陶冶情感,使之发而中节,从而循性达命,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正是中国人追求的与天地万物和谐一体的人生终极境界。 托尔斯泰之注重情感,不仅出于他对一生创作实践的体悟,也和他自19世纪80年代始,愈来愈积极地接触和认同中国古典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当年一系列理论著述如《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艺术论》、《谈艺术》中,他都把情感和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人的心性的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既然托尔斯泰把对生命意义的求索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也就必然地把情感——这一生命的最真切的表现,作为关注的对象。他从事艺术,也正是认为只有艺术才是推动人的情感活动的至高手段。 托尔斯泰对西方的思辨理性一贯有怀疑。1867年6月28日,他给俄国著名诗人费特的一封信中,他就赞赏费特把智慧分为“心的智慧”和“脑的智慧”,而他当然地站在“心的智慧”的立场上⑦。对于心与脑,情和智,情感活动和理性思维,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分析的:“无法强迫脑去辨明心不想接受的东西”,“人想往的是他的心所希望的东西。只有在他的心希望得到真理的时候,他才去思索真理”⑧;“我愈发坚信,在生活中,在所有人际关系中,一切都基于情感的遭际和波动。而推论和思索不仅不能左右情感和事情,而且还要去模仿情感。甚至客观条件也不能左右情感,而是情感在左右客观条件,即从千百个客观事实中进行选择”⑨;他又说,“生活使我越来越明确地相信,脑的理智的论据不能改变生活。它只有在生活受到触动之时才能改变生活。情感、愿望,利益和对幸福的想望在唤起思想的活动”⑩。 这种对心、对情感的注重和对脑、对理智的怀疑和贬抑态度在托尔斯泰1904年4月29日的日记里得到了清晰的总结。 托尔斯泰把人的知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我了解我自己,由于我是我。这是最高级的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深刻的知识”。而“下一种知识,是通过感觉(我听到,看到,摸到)所获得的知识。这是外表的知识……但是了解它已经不像了解自己那样了……第三种知识更浅些,那便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即从自己的感觉推论出的知识或别人用语言传达的知识——论断、预言、结论、学问”。 然后,托尔斯泰对这三种知识加以举例: “第一(种知识),我忧伤,疼痛,寂寞,高兴。这是没有问题的。(即情感——引者) 第二(种知识),我闻到紫罗兰的香味,看见光和影,等等。这里面可能有错误。(即感觉——引者) 第三(种知识),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且在旋转,知道有日本和马达加斯加,等等。这些都是可疑的。(即理性知识——引者)” “我想,生命在于将第二、第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在于人自己感受一切。”(11) 我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对知识的重要性和可靠性的评价,是以其获得的方式:情感、感觉、理性的程度依次为序的。情感方式至上,而理性方式最为浅薄可疑。这首先在于托尔斯泰对情感有着不同于现代认识论而认同于中国古典知论的理解。 按照中国知论,这第一类的喜怒哀乐(忧伤,疼痛,寂寞,高兴)之情才算得上是最根本的知:它是天生的,人性中固有的真知,是所谓德性之良知,最真切可靠的知识。而不仅这种 “德性之良知,非由闻见耳” (王阳明《传习录·中》),并且那些“闻见小知”还往往对“德性大知”起着蒙蔽、误导的作用,即张载所说的,“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而“止于闻见之狭”,所以要学“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走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 (《大心》)的路子。(12) 托尔斯泰“将第二、第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视为生命意义之所在,同样也就是认为,一切外在得来的知识只有和人的情感所蕴含的德性真知相融一,化为“性中所有之物”,这才是最真实可靠的知识。因为只有通过真情实感才能去认识自己的心性,从而循性达命,认识自己心中的上帝,达到和上帝的同一。 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 中国人既认识到人的情感是其心性最本真的表现,它比思想、理性更本质、更真实、更有力,而文艺的功能则正在直接诉诸人的情感,所以就力图通过文艺陶冶性情、沟通情感,来达到修己安人、天人合一的社会人生目标。于是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就成为进行生命追求、实现终极实在的一种手段。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雍也》),讲“兴于诗,成于乐”(《泰伯》),都表现了对情感、对直接作用于情感的文艺(特别是音乐)的推重。可以说,重视文艺对情感的不可替代的能动作用,成为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陆机的《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强调了情感在文学中的功能。《文心雕龙》五十篇,涉及情的,竟有三十余篇。重情之风延及后世,《金瓶梅》“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说,“其中大旨谈情”。即在当代,中国作家也是把表现情感作为文艺的主要功能。老舍就说过:“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述。”(13)而中国古典文艺学中,和“情”相连用的概念可谓俯拾即是:情志、情思、情致、情调、情理、情境、情景、情意、缘情、移情……对情感的论述更不可胜数。 托尔斯泰在188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谈到有人说“科学能够指出道德法则”时,则提出文艺优于科学、理论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能够“指出道德原则”,而且能够“抓住人的心”: 的确,不可能向人们证明什么,就是说,不可能驳倒人们的谬见,每一个走上歧途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谬见。当你想驳倒这些谬见的时候,你就要把一切归纳为一个典型的谬见,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谬见……他就认为你没有驳倒他。他认为你说的是另一回事。的确,怎么可能盯住所有的人呢!因此,永远不要反驳、争论。 那么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指出: 只有用艺术手段才能影响那些步入歧途的人,做到你想通过争论去做的事。通过艺术你能抓住步入歧途者的全身心,把他引上应走的道路。通过逻辑推论阐述一个思想的新结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争论、驳斥,而要引导。(14) 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托尔斯泰都反复谈到艺术的这一作用。比如,在谈到“《克莱采奏鸣曲》的跋没有必要写”时,托尔斯泰说:“原因在于,不能依靠议论使那些和我见解不同的人信服。应该首先推动他们的情感……这不是议论办得到的,而是和感情有关的事。”(15) 在这里,托尔斯泰对比了科学的方法、逻辑推论的方法和艺术的方法。明确地道出了自己为什么要诉诸文学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艺术的功能不是去以理服人,而是将理化为情而以情感人。它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引导人的心性。所以说是“推动他们的情感”——传情而感人才是艺术的不可替代的功用,也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之所在。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这一思想,大抵是普列汉诺夫和奥夫相尼科夫所未虑及的。 这一观点托尔斯泰不仅躬行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而且也是他文学批评的尺度。比如,他对契诃夫和果戈理的褒誉和批评,就是要论证艺术的感染力在于传达情感,而非论说思想。 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是托尔斯泰最喜欢的小说。不过,他们对这个夫唱妇随的“宝贝儿”的态度并不一致。托尔斯泰指出,契诃夫在理性上,本意“显然是想嘲笑凭着他(指契诃夫——引者)的推理(而不是他的感情——引者),认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然而“因为是无意中(即不靠理智,而靠情感——引者)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契诃夫对这一问题的本然情感(即他的良知)“不允许”他嘲笑,所以托尔斯泰说契诃夫竟像《圣经》中“巴兰的诅咒”一样,一开口却成了赞许(16)。结果小说“如此出色”地描写了“宝贝儿”的可爱。 而对果戈理,托尔斯泰说,“当他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感情时”,他就表现了“扣人心弦、常常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思想”,可一旦他想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教诲说话时,“就出现了很恶劣很讨厌的胡言乱语”(17)。 可见,托尔斯泰不是反对艺术的思想性,而恰恰是要求一种真挚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应该是 “听命于自己的心灵和宗教感情”,是真情的流露,而非做作、违心之谈。 三、醉心音乐是他的艺术情感说的佐证 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鲜明地诠释着他的艺术情感说。 托尔斯泰一生都醉心于音乐勾魂摄魄的征服力。他自认“很容易受音乐感染”(18),听着音乐,他会动情地说,“活在世上真好!”“他的脸上会现出特别的神态,脸色发白,目光凝视着远方,常常不能自已,眼里噙着泪水”(19)。托尔斯泰借自己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主人公之口喊出:“音乐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它能一下子把我带进写音乐的人当时所处的心境中,我和他心心相印,并和他一起从一种心境转到另一种心境”——这不正是对托尔斯泰艺术定义的最好举证吗!于是主人公慨然叹道:“在中国,音乐是由国家管辖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文艺观从一开始就把文艺,特别是音乐的社会功能极强地突出出来,主张 “礼非乐不履”的治国安邦之道,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礼教政治服务。 孔子和托尔斯泰虽隔万里千载之遥,同样对音乐有着极强的感受力和着魔般的爱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他重视音乐,把乐作为推行德政教化的工具。《孝经》载孔子语:“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他们都明确认识到,在所有文艺手段之中,音乐恰恰是能最直接、最有力地作用于感情的。正如托尔斯泰在1876年12月致柴可夫斯基信中指出的:“音乐是直接作用于情感的艺术”,“是最最感人肺腑的艺术”,(20)所以“是艺术世界中最高的艺术”。托尔斯泰给音乐下定义说:“音乐乃是情感的速记。”(21)这正合于中国人的看法:“乐者,心之动也”(《乐记》)。
这就是托尔斯泰所寻求的那种感情的传达、沟通、启迪和共鸣。库图左夫和士兵们这时的关系,正表现为一种艺术家和感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的关系。 托尔斯泰指出,“艺术作品里主要的是作者的心灵”(33)。而在文艺沟通心灵的过程中,“感受者和艺术家那样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至感受者觉得那个艺术作品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而是他自己创造的,而且觉得这个作品所表达的一切正是他早已想表达的。”所以,“真正的艺术品做到了在感受者的意识中消除他和艺术家之间的界线……而且也是他和所有领会同一艺术作品的人之间的界线” ,“使个人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34)。 托尔斯泰在1909年的一篇日记里也说过这样的意思: 艺术作品使“感受者这时体验到一种类似回忆的感情——‘啊!正是这个!以前我发生过多次了,我早就知道它,可硬是吐不出来,看!现在,别人向我说出了我自己’”(35)。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不过是艺术家能够察人所未能察,言人所不能言罢了。 而恰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附录十六》里也讲过: 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 而这也正是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所要传达的妙义。 质言之,恰恰在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中,寄予了极高的思想境界:他把“艺术的使命”定为实现“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这就是要“把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的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36) 托尔斯泰试图用文学艺术改造社会尽管带有空想的性质,但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中所包含的,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相合的真谛却值得反省:在弘扬理性、科学精神的时代,不要忘却对人的最本真的情感世界的陶冶。 ①(16)(17)(18)(26)(27)(31)(34)(36)《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第399页,第406页,第267页,第271页,第172页,第5页,第273页,第324页。 ②奥夫尼相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张凡琪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433页。 ③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托尔斯泰》,中国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④刘宁、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31页。 ⑤刘殿爵主编《白虎通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55页。 ⑥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3页。 ⑦《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⑧⑨⑩(30)Л.Н.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 (в90тыхтомах)М.1958 .том. 53 стр.7779;том. 48, стр. 51 ; том. 51. стр.96 ;том.42,стр. 315. (11)(14)(15)(29)(33)《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70页,第157页,第162页,第176页,第206页。 (12)参见廖小平 《道德认识论引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0—202页。 (13)《老舍谈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第91页。 (19)(21)(22)Н.ГусевА.ГольденвейзерЛ.Толстойимузыка М.1953, стр.1. стр. 6 ;стр. 13. (20)(23)(24)《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第99页,第96—99页,第252页。 (25)参见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卷第5章。 (28)参见托尔斯泰《复活》,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卷第21`章。 (32)参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卷第6章。 (35)《托尔斯泰论创作》,戴启篁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