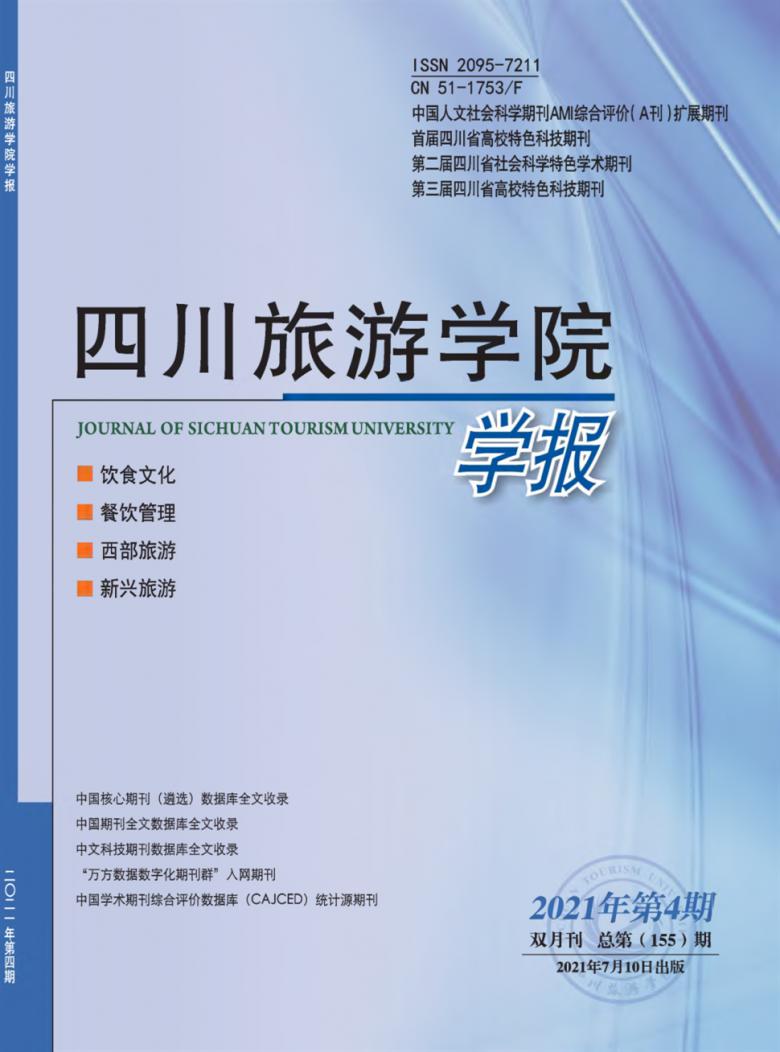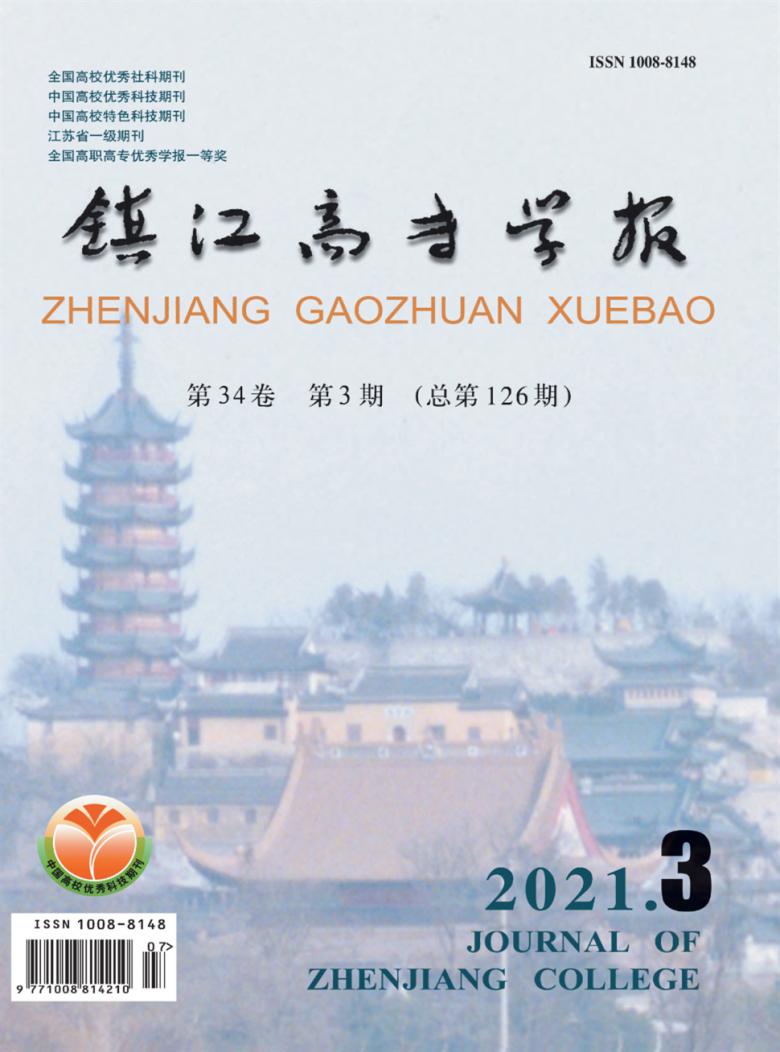影响唐代死刑适用的法律观念分析
未知
【内容提要】唐代的死刑适用相对于其他朝代比较克制。法律观念对死刑适用的影响不容低估。慎刑观念主张“惟刑之恤”;公平观念倡导“平恕无私”、“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理念”;礼刑迭相为用观念则强调斟酌情理,结合礼刑,因时制宜。这些法律观念,不论是对于司法官员,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都是一种约束力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刑法的运行轨迹,影响着唐代死刑适用的状况。
【关键词】唐代 死刑适用 慎刑观念 公平观念 礼刑迭相为用观念
唐代的死刑适用相对于其他朝代比较克制。通过整理引日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全唐文》中记载的死刑案例可以发现,唐代司法中被实际适用死刑的,相当数量集中在“十恶”罪中的谋叛以上重罪,在笔者收集到的全部适用死刑的案例中约占50.6%;官吏因赃罪被适用死刑的约占16.3%;因其他各类犯罪被适用死刑的约占33.1%。⑴在某些“治平之世”,死刑适用的数量甚至相当少,深为史家所称道。如“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三十九人。刑轻而犯者少,何其盛也?”[1](P51)“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尝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余人,惟二人合死。’”(《旧唐书·刑法志》)“玄宗开元年间,号称治平,人罕犯法。二十五年,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1](P51)在查处地方官吏违法犯罪过程中,因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的比例也不高。例如唐太宗二十年,“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人”。[2](P2)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取决于唐代立法上对死刑的简省;另一方面,法律观念对死刑适用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英国历史法学创始人梅因指出:“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或多或少地是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他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之处,但永远存在的局面是要把这个缺口重新打开。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人们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或程度”。[3](P15)这是对法律规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发展现实这一现象的经典表述。不仅如此,法律与社会之间还存在着有限性和多样性的矛盾,法律本身存在着抽象性和模糊性的局限。上述这些因素,为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挥各种作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法律适用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可能不会有个人理念的加入,突出表现在死刑适用出现立法空白和争议的时候,它能够起到填补立法空白、指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对唐代死刑适用影响较为显著的法律观念主要有:慎刑观念、公平观念以及礼刑迭相为用观念。
一、慎刑观念
慎刑观念是儒家推崇、倡导的刑法观念。该观念主张不惟刑,不尚刑,省刑法,缓刑罚;倡导刑法的紧缩与清简,刑罚的慎用与节制;强调对司法官治狱用刑严加约束,对死刑严格控制。
慎刑观念得到了唐代统治者的崇尚与践行,这一点后来受到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肯定和赞誉。沈氏有言:“综论有唐一代,除武后之时、李林甫之时及甘露之变、清流之祸,并由于阉宦之肆孽,其余诸帝,无有淫刑之逞者。贞观、开元之治,代宗之仁恕,无论矣。德宗之猜忌无恩,然用刑无大滥。宪宗之英果明断,然用刑喜宽仁。穆宗之童騃,然颇知慎刑法。”[1](P53)
慎刑观主要包含“慎于制刑”和“慎于用刑”两个方面。这种观念对唐代死刑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统治者认识到“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贞观政要·论求谏》)立法要“务求宽简,取便于时”。(《资治通鉴·唐纪十》)事实上,早在“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太宗尤其注重对死刑的限制,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旧唐书·刑法志》)杜佑给予高度的评价:“圣唐刑名,极於轻简。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条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递减唯轻。开辟以来,未有斯比”。(《通典·刑法八·竣酷》)经过渐次的修改,唐律从结构、体系、内容等方面渐趋合理,以致被后代模仿。
唐律一方面大幅削减死刑条款,“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旧唐书·刑法志》)死刑的执行方式法定为绞和斩,祛除了前代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还限定死刑适用的对象等等。另一方面还创设了死刑适用的两个特殊制度:
其一是死刑覆奏制度。史载:
其后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旧唐书·刑法志》)
其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过度刑讯的现象设置了死刑案件平议制度。史载:“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议之。”(《旧唐书·刑法志》)此项制度的设立,不仅使审判得到了有效的监督,由于多方参与,集思广益,也为纠正和减少重判、错判提供了条件。
依据慎刑观念,制刑之本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尚书·大禹谟》)“辟以止辟,乃辟”。(《尚书·君陈》)更强调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即刑以去刑,而非以刑止刑。这种观念对于司法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制约。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曾对盾代法律的适用有论:“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册俱在,徒虚器耳。”[1](P51)尤见司法典狱之官的重要性。唐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司法官应讲求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唐律疏议·断狱》)具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以情审察情理;第二,不任喜怒,严禁“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贞观政要·论求谏》);第三,不徇私情,一断于法。对待死刑案件的适用,力求慎之又慎。
例如《唐会要·谏议大夫》载,永徽二年九月一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踰垣盗左藏库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而身行盗窃,命有司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认为:“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准诸常法,罪未至死。今致之极刑,将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遂“特为卿免其死”。萧钧从侧面说服高宗,不要“贱任命,任喜怒”,唐高宗也欣然接受。囿于的慎刑的法律观,高宗纳谏对卢文操免死,卢文操得以死里逃生。
又如《唐会要·定格令》载,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刑赏。古先圣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尧舜之典……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诏遂配流岭南。此所谓“惟刑是恤”,语本《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即考虑到刑罚可能滥用失当,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意,使刑罚轻重适中。重视人命,不轻率的判刑,尤其谨慎的判处死刑。如丘浚所言“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罪疑从轻可也,不疑然后杀之,如是则狱无不得之情,世无冤死之鬼矣。”(《大学衍义补·总论制刑之义(下)》)
唐代慎刑观念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以及道家的“元气”理论。儒家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贵生成”,人是万物之中最具有灵气的,“万物之灵,莫大于黔首”。天人是合一相通的,“人通于天也,天应予人也”,(《全唐文》卷二一三)人是天的副本,天之所贵,就是人之所贵。因此,世间最大的功德就是使人能够生活下去。然而,“茫茫率土,蠢蠢群生,贤愚中余,具伪相倾,如鸟之惊,不能不犯”。(《全唐文》卷二二六)这就是说,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刑罚的适用,是“盖非获己”,也就是“不得已而用之”。考稽于君主,一方面要“务胜残”,要致力于战胜邪恶的行为,惩罚犯罪之人;另一方面,还要十分重视养育百姓。总之,要做到“顺天顺人”,才能称作是“理”。同时,还要务必防止出现“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人愁”(《全唐文》卷二一二)的被动局面和负面影响。
同时,唐朝也是我国历史上道教盛行的一个时代。因为道家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于是李唐一族就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将道教算做“本朝家教”。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即追认老子为“天下李氏始祖”,并于武德七年颁布《先老后释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即道家第一,用行政手段规定道家在儒家、佛家之上。贞观十一年,太宗李世民下诏称:“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全唐文》卷六)他还在《帝范》中说:“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明确以不劳民、不扰民为大唐执政原则。乾封元年,唐高宗李治始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称帝后追封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天宝二年,唐玄宗李隆基加尊号老子为“太圣祖太上玄元皇帝”。而且唐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尊道教为国教。基于此,唐朝统治者很注重阴阳之道,他们认为“元气”非常重要,武则天在垂拱初年就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何以道?”陈子昂立即上了《谏理政书》,提出元气“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全唐文》卷二一三)元气是统治的基础,阴阳因元气而相伴而生。因此如何维护元气和阴阳平衡是首要思考的问题。圣人告诉他们的方法就是“下务济人”,(《全唐文》卷二一三)“济人”则“人安”。因为,“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全唐文》卷二一三)于是“人得安共德乐,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已和,元气以正,天瑞降,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全唐文》卷二一三)他认为这是“至理也”,是一个不断的良性循环,可以使统治万古千秋。对于刑罚适用来说,首先要“贵适时变,有用有舍,不专任之”。(《全唐文》卷二一二)惟其如此,阴阳才和谐,元气才正位,否则就阴阳失调,元气不正,就会“群生痢疾,水旱随之,则有凶年。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全唐文》卷二一三)
二、公平观念
公平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观念,可表述为“公”、“平”或者“公平”,“平允”。宣传“平恕无私”、“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理念。正如陈澔在《礼记集说》中曰:“天之理至公而无私,断狱者体而用之,亦至公而无私。凡有罪责而当诛罚者,必使罚与事相附丽,则至公无私而刑当其罪矣。”《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战国策·秦策一》:“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公平观念是唐王朝治世与用法的一个基本理念。《贞观政要·论公平》中唐太宗明确指出:“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称:“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他坚持认为治国要以天下为公,不能有私心。贞观元年,有人要求授职于秦府旧兵时,太宗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论公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事实证明,不公平行事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诉求或政治局面的混乱。“背公向私,其伤则多,为政必紊”。(《全唐文》卷二七)因此,治理国家、适用法律必须公平合规矩,坚持同一标准,平等要求,做到正而不偏,平而不倾,直而不曲。
例如《贞观政要·论公平》记载,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校尉、长孙无忌都因过失而得罪,依律都当处死,然而对他们拟适用的刑罚悬殊极大,一生一死,严重违反了“事既同科,法当均罪”的规则,极不公平,因而受到戴胄的极力反对。之后,出于公平的考虑,在长孙无忌因亲而赦免了死罪的情况下,也免去了校尉的死罪,这样对校尉来说,才是公平的。
唐《考课令》中规定了“四善二十七最法”,其中“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所谓“处断平允”,即要求司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应严格秉承“平恕无私”、“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公私观念。魏征引用汉朝杜恕《体论》作了精辟的阐述:“夫窃盗,百姓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百姓不以为暴,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循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反之,私之于法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贞观政要·论公平》)其意是:刑罚适用只要公平,即使有所偏失,或重或轻,都不会招致抱怨;强调公平对法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刑罚适用就不公正,其结果就是放纵为非作歹的人或者是伤害良善的人。这深刻地揭示了公平对刑罚适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杜佑也主张执法者当“以至公为心,至平为治,不以喜赏,不以怒罚。”极力避免“杀戮过差,及于非辜。”例举汉代张释之犯跸一案,指出“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或因之淫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贞观政要·论择官》)李乾祐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判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便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帝意解仁轨竟免罪。”(《册府元龟》卷六一七)裴仁轨因犯轻罪而要被处以死刑,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李乾祐据理力争,他才幸免于难。
公平适用刑罚还体现在“法不阿亲贵”,“罚当其罪”,要力图避免“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贞观政要。·论择官》)避免“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贞观政要·论刑法》)例如《册府元龟》卷六一七载:
上元二年九月,(狄仁杰为大理丞)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并为斫昭陵柏木,大理奏:“官减死外并除名”,帝特令杀之。仁杰执奏称罪不当死。帝引入谓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须杀之”。仁杰又执奏,帝作色令出,仁杰进曰:“……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且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 适用死刑上所要追求的“公平”就是“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全唐文》卷三二九)“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欢悦,见详刑之意”,(《全唐文》卷二七二)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令肃如秋,化行如春”(《全唐文》卷五五),法律得到执行,社会秩序井然。
总的来说,公平适用死刑及其他刑罚,对于司法主体来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信任司法的起码的条件;同时,还是死刑判决能够被顺利执行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
三、礼刑迭相为用观念
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称:“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刑之所以生,本以遏乱,礼之所利,盖以崇德”。(《全唐文》卷二一三)作为行为规范,礼与刑对于统治者来说同样的重要,“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礼通过内心的修养,规范的教化,对人进行积极的引导,教人向善;刑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们为非作歹,相比之下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圣人、君主通过制定礼来约束人的内心,通过立法来预防有害的行为。“然后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此,社会就可以稳定和谐。(《全唐文》卷二一三)礼和刑性质、功能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般无二的,两者关系密切,迭相为用。对此,白居易对“礼刑道迭相以为用”作了深入的阐述:
臣闻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之以刑,其辟也则莳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然则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并用亦不可也,在乎举之有次,措之有伦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后劝惧,莫先后刑;划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宏礼;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亦如祁寒之节,则疏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则远火而狎水。顺岁候者,适水火之用;达时变者,得刑礼之宜,适其用,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将欲较其短长,原其始终,顺其变而先后殊,备其用而优劣等,离而言之则异致,合而理之则同功;其要者在乎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达其理而已。(《全唐文》卷六七一)
这是历史上对礼与刑独自各具功能最为经典的描述。白居易突破了历史上儒家“德主刑辅”之见,认为:刑、礼与道作为治国的规范都是维护君主统治的,要结合适用,“废一不可也”;同时还要因时因地制宜,“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事半功倍;最终能够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暴礼不作,廉耻以兴”,(《全唐文》卷二一三)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同时道德风尚也蔚为大观,这样的社会才是“治”的社会。
对于某些事涉伦际纲常的案件,可能会出现礼与刑的规定相矛盾的情况,“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如果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刑法的角度来处理都不合适,所以,对待这种情况唐代统治者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这一点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一些复仇案件与孝子案件上。但是,正如韩非所说:同类案件“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全唐文》卷五四八)司法者往往是对这类案件临时进行集议,权衡时局而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可能会各有所偏重。或者为了巩固政权,国家通过对复仇、孝子等的赦宥,彰显孝的意义,从而教化人民,以达到“忠”之作用;或者为了强化社会的稳定性,使更能呈现法治的效果,于是对复仇、孝子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4](P236)
其一,折中礼刑而偏重于依礼处断。
例如“莫诚救兄”案。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时,“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依据唐律规定:“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内死者,依杀人论。”柳宗元在《上桂管观察府状》中指出:“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于深衷,周身不遑于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文献通考·刑九·详谳》)按照唐律,用器物殴伤他人,又在保辜期内死亡者,应以死刑论处。虽然法律这样规定,但柳宗元还是希望开脱莫诚的死罪,其彰显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用意十分明了。
又如“康买得救父”案。穆宗时,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康买得被赦免了死罪。(《册府元龟》卷六一六)
再如,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旧唐书·列女传》)
其二,顾全时局依法论处的情况。
例如《旧唐书·孝友传》载“张理张诱兄弟为父报仇”案: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寉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斩之,籍没其家。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待御史,改名万顷。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乃下敕曰:“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哗谊议,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在本案当中,杨汪之所以杀张琇、张瑝兄弟的父亲张素,原因是张素犯了军法,并非是出于私仇,因此按一般道理来讲,张素应该是罪有应得。然而,张氏兄弟却心怀旧恨,长大后,终为父报仇。在定刑期间,有人以“申为子之志”为之开脱,有人则要求“法在必行”,争议颇大。但出于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考虑,就严格按照唐律规定,判处张理等兄弟死刑。
又如《全唐文》卷三五所载余常安复仇案。“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
可见,在死刑的适用上,唐代的司法者已认识到必须因时因人而宜。作为法律。死刑虽然有其明确的范畴与内在的规定性,但在量刑时,它与伦理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罪与恶的判定中,必须考虑社会现实需要,斟酌礼刑,以谋取平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慎刑观念、公平观念以及礼刑迭相为用观念,在唐代,不论是对司法官员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都是一种约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刑法的运行轨迹,影响着死刑适用的状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与
⑴笔者在进行司法部项目“传统的慎刑观与死刑控制”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全唐文》记载的唐代司法中适用死刑的案例进行了归类与分析。这些案例主要涵盖了从唐太宗至唐武宗时期,包括了唐代上升时期、全盛时期、衰落时期。但为了方便起见,舍弃了高祖时期、武则天主政时期和唐末的案例,主要因为这三个时期不是唐代的正常时期,不能够反映唐代司法的常态。参见杨二奎:《唐代死刑适用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3—20页。
[1][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日]西田太郎.中国刑法史研究[M].段秋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