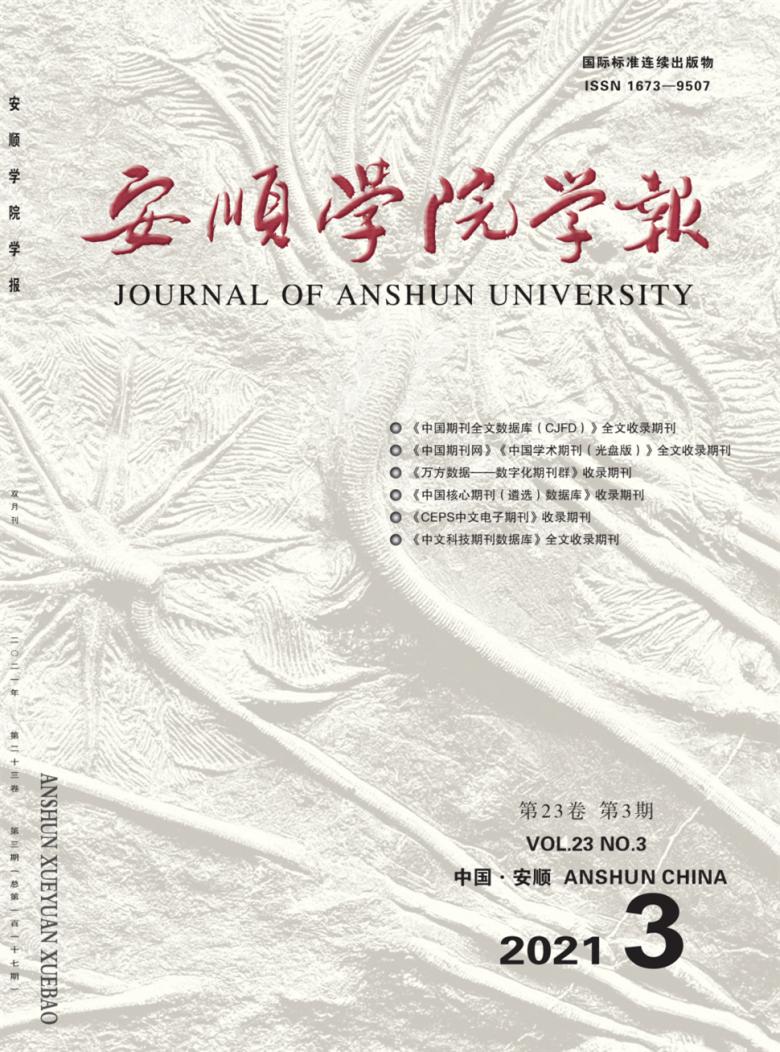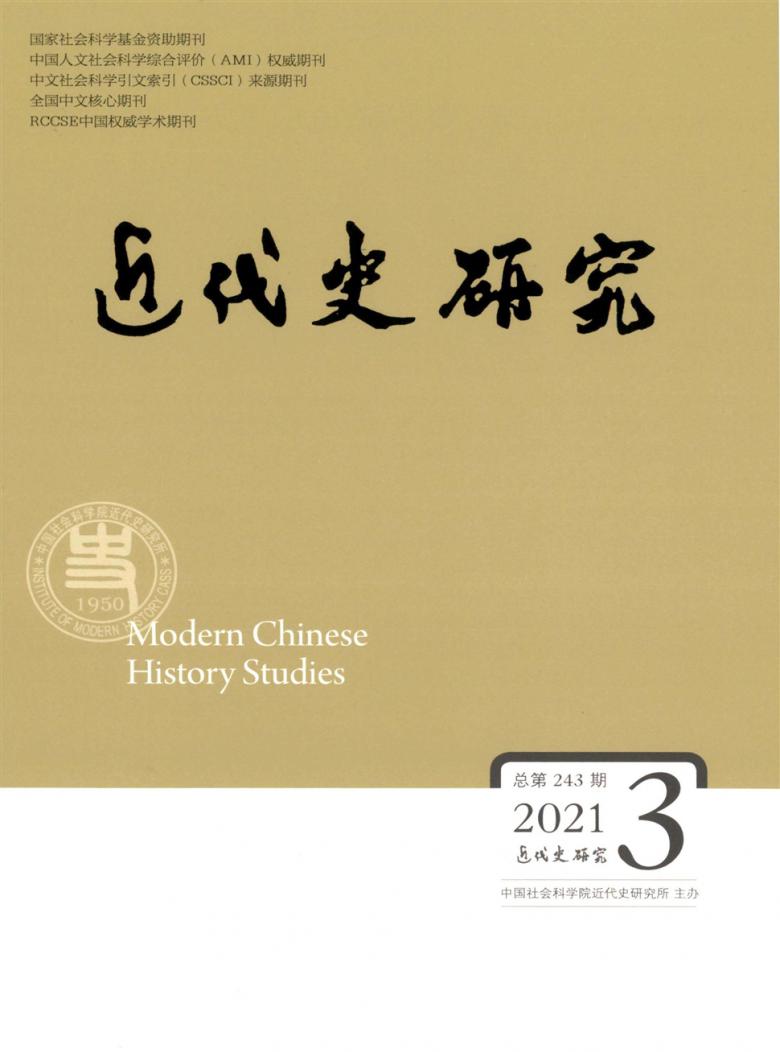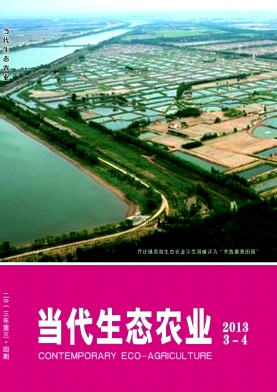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
佚名 2006-04-20
市场源于分工。但市场一词,因所论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概念。本文目的在探讨十五世纪以来我国国内市场变化对于资本主义发生和的作用。因而可定义为:商品流通形成市场。商品流通的量决定市场的大小,商品交换的决定市场的性质。
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前提。”[1]①在西欧,由于日耳曼人的征服和城市的破坏,进入封建后,商业大大衰落了,封建领地变成彼此孤立的庄园。到十六世纪以后,民族市场和世界市场形成,才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在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制割据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商业一向比较发达。但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不是较早,而是萌芽较迟、发展甚慢。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迟缓,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去寻找原因;另外,也有流通上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流通都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是要看这种流通,能否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市场,能否为生产积累货币资本,在这样的非海上贸易国家,还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
一 我国封建社会的各级市场
我国的封建商业,在宋代有了飞跃的发展。它打破了坊市制,形成各级市场。下面就按照各级市场,考察一下流通的作用。
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贸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十分发达的一种交易形式。宋代的墟集、草市已颇具规模,其税收几占全部商税之半。然而,和西欧所称集市不同①我国的墟集基本上都是地方小市场,范围不出一日内往返里程。这种市场上的交换,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内的交换,它的一定的发展,不是破坏自然经济,而是巩固自给自足。这种交换,虽采取商品形式,但是为买而卖,实际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虽也经商人之手,但除临近大城市水陆要道的一些草市外[2]②,实际上没有什么流通的作用。只是在后来,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小地方小市场逐渐有了大宗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以至成为真正的初级市场,其性质才有所不同。这种变化,是在明代在江南某些丝的集中产区开始出现的。
第二,城市市场。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发达的一种市场形式。宋代的汴京和临安,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所记述,已达高度繁荣景象。然而,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同,我国的封建城市,原来都是各级政权统治的中心,或是军事重镇,集中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手的生产也主要是供城市居民的消费。[3]③因此,城市市场上,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以及他们的工匠、隶役、士兵、奴仆)用他们的收入来购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而他们的收入,基本上不外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即农民的剩余产品。[4]①所以,城市市场的繁荣,主要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剩余产品和地租量的扩大),并不代表真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交换中,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单向流通,而没有回头货与之交换。这种流通大体包括三个内容:(1)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2)城居地主引入城市的地租;(3)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润或利息。这三项,无论采取实物或货币形态,家村每年都要把同值的产品输往城市,而不能从城市取得商品来补偿。这种单向流通造成城市繁荣,但由于没有商品交换,它实际不是商品,不是商品流通。
我国城市市场这种消费性的特点,双使得它特别发展了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象宋代《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都是这种商业。这种商业自然也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资本,但是,与那些经营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大商人(如后来的微商、山陕商、粤商)是不可比拟的,并且,直到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城市零售商业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饮食、服务业当然更不是了),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5]②。因而,这种商人资本尽管发达,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作用是不大的。
但是,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在沿江、沿海等商路要道上,逐渐会兴起一些新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市场,反映真正商品的扩大,其作用就不同了。宋代已有许多商业城市出现,不过,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明州、秀州等,反映海运贸易的发展。经元代大规模修建水陆驿道,到明王朝,国内市场的新兴商业城市才有比较显著的发展。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概念中的市场,以及多数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地里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此,区域市场内的流通,一般并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或社会分工。这种区域市场,可视为农村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指农民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在我国小农经济中,那几种是不可能的),它实际是指社会是由许多的“单一的经济单位”所组成,而全部或大部分再生产条件,都能在本单位中得到补偿。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在古代是指氏族、村社、奴隶主庄园,在中世纪的欧洲是指一个个的封建领地;在我国的地主制经济中,则应是相当于过去采中邑的乡里或区县,并且是包括地主和农民两上方面,不是单指农户。[6]①
不过,区域市场范围内的流通,究竟已不限于单一的经济单位,而至少是各单位间的商品交换,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了。尤其是一个区域总包括一定的城镇,区域市场内的城乡交换,反映一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这是应予充分注意的。这里,重农学派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形式市场”这一古老概念,对我们研究的目的来说颇有用处。因为这和交换代表真正的社会分工,也是自然经济瓦解的前兆;并且,市场的由小而大,也常是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参加交换的结果[7]①。我国城市手工业者由承接顾客来活的手艺人向小商品生产者的转化,是在明代才显著。区域市场的重要性,也自此始。但总的说,我国区域市场内的工农来产品交换并不多,因为农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而城市手工业又主要是供应城市消费。这种情况,直到清代前期,没有根本变化。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一个区域市场的自给自足,在某种势力下,也会成为封建割据的依据,以致关卡封锁,阻碍流通。边远省区尤多这种情况。
第四,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这种市场,和形成这种市场的长距离贩运贸易,才是促进资本和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海外贸易,也是一种大市场,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是在海外贸易的基地出现的。但我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国家,明清两代又受禁海政策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我们的考察,一般也限于国内市场。
我国长距离的贩运贸易很早就有发展。但在宋代以前,除了官营和专卖品外,发展最盛的是那种“奇怪时来,珍异物聚”[8]②的奢侈品贸易,其次是由“任土作贡”遗留下来的土特产品的贸易。这两种贸易经营的都是已生产出来的(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东西,其消售对象又限于贵族、官绅小范围,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所以尽管琳琅满目,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却极少作用。大约从明中叶起,我国的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又很早就有盐、铁以及渔、猎产品的贸易,其中也大部分是长距离贩运的。这种贸易,除有些是受官府控制外,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从生产上看,盐民、炉户、渔民、猎户等都可说是小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们这种地位纯粹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9]①。他们是由于盐、铁等不能当饭吃才进入交换的,为买而卖,目的在取得口粮。因此,我宁愿称他们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而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事实上,自有自然经济,就必须有盐、铁等贸易作补充,否则也谈不上自给自足。[10]②这种贸易,乃是自然经济题中应有之义;除非它们生产方式改变,对我们研究的目的来说并不起多大作用。
盐铁以外的民生用品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主要是从明代开始的。这就使得我国国内市场,在市场结构和交换性质上,发生一种定向性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本文的目的即在考察这种变化,同时也要说明其变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市场,从来就有个量的内容。但是在明代史料中,还很难进行定量的。本文只能从商货路线的增辟、新商业城镇的兴起、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商人资本的积累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也尽可能提出一些量的概念,而撇开那些“舟车鳞次”“店肆栉比”等无具体内容的。以后关于清代市场的考察中(它将成为本文的续篇),我希望尽可能作一些计量分析,并试图探索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的结构。
对于市场和商品流通的上述观点,只是个人在中不成熟的看法,谨先缕出,以求教于贤明。
二 商路的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
二十世纪铁路修筑以前,国内商运主要是靠江河和沿海水运。长江历来是我国最重要的一条商品流通渠道。宋代的长江贸易主要是集中在下游。明初也还是这样。宣德间,明廷设三十三个征收商品注通税的钞关,其中十五个在长江沿线,即上游的成都、泸州、重庆;中游的荆州、武昌;而有十个集中在下游,即扬州,镇江、仪征、江宁、常州、苏州、嘉兴、杭州、湖州、松江,并限于江、浙两省。但在正德以后,钞关剧增,芜湖、宁波成为新兴商业城市,就是说,这个最繁盛的贸易区向东南两方面延伸了。长江中游的荆州、武昌,本来都是军政重镇,武昌虽已“四方之贾云集”[11]①,但比清代的汉口镇还相差远甚。不过一明后期,沙市、九江成为新兴商业城市,这样就与长江下游珠连起来了。这是一个重要。至于上游的成都、泸州、重庆三钞关,主要还是处理本区域贸易,这时无粮食出川,与下游主要是丝、茶等细货贸易,贸易量有限。
总之,明后期长江贸易有了发展,不过主要还是在下游和中游,这主要是由于江、浙两省桑、棉和手的发展所致。这时两湖丘陵地带和川、滇尚未大力开发。据我看,明代国内市场的开辟恐怕更重要的是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畅通,以及沿赣江南下过庚岭到两广一路的开通。
大运河自元代开会通河后,补救了黄河改道的困难。但元代漕粮仍以海运为主。明永乐九年(1411)重开会通河,运河才畅行无阻。运河原为漕运(不属商品流通),但官船都带私货,而商船亦可包揽一位官员剩坐,即可沿途免税,所谓“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盐,凭官附势如火热,逻人津吏不敢诘。”[12]②所以实际是一条重要商路。
大运河自北京(通州)至杭州全长一千余公里,河漕(利用黄河一段)以下,航运尤繁,并由河漕东走济南,西走开封。明初人孙作说:“自杭走汴,水陆二千里,如游乡井,如入堂奥,如息卧内。”[13]①宣德间,沿北河在北京、德州、临清、济宁和济南、革封设六个钞关。其中临清是元代兴起的商业城市,济宁又是明代官商会聚之地。中叶以后,北部的天津、南部的淮安,又都是新兴商业城市。又有通州和天津之间的河西务,临清和济宁之间的张秋镇,成为新兴商埠。再如北直隶的中定、清苑、河间、景州,虽不是临河,但也因漕运关系,“商贾肩相摩”[14]②。又如山东的清源,原属荒村,正统间因战事筑成,但随着淮北水运的发展,到嘉靖时就又筑新城,成为“商旅往来,日夜无休”[15]③的商业城市了。
明初,赣江水运已颇盛,设有南昌、清江、临江、吉安四个钞关。其后,九江设关;饶州、景德镇商旅日繁;而铅山县的河口,由二、三户人家“而百而十”,到嘉、万时已“舟车四出,货镪所兴”,成为“铅山之重镇”[16]④。赣江贸易的发展,又是和大庚岭山路的开修分不开的。这样一来,赣州成为一大商业城市,庚岭路上,“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17]⑤,和苏轼过庚岭时“一夜东风吹石裂”“细雨梅花正断魂”的景象不大不相同了。
明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8]①南北货运的流畅,大约是明代市场扩大的一个特征。下面在叙述商品运销中,还可见到。不过,明代运河贸易的发展,多半还是因为中心在北方,以及北边多事、行开中制等原因;南货北运者多,北方出产有限,故漕船常回空。因而,这种市场的扩大,并不完全反映地区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是长距离贩运的主要商路。此外,如北边宣化,主要是两淮、长芦盐运集中地;湖北襄阳,主要是西南木材集中地;各有局限性。西北太原、平阳、蒲州,早设钞关,但主要是处理本区域贸易。后期发展起来的西安,则“西入陇蜀,东走齐鲁”[19]②,使西北商路稍畅。更远的到辽东一路,商货多由山东临清转运,限于细货,为量有限,而海路在明代反衰落。近人常引宋应星“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那显然是夸张了[20]③。
县以下商业镇市的兴起,却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些镇市,除上述河西务、张秋、河口等外,都是在作物和的手工业品商区,货量不太多,但都远销,实际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起点。不过,大都是集中在江、浙一隅之地,如苏州的枫桥,湖州的菱手工业镇市。如苏州的盛泽镇,明初是五、六十家的村,嘉靖时成为百多家的市,居民“以绫紬为业”[21]④;震泽镇,元时仅数十家,嘉靖时已七、八百家,“竞逐绫紬之利”[22]⑤。嘉兴的濮院镇,万历时“日出锦百匹”,“人可万家”[23]⑥。这些镇上的居民已由农业分离出来,或者虽未分离但也是为市场而生产了,这些地方就成为商品生产的基地,商贾云集。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多”[24]①。七千多家,多数不耕地、不绩麻,不从事自给性的生产了。因而“国方商贾俱至此收货”,“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25]②。
最后,结合海外贸易,看一下福建、广东的海运。
我国海外贸易在宋代有较大发展,通商五十余国,进出口商品数百种。明代丝织、瓷器、棉布、漆器、糖等出口品的生产都有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宋代基础上也有改进[26]③,正是发展海外贸易的良了时机。但是,明开国之初,即严海禁,“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寘之重法”[27]④。虽设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所谓朝贡贸易,对外使横加限制,两三年甚至八年十年始准来华一次。永乐后,驰禁之仪屡起,但总是以禁为主。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种政策不能阻止经济发展的要求,私人海上贸易并未断绝,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则是肯定的的。
明代的海外市场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南洋有二商路,称大西洋和东洋。大西洋以越南(安南)、柬埔寨(占城)、暹罗为主,进口主要是苏木、胡菽、犀角、象牙等天然产物,而出口则以工艺品为主,以及铜、汞等矿产品,这又是贸易上的一个有利条件。东洋指吕宋(佛郎机),进口品种有限,多是以银换取中国物产。外贸利润很厚,“湖丝百觔,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28]①。输往日本者,更多系日用工艺品,丝绸、瓷器之外,棉布、布席、扇、脂粉等都能畅销。明庭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因而在贸易上“东之利倍蓰于西”[29]②。
明代的海外贸易,由于正德至嘉靖间一度严格海禁,到万历以后才有较大增进。这对广东、福建两地经济颇有。明代经济作物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又接近江、浙手工业产区,外贸中心也由南宋时的广州移到福建来了。万历时,有人说:“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延之铁,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30]③话虽如此,福建的商品性生产,究竟运销海外的只是一小部人,大部分是运销售内陆以换取粮食。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二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31]④,而南宋绍兴时广州市舶司的税收曾年达110万贯。明代的海外市场,恐怕是比宋代缩小了。
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大量借助于海外市场,在地中海沿岸和北欧低地,尤其是这样。当时我国开辟海外市场的能力,从出口商品看,从航海技术看,从郑和七下西洋的路线看,都是很大的。而明(以及清)王朝的禁海政策,起了很大的阻塞作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只能依靠国内市场。
三 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
市场扩大,只是商品流通的一个侧面,它的性质和作用,还要看进入流通的是什么商品,以及其交换的对象。明代长距离的商品运销,就我所见,重要的有:(一)粮食;(二)棉花和棉布;(三)丝和丝织品。盐和茶也是长距离运销的重要商品,但都属专卖性质,我把它们放在下节论商人资本中去考察。
(一) 粮食的运销
粮食是封建最重要的商品,不公因为它流通量大,而且粮食商品率(指对产量而言)的大小,是测量结构演变的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说,在考虑粮食的商品流通时,首先要排除田赋、加派等非商品部分。这以外,在封建社会,粮食的交易就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在区域市场内供城镇人口的需要。前者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实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供城镇人口需要的,也主要是来自附近的。粮食体大价低,原是不适于远销的。以明代而论,大约每年的漕粮和开中纳粟,已可供洋畿官吏、工役和北边驻军所需,此外并不需要南粮北调。有些地方,如河间府,需粮食调剂:“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皆辇致之。”[32]①这种有来有去的情况大约相当普遍,并且多半还是区域内的运销。较长距离的运销,主要是供应东南经济作物地区的农民和手者的口粮,也只有这种交换,最能反映地区分工的社会分工。这在明前期,尚未见记载,估计主要是明中叶以后起来的。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地区,常患粮食不足。不过,这个地区本来是鱼米之乡,有粮外运,宋人所谓“苏常熟,天下足”[33]②。到明后期,常州米仍然外调浙江[34]③,湖州米接济杭州[35]④,常山米取给于附近的玉山、西安[36]①,宁波米取给于邻府台州[37]②,就是说,区域内的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未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38]③。说“半仰食”可能夸大了,我们没有可靠材料,估计每年运入几百万石也就够了。
福建是经济作物发展最早的地区,这时烟草尚少,但甘蔗已普遍,又有茶、麻、苧、蜡、蓝靛、果木等。手工业也发达,前引《闽部疏》已见。和江苏、浙江不同,福建地多山陵,粮食本非丰腴,这样一来,必难自给。其中温州米运福州[39]④,尚属近距离调剂,甘蔗产地泉州,则需“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40]⑤。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米海运入闽,据说“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41]⑥,这就怕有上百万石了。况且,广东食米原是靠广西接济[42]⑦,而“盗载”(因朝廷禁海运)如此之巨,可见福建米缺。而自江、浙输闽之米,恐怕又多于广东。福建省大约可以说是当时自然经济受到破坏最多的省份,但也是全国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省份。
安徽南部的徽州一带,是个茶、木材和纸、墨产区,其土地贫瘠,粮食不足。这个地区虽小,购买力则较高(大约经商之故),粮食运至颇远,在明后期,“大半取给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贾从数千里转输。”[43]⑧
以上是粮食输入的主要地区。
粮食输出的地区就我所见资料,只有两个。一是江西南部。“赣〔州〕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44]①”另一个是安微江北一带。“六皖皆产谷,而桐〔城〕之辐舆更广,所出更饶。计繇(由)枞(川)阳口达于江者,桐者十之九,怀〔宁〕居十之六,潜〔山〕居十之三”[45]②。这两个地区都米谷丰饶。到近代还是这样。不过供应江、浙需要,恐怕还未足(赣米还要供应本省南昌)。长江中游一带即湖广的米,在明后期大约已有东运,唯史料未详,或者数量还有限。
总看上述,明代商品食的运销,主要还是在长江下游,即九江以下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其中又很多是本区域内部调剂。象清代的湘米大量东运、川米出川、东三省豆麦南下等大规模运销,明代尚未出现。在明后期,较长距离的粮食运销,包括广东米北上,恐怕不超过一千万石。按嘉靖间米价每石零点八五两计,约值银八百五十万两。[46]③
粮食是农民个体生产的。进入长距离运销的粮食,部分是小生产者的余粮,大部分是来自地主的租谷。无论何者,都不是商品生产,而是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而使已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商品。所以,粮食贩运,是当时最大量的商品流通,但也是最典型的封建商业,在当时条件下,无助于改变生产关系。但是,粮食的长距离贩运主要是输往东南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区,它反映了后者的发展,并对这种发展起着保证作用。
(二) 棉花和棉布的运销
棉花的种植是在明代推广的,而这时农民织布还不普遍,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一带,因而棉花和棉布都有较繁的长距离运销。徐光启说:“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47]①”这是总的流向。
当时北棉南运,主要是河南、山东的棉花。万历间钟化民说。“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48]②。又有记载说南阳李义卿“家有地千亩,多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49]③。这是河南棉花。山东植棉,“六府皆有,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溥。”[50]④东昌府的棉花以高唐、恩县、夏津为集中地,“江淮贾客,列肆齍收”[51]⑤。兖州府也多棉,“商贾转鬻江南”[52]⑥;而郓城是另一集中地,“贾人转鬻于江南,为市肆居焉。”[53]⑦
江苏省太仓州所产棉花,也向南贩[54]⑧,而嘉定的新泾镇,遂为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55]⑨。不过,太仓州的棉花不少是运销福建。福建在宋代是最早的值棉区,到明代则甚少栽培了。“隆万中,闽商大至〔太仓〕州”购棉,吴梅村曾咏其盛况[56]⑩。
江西棉花,生产未详,但有棉经大庚岭运销广东。广东惠州,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57]⑾。明代湖广的江花,产量亦丰,但少见外销记载[58]⑿,可能有运往广东者[59]⒀。
明代棉纺织业,集中在松江、嘉定、常熟三地,有松江布、嘉定布、常熟布之称,而以松江产量最大。但松江府原系产棉区,从后来产布最盛时情况看,其所需棉花可以自足,并有余花供毗邻的浙江嘉兴、嘉善一带织户。由北方南运的棉花,大约主要供应滨海各县,那里农民也多织布 。嘉定位于太仓州产棉区,棉花亦可自足。常熟缺棉,大约须由北棉接济。
松江布的运销,叶梦珠《阅世篇》所记最详。他是记清初上海县(属松江府),但兼及明代;“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得曰标布,……俱走秦晋、就是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为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中机客少,资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无几。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全,少年或二、三千斤,利亦微矣。而机之行转盛,……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又忆,前朝更有一种如标布色稀松而软者,俗名浆纱布,……今亦不复见矣。”[60]①
棉布是农民家庭分散生产的。由于商人收购,有了一定规格,又因销地不同,织成不同品种,说明松江的织户已多半是为市场而产生了如尤墩布 ,“轻薄细白”,用以制暑袜,属专用布。又有高级布,如三纱布、番布、兼丝布、药斑布等,多销京师,皇室、贵族所用[61]②,俱为量不大。明代松江主要商品布是标布,这是一种比较厚实、幅面较阔的布[62]③,销往西北和华北。清人褚华也说,松江“标布,关陕及山右诸省设局于邑收之”[63] ②,他的六世祖在明代即做棉布生意,“秦晋布商皆主于家”。浙北嘉兴,嘉善一带与松江相连,所产可能也是标布一类,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谚[64]②。
嘉定布,“商贾贩鬻,近自抗、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65]③。常熟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什六”[66]④。这两种布规格未祥,主要也是北销。
大约明代南方用麻布还相当普遍。麻主要产在南方,麻布也北运。棉布兴起,御寒较胜,首先在北方代替麻布。不过,福建、广东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棉布也已盛行。福建“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重”[67]⑤。但福建所产青麻布,“商贾转贩他方亦广”[68]⑥。福建惠安的北镇还有一种精制的布很有名气,“北镇之布行天下”[69]⑦。广东,“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稜布、咸宁(在湖北)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但广东所产“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70]⑧。
其他地区,也有布贩售。乃至甘肃的“洮兰之间小民,制造货贩以糊口”[71]⑨。不过恐怕都行销不远,不赘述。
明代棉花、棉布的运销颇为活跃。但这并不说明已经有了高度社会分工或纺织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72]⑩,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棉纺织业生产力落后所致。我国汉族的棉纺织业本来发展较迟,又都是农民家庭副业,其推广落后于棉花的种植,所以要运棉就织[73]①。“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紝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74]②明末徐光启看到河北肃宁的织布业兴起[75]③,即预见到松江布北运将衰。果然,入清以后,如前引叶梦珠所说,在松江就“标客巨商罕至”,棉花南运自然也减少,甚至“东北绝无至者”。但松江的织布业并未衰落,因改向中南和东北销售,反达最盛。
还应看到,我国手工布的生产,从来不是家家纺织的,据考察农村织布户最多时(十九世纪中叶)也不超过全国农户的一半,因而,他们生产的布总要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拿出来卖给非织布户,以换取口粮。这种粮布调剂,正是我国小农经济耕织结合的一种形态。这里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商品率”是一种虚假现象。因此,我总是把重点放在长距离运销上,这种地区间的运销才代表真正的商品流通[76]④。在它的集中产区,即松江一带的织户,才大体可以说是小商品生产者。松江府的棉布上市量,在清代盛时年不超过三千万匹[77]⑤,以此估计明代约不超过二千万匹,按每匹一钱六、七分计,约值银三百三十万两。
注释:
[1]① 《资本论》第三者卷,第167页。
① 十一世纪以后西欧集市的兴盛,主要是为了逃避城市行会的限制;集市是大商人集中进行批发的、集中的贸易的地方,大集市都是国际贸易中心。
[2]② 王建:《汴洛纪事》:“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3]③ 西欧大陆的罗马城市,大部分在日耳曼人南下时荒废。封建城市,主要是十一世纪以后,由手工艺人和从庄园中逃亡的农奴和商人恢复蔌新建的。手者和商人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因而其市场上的流通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另有些城市是海外贸易的基地。在西欧,十六世纪初才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出现;我国则在唐代即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十余座,北宋时有四十余座。
[4]① “在亚洲各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在亚洲:“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马克思:《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6、474页。)
[5]② “商人资本的相对量……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但在这里,零售商人的资本作为一种杂种,是一个例外)”:不过,“随着商人资本越来越容易挤进零售商业,……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资本论》第3卷,第320、347页)。
[6]① “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产生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列宁全集》第3卷,第17页。)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毛泽东:《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87页。)
[7]① 农产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市场范围宜小不宜大,因运输里程增加一倍,常会使运费增加二倍。若是工业品参加交换,情况就不同了。因工业品运输费用所占比重不大,并且大量生产会降低成本,这就会引起市场的延伸。
[8]② 《管子·小匡》。中世纪欧洲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也主要是奢侈品贸易,但其主要奢侈品香料、丝绸等是来自东方,属于东西方贸易,正是这种贸易,促进了意大利、佛兰德等地城市的纺织、玻璃、五金工业和矿业的发展,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9]① 林正清:《小海盐场新志》。
[10]② 欧洲的领主制经济,也需要这种贸易作补充。不过,欧洲的庄园有较多的公用林区、牧地、渔场和狩猎场,有的领主还规定所属农民缴纳一定的盐和铁。
[11]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2]②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续编》卷一,马船行。所说是江浙马船,据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三,运河情况亦然。
[13]① 孙作:《沧螺集》卷二,郑淮南省椽梅择之序。
[14]② 查志隆:《金台郡城西北二桥记事》,载民国《清苑县志》卷五。
[15]③ 周思兼:《周叔认错先生集》卷五,二城记。
[16]④ 费元禄:《量采馆清课》卷上。
[17]⑤ 桑悦:《重修岭路记》,载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
[18]① 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借箸编。
[19]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20]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此语下文:“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其实是说信息传播,不是指。
[21]④ 嘉靖《吴江县志》。
[22]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卷二五,生业。
[23]⑥ 杨树本;《濮川所闻记》卷四。
[24]① 万能胶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
[25]② 《石点头》卷四。
[26]③ 明代出海以广船、福船、消船、沙船为主。广船、福船是尖底船,能用多段龙骨,创于宋代。沙船是平底船,用平板龙骨,靠两舷大擸(木字边)加固,宽敝,干舷低,稳性好,比较安全。沙船之名,明代始见,日本称南京,当是明造。但宋代即有防沙平底船。元明代的改进,大约在于用披水板(橇头)和升降舵,使船能逆风行驶。又这种船,元代载重达八、九千石,鑫桅多帆。明代一般载二、三千石;并由多帆改为二、三帆,帆下宽,以隆低风压中心;这都增加了稳性和灵活性。郑和下西洋大约即用沙船,其大者称宝船,长150米,张12帆。在船海技术上,明代改进牵星术,除北极星外,并观测方位星。又广用罗盘,创更香计时,制成方向与时间结合的针路图。
[27]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
[28]① 傅元初:《清开洋禁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
[29]② 王胜时:《漫游记略》卷一,闽游。
[30]③ 王世懋:《闽部疏》。
[31]④ 傅元初:《清开洋禁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
[32]① 万历《河间府志》卷四,风土志。
[33]②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常州奔牛闸记。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乙集、吴泳《鹤林集》卷三十九均作“苏湖熟,天下足”。
[34]③ 常熟“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于邑。”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
[35]④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州]……,人无担石之储”。《肇域志》第九册,浙江。
[36]①常山“米谷豆面之类,苟菲玉山、西安通权,则终岁饥馑者十家而七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37]② 宁波食米“常取足于台[州]”。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38]③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
[39]④ 福州食米“常取给于温[州]”。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40]⑤ 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志。
[41]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42]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
[43]⑧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平物价议。
[44]① 天启《赣州府志》卷三,与地志三。
[45]②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十八,稻部,引明方都韩:《枞川榷稻议》。
[46]③ 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皇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一、三一二,《云间杂志》卷中,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六,采九德《倭变事略》卷二零,所记嘉靖二年至四十五年米价平均,为每石零点八五两。
[47]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48]② 《救荒图说》,载《荒政丛书》卷五,钟中惠公赈豫记。
[49]③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七。
[50]④ 万历《山东通志》卷八。
[51]⑤ 《肇域志》第三十二册,山东。
[52]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十三,兖州府部,风俗考。
[53]⑦ 万历《兖州府志》卷四。
[54]⑧ “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中男子多轧花生业”。崇祯《太仓州志》卷五。
[55]⑨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56]⑩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韈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
[57]⑾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三○,惠州府部,物产考。
[58]⑿ 《花村谈往》卷二记有正德间“荆湖川蜀远下客商所带板枝花俱结算在主”一例,板枝药是絮棉,主指京口牙行主人。
[59]⒀ 广东“冬布鞋多至自吴楚,……与棉花皆为正货。粤地所产吉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葛布。
[60]① 叶梦珠:《阅民编》卷五,食货五。
[61]② 见正德《松江府志》卷五,正德《大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十七。
[62]③ 近代松江布分为标布(东套)、清水、销北方;东稀,销两广、南洋;北套、扣套,销南北二路。
[63]① 褚华:《木棉谱》。
[64]②雍正《浙江通志》引万历《嘉善县志》。
[65]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考,物产。
[66]④ 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
[67]⑤ 王院:《漫游记略》卷一,闽游。
[68]⑥ 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二,货殖志。
[69]⑦ 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志。
[70]⑧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葛布。
[71]⑨ 明《神宗实录》卷三○九。
[72]⑩ 只有福建的以精制的北镇布换江、浙江,广东的以蕉布换冬布,才是真正的地区分工。
[73]① 褚华:《木棉谱》说:北方“风日高燥,棉纳断续,不得成缕”,要在地窖中“借湿气纺之,始得南中什之一二”。乃至乾降《乐亭县志》卷五还有“女纺于家,男织于穴” 的记载。其实,这只是技术未熟练而已。后来事实证明,北方产棉区农户大都自已织布,而乐亭还是个小的棉布集中产地。
[74]② 王象晋:《木棉谱》,载《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
[75]③ “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初优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76]④ 这里还没考虑官布。明代除宫庭用布和赏赉用布外,最大量为军服用布,明初年平均在一百万匹左右,又西北易马的布每次十万匹左右。但官布并非都出自官课,尤其明后期,主要还是商人所贩。开中制的“纳布中盐”也是这样,所谓“秦晋大贾”其实很大部分是贩运官用布匹的。我这里都视同商品布了。
[77]⑤ 见本书《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