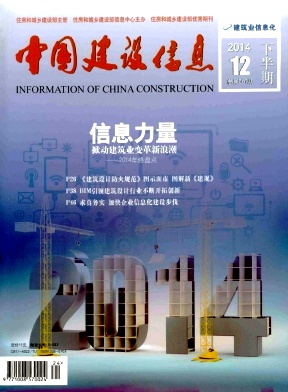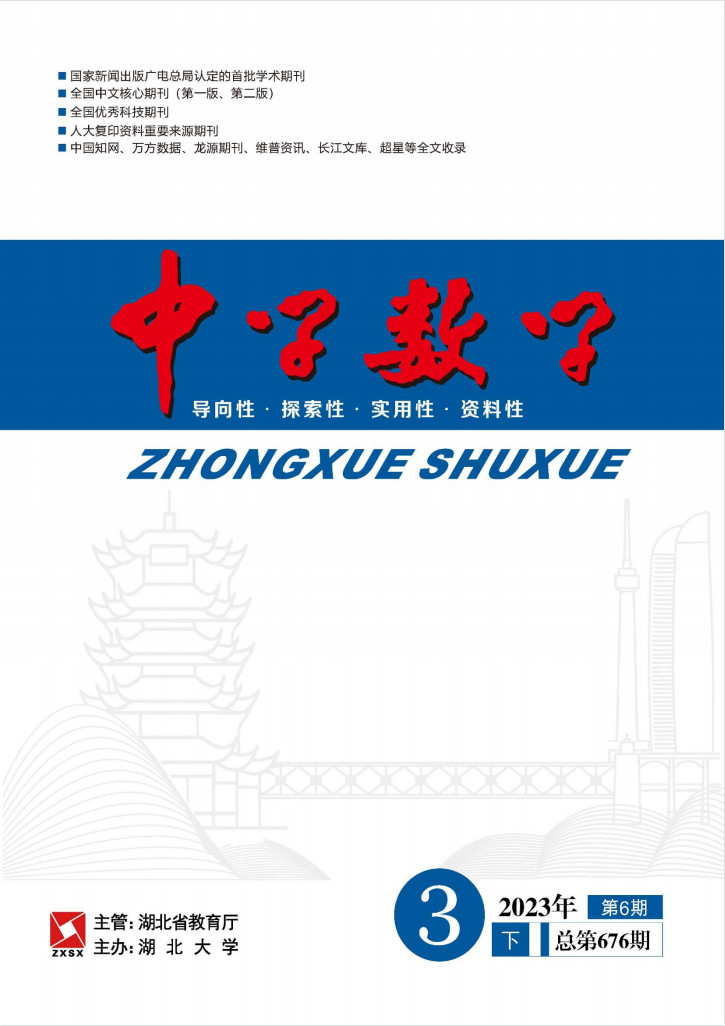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二)
佚名
(三)丝和丝织品的运销
织品的产地多在丝产区,但也因土地、技术等关系,有作为原料的丝的运销;尤其经丝,要求质量高,远销最多。
明代的商品丝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丝,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有人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多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山西〕潞〔安〕最工,取给于阆茧。”[78]①
湖州丝的贸易中心在归安县的菱湖镇,镇临苕溪,隆、万时,“四、五月间,豀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79]②。从这里南下杭州,北走苏州;销福建者,则多系闽商由苏州运去。湖州邻府嘉兴也是个丝产区,其贸易中心在石门,地临南运河,“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80]③其丝也走苏、杭。其实,苏、杭也都产丝,购湖丝多用于经丝。福建虽不产丝,也不专用湖丝。苏州丝还销往广东。广东也产丝,但要织精细的粤缎,则要用苏州运来的好丝。[81]④
阆丝是四川宁府诸州所产,不限于阆中。阆丝也不止贩运到山西潞安,也贩运到江、浙丝产区,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为它质量好,可能生产成本也较低。阆丝中有称水丝者,“精细光润,不减胡(湖)丝,……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绫绢,岁夏,巴、剑、阆、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苍溪,商贾贸之,连舟载之南去。土人以此为生,牙行以此射利。”[82]⑤
苍溪是保宁一县,临嘉陵江。改机是一种幅面较阔的品种,用阆丝可能因坚实。其实,潞绸也不仅用阆丝,并远取湖丝[83]⑥。阆丝又不仅销山西、江浙,大约也是成都著名的蜀锦的原料。[84]⑦
明代丝织业已甚发达,不产丝之地,只要有能工巧匠,如潞安、泉州、成都,也有著名的丝织品销往各地。不过,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还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如前所述,这里并形成几个丝织手镇市。对于这些城市和镇市的商业繁荣,史料甚多,但很少言及具体运销路线和品种、数量,这也是我国史笔不足之处。仅见者如:“秦晋、燕周在机,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85]①,具贸易中心则是杭州。杭州市场上的绢,“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86]②。又湖州的包头绢,“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87]③。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浙江丝品的主要走向也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局改为领织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当然更盛。不过,明代丝织品的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了,在北方各城市均有市场。如山东临清,万历间有“缎店三十二座”[88]④;乃至北边如宣化,亦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89]⑤等。这种远销的大约以高档货为多,一般的绸和纺绸,可能还是南人习用。
潞绸原因入贡而织,系长治、高平、潞州等地民间织户所造,但也有大量商品绸。“在昔(指明代)全盛时,……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90]⑥。
这种绸大约适地北方,“是绸也,士庶皆得为衣”[91]⑦。
福建,“闽不蓄蚕”,而闽绸则颇出名,这也是因为质量好。“泉人自织丝,玄光若镜,先朝士大人恒贵尚之,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航互市。”[92]⑧“福之丝,……下吴越如流水”,并“航大海而去”外洋[93]⑨。广东也是这样。“广纱甲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粤缎“行于西北”,外输“东西二洋”[94]①。
丝和丝织品与棉花、棉布不同,它们基本上是商品生产,价值较高。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凡是质量好的,都能远销,并有出口。因而运销繁荣,市场的扩大,对生产的作用也比较大。明代官丝织局的生产能力大约为五点七万匹,这是按高级产品缎来。明后期,苏、杭一带民间机户的织机大约为官织局的三倍,生产不限于绫、缎,产量较高。嘉靖以后,官织多改为领机和市买,历次加派常达十万匹,即靠民机生产。还有,农家副业的丝织品生产,主要是绸和绢,也大部分是商品性生产。这样,粗略估计一下苏杭一带的上市量,即参加长距离运销的丝织品,每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按各类平均每匹一两计,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
棉布是明代新兴的大宗商品,丝织品则是有悠远的商品了。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商品市场的扩大,常是伴随着它价格的降低的。丝织品的贸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据汪士信同志,绢的价格,明代平均比宋代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这里面有银价下跌的因素,但若将绢价折米计算,明代平均也比宋代下降百分之十一。明代从永乐到嘉靖,绢的价格是上升的,但一般物价的上升更大于绢,如将绢价折米计算,仍是下降的。其情况如下:[95]②
绢每匹合银(两) 绢每匹合米(石)
永乐时期0.63 ?
正统时期0.50 2.00
成化时期0.73 1.27
嘉靖时期0.70 0.82
(四)其他工业品的运销
以上,分别考察了粮食、棉花和布、丝以及丝织品的长距离贩运。此外,传统工业品中,除盐(它的运销只决定于人口数量)外,最重要的是铁。明代较早地开放民间冶铁,明后期,广东佛山的铁冶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四川的铁,经长江运到江苏无锡[96]①;福建的延(平)铁,经海路运到苏州[97]②。而广东的铁,长途跋涉,用驮运经大庾岭到江西[98]③,非有有利的市场是不会行销这么远的(这里所说的铁,也有可能是铁器。)
铁器,原来是铁匠就地锻造,并主要是接受用户加工。明代,开始有了小商品生产,同时也就有了商品运销。明后期,并出现铁器集中产区,成为有名的铁市,如苏州的 村市,震泽的 丘市,以及广东的佛山市。佛山在景泰时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辏”;[99]④在天启年间即已分为炒铁、铸锅、铁钉、铁线、制针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铁器,尤其是铁锅,之所以行销甚远,主要是由于其质量好。冶家对于技艺人“必侯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故佛山之冶遍天下。”[100]⑤在佛山铁器铸造业中也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江西饶州的制瓷业,是明代起来的,景德镇之名即得之于明瓷。明后期,景德镇的瓷器运销已是北到燕北,南到越南,西到四川,东出海外了[101]⑥。
此外,若漳州、泉州的糖运销江浙及海外[102]⑦,江西铅山的纸运销河南、安徽[103]⑧,都是明代新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前已屡提及,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之陆续进入市场,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四 大商人资本的兴起
明代徽商和山西、陕西等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曾引起中外学者重视,不少著作。本文不拟多论,而是把它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从他们经营的、资本组织和资本量上,来考察一下大商人资本的作用。
明代市场上最大量商品是粮食,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也于粮食运销。但粮食的经营很分散,所在产地和销地都有粮商;并且运销利润较低,明代多数贩运商尚未专业化,粮食常是兼营的。因此,新兴大商人资本的主营业务不是粮食,而是盐、茶和布、丝织品、木材等。
先看徽商。安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104]①。这里“鱼盐”是偏义复词,实指盐。汪道昆的《太函集》记徽商最详,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又“吾郡中称闾右世家,首推东门许氏,……以盐 贾”;“邑中世业最显者莫如诸程,之浙贾盐 ”;汪本人的先世也是“宗盐 ”。[105]②就是说,微商资本最大的都是盐商,或以盐起家。
就徽商说,盐以外,最大的资本是典当,徽典遍于大江南北。一家典当所需资本并不多,但典当多系联号或联营,故成大商人资本。典当不属商品经营,本文不论。再其次,则当是茶和布。安徽是茶产区,茶商自多。张瀚说:“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106]①。布是大宗商品,当不少经营。还有木材,也是安徽特产,尤其是婺源寿材,经营者也是大资本。在清代,对徽商习称“盐、典、茶、木”[107]②,是指其声势是显赫者而言,不是指商品多少;在明后期,看来也是这样。
盐,是王朝最重要的专卖品,利润特大;盐商又都经营私盐,利润就更大[108]③。正因如此,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盐商带有官商性质,尤其是明代实行纲法,引商编入纲册,世袭专利,其特权性质尤为显著。并且,盐的运销自不是的补充,它的生产和消费决定于人口数量,无论有多在资本投入经营,对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并无多少作用。只不过是扩大剥削量,从而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而已。
茶,在明代,除官茶、贡茶外,茶商都是引商,也属特权商人;张瀚就说,其利润大是因“第市法有禁”[109]④。不过,茶叶运销的扩大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江南茶产量的增长主要是在清代,明代发展有限。木材虽是一般商品,但当时大的木料主要是宫廷和官廨所用,大的木商领有官帑,替官采办,因致大富。如万历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 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20]⑤
再来看山西、陕西商人。这些西北商人中资本最大者也是盐商,这又和明代的开中制有关。洪武年间,边防缺粮,乃招商纳粟,给以盐引,令持引到两淮、河东贩盐,所谓纳粟中盐。经营此业者多系西北商人,称边商。在这种场合,商人须有两套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故非大商人莫属。这些大商人,实际是替官家购粮、替官家销盐,其资本实际不是独立的商业资本。为了纳粟北边,有些商人即在边地募工垦植,以免运粟之劳,称商屯。这种商屯是“自筑墩台,自立保聚”[121]①,看来还不是自由雇工,其剩余产品交官,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其后,北边战事,商屯破坏。弘治间,出支,即纳粟产人领得盐引后,可将盐引卖给别的商人去贩盐。又出现开中折色,即纳粟改为纳银。这样一来,边商内徒,多寓籍淮扬,西北盐商也和徽州盐商一样,变成专业盐商了。万历时,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122]②
在开中制中,除纳粟外,还有纳茶中盐、纳布中盐之举,与纳粟作法同。纳茶、纳布虽不经常,但有重要性。西北商人贩茶,多自四川,主要是供官府作茶马互市之用。布,很大部分是供军服之用;明初西北军服,一次常需六、七十万匹布,较燕北、辽东都大。所以前引史料,常见秦晋大贾到松江贩布。傅衣凌同志说:“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123]③还可补充说,这些活动都与官家的需要有关,并以盐为关键,因为是大利之所在。到明后期,这些活动基本上都属于商品流通性质了,但其与封建政权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
现在再从商人资本组织上来看。明代出现贷本经商和合伙制度,这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有一则徽商的记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124]①又商人王敦夫,“从族人贾汪陵,……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125]②。这里的贷本,或是贷给族人,或是有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亦系族党子弟;看来,宗族关系很重要,还说不上是货币资本的信贷。此外,徽商中有友人“寄金”之事,就事例看,“寄金”不过百两、数百两;又商人间使用借券,要维护借券的信用。这虽不限族党,但不象是借本的性质。
合伙制,在徽商中有“伯兄合钱”“昆季同财”等记载,这等于是一家合伙,是从家族经商演变而来的,也是一个商人的第二代常见现象。又如休宁的程镇:“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久之,业駸駸起,十人皆不赀。”[126]③这已是多人合伙,但仍以程氏宗族为限,并且这种“合从”,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所以发家后“十人皆不赀”。不然,商人在生意发民中,“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127]④,有外姓人加入是很自然的,但未必是合资关系。宗族制在明代仍是一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
合伙制或伙计制,在山西商人中尤为流行。有一则常为人引用的史料:“平阳、泽〔州〕、潞〔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藏。但父或子母息匄贷予人而道亡,贷者业舍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得斯人以为伙,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具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128]①
我引录较详,因可不同解释。我认为,晋商的合伙制,实际是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也许是由贷本经商发展而来,但文中插入的子孙为亡父还债一事,并不一定是借本,而这一节,只是说“有居积”的东家争着要这种有信义的人作伙计,不是说放贷给他。东家与伙计是“合伙而商”,有类后来的钱股和人力股合伙。其经营利润,是双方共亨的。
《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这是伙计制的很好说明。不过,《金瓶梅》是写山东地区,不是讲西北。“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29]②,大约伙计制在徽商中也是通行的,不知为什么《太函集》中没有反映。《石点头》第八回有“两个伙计认他本钱,在金陵开了个当铺,前来盘帐”,这也是工伙关系,并且是任伙计在外地独立经营。这种伙计,同近代商业上雇佣的伙计,完全是两回事。《金瓶梅》第九十九回说,“两个主管齐来参见”陈经济,问病,陈经济说“生受二位伙计挂心”。伙计在店就是主管,伙计也是尊称。
看来,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组织,贷本经商主要限于宗族,外姓参与主要是作伙计。
最后,看一下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究竟有多大。这方面无确切记载,只能大体观察。万历时,徽州商人“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130]①,这大约指平均而言,其大者不会超过徽州。徽州歙县的“盐筴祭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131]②不过一般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了,上百万的是少数。徽商“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132]③。前引叶梦珠《阅世编》说,到松江贩布的大贾,可能是秦晋商人,“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前引山西平阳、泽州、潞安商人,“非致数十万不称富”,又“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西北商人,大贾也是数十万,也有达百万者。
“数十”的含义模糊,但一般理解,是十一百之间的较镐位数,以别于二、三十的称谓。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即明后期的商人资本,银二、三十万两的算中贾,五十万两以上的就是大贾了,达一百万两以上的是极少数。
王世贞记有严嵩的儿子论天下富豪的一段史料;“严世藩……尝与所厚旨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133]④这是说,在明嘉、万时,积资五十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十七人。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应是商人。不过,在这之前还有邹望、安国二人,他们是正德时的无锡商人。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明后期大商人的资本可与王公、太监、都督并列,可谓“富与敌国”了。但是,五十万两这个标准,与清代比,却果不大的。王世贞也说,后世官僚过百万、二百万就很多了。
五 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关于明代国内市场的考察,可以得来如下一些结论。
一,国内市场显著地扩大了,这表现在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但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这包括有因素,不完全是商品的结果。以南北贸易而论,其量也是有限的,除漕粮外,这毋需南粮北调。而经济上最重要的长江贸易,还主要是在中下游。地方小市场,也仅在个别丝的集中产区发展为初级市场。
二,长距离贩运有了发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转向以民生用品的贸易为主,即由产品与收入的交易转化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这是市场性质的一大变化。品之陆续加入市场流通,也是值得注意的动向。但是,终明之世,长距离贩运贸易在整个市场交易中仍很有限,而其中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并不占主要地位;产品,大半还是单向流出,得不到补偿和交换。
这里,还提不出什么数据。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前)的状况,长距离贩运约占全部商品食的百分之二十,明代远不会达到此数。从上文粗略的估算,在长距离贸易中,布和丝织品的价值合计还抵不上粮食的一半(而到清代前期,两者约略相等)。又上文估计进入长距离运销的商品粮食不过一千万石,而明廷征收的赋、课等如全部折成粮食常达三、四千万石。
三,徽商、山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说明国内市场已有相当的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但这种积累主要是从经营盐以及茶、布等商品而来,多少是假借封建政权的力量形成的。大商人的资本关系还限于家族范围,尚缺乏信用。大资本还限于银五十万两级、最高百万两的水平(清代已达百万两级、最高以千万两计的水平)。
注释:
[78]① “茧”应作“丝”,明代尚无茧的贸易,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二十,蚕论。
[79]②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三十一。
[80]③ 王犀登:《越客志》。
[81]④ 粤缎极精,“然亦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所不取。”《岭南丛述》引《广东府志》。
[82]⑤ 嘉靖《保宁府志》卷七,食货记。
[83]⑥ “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顺治《潞安府志》卷一。
[84]⑦ 成都善织锦,但“千里无一蚕株”。章璜:《图书编》卷四十,水利蚕桑。
[85]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宗四。
[86]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引万历《临安县志》。
[87]③ 嘉靖《湖州长府志》卷四十一。
[88]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89]⑤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90]⑥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地理四。
[91]⑦ 吕坤:《去伪斋集》卷二,停止砂锅潞绸疏。
[92]⑧ 王澐:《漫游记略》卷一,闽游。
[93]⑨ 王世懋:《闽部疏》。
[94]① 《岭南丛述》引《广东府志》。此记载较晚。但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所述略同。
[95]② 汪世信同志的,将载入《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
[96]① 万历《无锡县志》卷八,食货二。
[97]② 王世懋:《闽部疏》。
[98]③ “梅岭道路,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日有数千[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十二册,江西。
[99]④ 景泰二年陈贽《祖庙灵应词碑记》,载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
[100]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101]⑥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102]⑦ 万历《闽大记》卷一,王世懋:《闽部疏》。
[103]⑧ 万历〈〈铅书〉〉卷一。
[104]① 谢肇《五杂俎》卷四。
[105]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吴长公墓志铭卷二十八,许长公传卷三十二,程长公传卷三十;九,世叔十一府君传。
[106]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07]② 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
[108]③ 盐的销售价格和产地价格一般相差五至十倍,不过大部分是专卖利润。万历时有人说商人经营盐的利润和经营一般商品是五与三之比,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册,苏上,耿橘。
[109]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20]⑤ 陈眉公:《冬官记事》。
[121]① 《国朝典汇》卷九十六,记明初事。
[122]② 万历《扬州府志》卷一。
[123]③ 傅衣凌:《明清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版,第170页。
[124]① 方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
① [125]李维桢:《大必山房集》卷一零六,赠罗田令王公墓表。
[126]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127]④ 金声:《金太史集》卷四,与歙令君书。
[128]① 沈思孝:《晋录》,又见王士性:《广志绎》,《肇域志》第三十七册,山西,方与崖略。
[129]② 谢肇制;《五杂俎》卷十四。
[130]① 谢肇制:《五杂俎》卷四。
[131]② 万历《歙县志》卷十。
[132]③ 《肇域志》第三册,安徽。
[133]④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