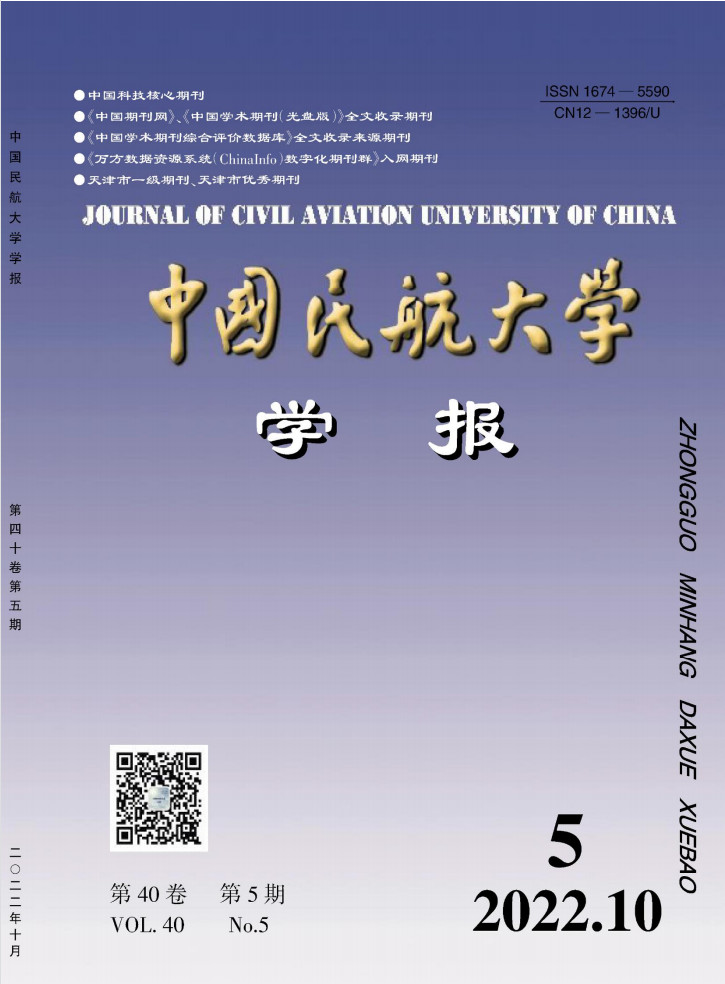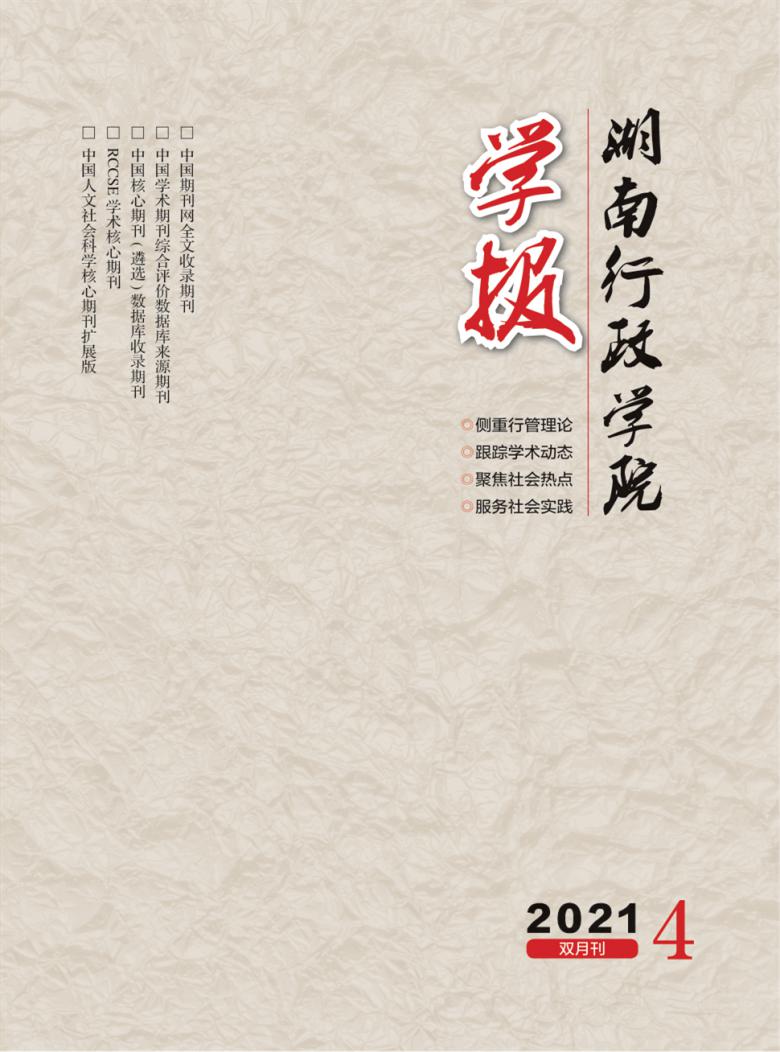对中国、阿拉伯、英国三部爱情悲剧的文化审视
丁淑红 2006-01-19
提 要:本文以平行研究角度对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文化层面的多向观照和审视,从梳理其表面的趋同入手,再探究分析其深层的相异之处,从而揭示出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造就了三部爱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迥然各异的爱情表现以及三部悲剧文本所凸现的不同文化景观和审美需求。
关键词:爱情悲剧 民族文化心理 文化景观 审美情趣
每个民族都有其对爱情婚姻的独特理解,但纯洁美好、坚贞不渝的感情却是每个民族追求向往的最高境界,因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纯情爱情的典范。汉民族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阿拉伯民族有“盖斯与莱拉”的故事,西方民族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这三个爱情故事都是讲年轻男女相恋不能结合,自杀而亡,有着纯殉情这一共同母题,本流传于民间,是各种族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和记忆的结果。后经文人之手再创造,跳出了民间文学的范畴,进入纯文学领域而名垂青史,在各自所属的文化圈中熠熠生辉。本文将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重新置放于其诞生的文化土壤中进行多层面的探究和体察,对中、阿、西三种文化体系中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追踪溯源,以对照解读三部文本中的悲剧人物受其影响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有何不同,期望对三国文化特质有所把握。
异曲同工之妙
世界上有不少戏剧佳作取自于民间传说,后经过剧作家的再创作,终成为流芳百世的艺术典范,在不同文化圈中广泛传播,例如:中国剧作家徐进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剧作家艾哈迈德·邵基的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徐剧、邵剧和莎剧。这三部爱情悲剧无论从母题来源、基本情节、思想题旨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1、母题来源:三部爱情悲剧均取自于本民族的民间爱情故事,后经剧作家之手的再创作成为纯殉情典型。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在江南一带更是流传甚广。最早出现在东晋,若从形诸文字的唐代张读《宣室志》中所记载的梁祝故事算起,记录、扩编梁祝故事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可谓种类繁多,数不胜数。特别是被改编成戏曲上演以后,梁祝的形象活跃于不同剧种的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了传统剧目。有些唱段更是脍炙人口,传诵不息。现在流传的剧本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口述,由剧作家徐进等整理而成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本文便是采用此版本。梁祝的故事虽诞生于中国,却广泛流传于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中。
“盖斯与莱拉”的爱情故事在阿拉伯国家妇孺皆知,可追朔到公元7世纪中叶。公元10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史学家艾布·法尔吉·伊斯法哈尼正式将这一故事收录于《诗歌集成》中。埃及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便是根据《诗歌集成》里的素材在1931年写了著名的诗剧《莱拉的痴情人》。邵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留学法国。一度受埃及总督宠幸,成为宫廷诗人。因在诗中表露出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懑情绪,而遭流放。他创作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的诗篇,收录在《邵基诗集》(四卷本)。他的诗独树一帜,享有“诗王”的美名。晚年专注于诗剧创作,写有六部诗剧,大多反映阿拉伯民族和埃及人民的悲剧,奠定了阿拉伯诗剧的基础。“盖斯与莱拉”的故事起源于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文化圈内广泛流传,并借助12世纪波斯大诗人尼扎米(1141-1203)《五卷诗》中的《莱拉与马杰侬》这一卷声名远扬,又以此为辐射核心进入欧洲。 “在阿拉伯文学中,马杰侬实际已成为一个典型。凡因爱情变得神魂颠倒、失去理智、或为爱而殉情的,人们均称他为‘马杰侬’”[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本为小说。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据此传说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故事便传入英国,在欧洲大陆传播甚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根据这首长诗在1594-1595年间写成《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这是莎翁三部爱情悲剧中第一部。此剧从16世纪上演以来,经久不衰,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拍成电影近20部,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2、基本情节:三部爱情悲剧的基本情节相似: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相爱;他们的爱情都潜伏着危机;男方向女方求婚遭拒绝;期间有好心人从中成全;女方家仍违背女意将她嫁与他人;一方死,另一方在其坟前为其殉情。
徐剧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途中偶遇也去求学的梁山伯,彼此互有好感,遂在草桥结拜金兰之好。三年同窗共读生活,使祝英台对梁山伯暗生情愫,可梁山伯竞不知祝是女儿身。“十八相送”聪明的祝英台以巧妙的比喻,向梁暗示她的爱慕之情,善良的梁山伯仍没识破祝的庐山真面目,这便是梁祝爱情潜伏的危机所在。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女授受不亲,不能相对独处。女子更要谨守闺范,不得混迹男子群中。结婚需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私订终身。祝英台曾托师母做媒,梁山伯父母向祝家提亲不成。祝父不顾女儿的反对硬是将其许配给马家,梁山伯为此怅然不乐,相思成疾而魂归西天。祝英台闻之后,到梁冢前失声哀恸,忽然冢裂,祝投而死。
邵剧中盖斯和莱拉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阿米尔部落,自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真诚相恋。盖斯用诗歌倾诉对莱拉的爱情和思慕,这就是他们爱情最大的障碍所在,也是莱拉父亲拒绝将女儿嫁给盖斯的原由。因为阿拉伯的礼教规定,不得将女儿嫁给一位写诗赞美她的人,以避嫌疑,维护家族的荣誉。一对情人被拆散,盖斯精神失常,被视为“马杰侬”—为爱而疯狂的人、情痴。地方官伊本·欧夫替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遭到拒绝。莱拉嫁给他人后忧郁而死,盖斯得知来到莱拉的坟前泪尽而亡。
莎剧中维洛那名城两大家族的后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次假面舞会上一见钟情,彼此真诚相爱,可两家“累世的宿怨”从根本上就取消了他们结合的可能性。劳伦斯神父暗中帮助这对恋人,无奈顽固的朱父硬要将女儿嫁与他人,朱丽叶假死被葬,罗密欧在其墓前服毒自尽,朱见罗亡也举剑自刎。
3、思想题旨:三部悲剧讴歌了青年男女纯真美好、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为爱情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摒弃旧的婚姻观念,最后以死来抗争、捍卫神圣爱情。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死亡而终结,而是通过死后永不分离而获得了永生。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爱情悲剧,也是一种社会悲剧,是两种生活制度、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之间冲突的结果。他们的叛逆行为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徐剧中没有提到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只是泛指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祝英台拒不接受其父对她婚姻的摆布,不屈服有权势马家的逼婚,敢于私订终生,他们以叛逆的姿态反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奉“父母之命”、由父母作主的婚姻制度,催发了那个时代个人婚姻意识和自决的权力。
邵剧中明确写着剧情发生在伍麦叶时期(公元661-750)初,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虽然建立,可是部落偏见却牢牢地控制着阿拉伯人意识和行为,扼杀了盖斯和莱拉这样一对情人。盖斯蔑视部落习俗,大胆追求爱情,而莱拉的行为始终受部落传统的制约,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和顺从它,并成了它的牺牲品。此剧揭示了“蒙昧时期阿拉伯旧礼教与伊斯兰新礼教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思想就是要消弱根植于莱拉和她父亲麦哈迪意识中蒙昧时期的偏执”[2]。
莎剧写于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创作时期,也就是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正盛之际,但血腥复仇传统仍在蒙、凯两个家族沿袭下来,阻碍了罗朱的结合。罗朱不愿因上一辈的恩怨而放弃美好的感情,朱巧妙地应付了母亲的逼婚,与罗秘密结婚,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他们的死消除了两家的仇恨。因而“构成悲剧冲突的不是两个家族,而是两种社会道德力量:一种是残酷、凶恶和复仇的封建精神,另一种是爱情、友谊、和谐的文艺复兴风尚”[3]。
各行其是之道
尽管三部爱情悲剧有以上的不谋而合之处,说明以纯殉情文学为参考点观照人类文化所具有的某种相同和审美上的共性,而差异之处却是它们的明显标记。三部爱情悲剧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的不同。而“爱情和婚姻实质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体现”[4],能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格、人格意识、婚恋观。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原初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某种应对生存条件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看法,这些观念通过种族世代相袭、承传下来,深深地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模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5]。
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汉民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半封闭的大陆地势,丰沛的水资源,便于农作物的生长。随季节变化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超稳定的生活方式,这就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即被动接受、内向调适、避免冲突、追求天人合一、稳定和谐的性格特征。由经验性生产实践而产生的习俗观念对民族普遍心理势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汉民族严格而稳固的宗法伦理秩序,以原始血缘宗族传统为根基,个人严格自律,置家庭、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出现了中华民族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坚固、完整而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人伦情感、孟子的内圣人格,到汉代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以及宋儒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都在不断丰富并强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
阿拉伯文化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文化。阿拉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满目荒凉的沙漠,零星点缀的绿洲,昼夜温差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严峻而恶劣的生存环境,极为匮乏的物资条件,为争夺有限的水草,流血事件频繁,复仇劫掠不断,时处于忧患之中,因而“阿拉伯民族是神经质的民族,常常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而暴怒如雷,不可遏”[6]。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该民族养成粗犷剽悍、无拘无束又易冲动的性格特征。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造就了阿拉伯民族独特的自然人格,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为了生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结成部落,患难与共,表现出狭隘的“团体精神”。这种精神状态使阿拉伯人注重个人和部落的名誉,恪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和国家,氏族部落林立,各据一方。到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提出“穆斯林皆兄弟”,逐渐化解、消除了部落间的隔阂与仇视,阿拉伯民族团结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并以开放的心态吸取了周边各种文明,创造出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则对阿拉伯人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都有所规定。可阿拉伯民族本性中粗犷、率直、冲动的性格特点却始终流淌在阿拉伯人的血脉中。
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生活在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上,这里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土地贫瘠,农牧业收获有限。为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进行物品交换和海上掠夺,从而发展了商业和航海业。无拘无束的海盗生活、独立自主的商业贸易形成了希腊民族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公元一世纪,来源于中东希伯莱文化的基督教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这有异于古希腊文化。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主张抑肉伸灵,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希伯莱文化吸纳了古典希腊文化中的某些成份后,演化成新形式的基督文化,以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禁欲主义。直到15世纪末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格全面发展为理想的“人文主义”。个人的权力、个人的的独立性及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肯定和发展。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又延续了这一基本属性,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张,不回避冲突,勇敢地迎接冲突。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上则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阿拉伯文化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向外突破,寻求扩张和掠夺。崇尚武力,有着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族意识强,重部落和个人的名誉,恪守部落习俗。改信伊斯兰教后,遵守伊斯兰教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千差万别。汉民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尚人伦,有着依附人格意识;阿拉伯民族率直、冲动,固守教规,有着鲜明的自然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奔放,追求俗生活、信奉爱情至上,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不同,使三部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表达上、对爱情的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异彩纷呈。
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
徐剧中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后又用黄狗“偏咬后面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与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憨厚的梁山伯不知贤弟竟是女儿身,一点都不接受暗示,祝英台气得骂他是“呆头鹅”,却仍然不公开真相,表达爱情,从而丧失了父亲指婚前明确两人爱情关系的良机。
邵剧中盖斯和莱拉公开而直率地表达互相爱恋之情。盖斯写诗赞美莱拉,将她比喻为“沙漠的月亮”[7]、“羚羊”,在阿米尔部落已家喻户晓。莱拉分别当着众人和地方官面承认“盖斯的爱深藏我心,我与盖斯心心相印”(第一幕),且“盖斯是我心之所恋、心之所托之人”(第三幕),极为坦荡,不掩饰内心感情。
莎剧中罗朱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其爱情炽热而又明确。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将其视为“天上明珠降落人间”,是“一位绝世的佳人”,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二幕二场),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托给罗,随他到天涯海角。
其次,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
梁祝对待爱情表现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其爱情产生于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学习过程中,这是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是先相知后相爱的。
盖斯和莱拉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盖斯癫狂而又神经质,不能自己,任其自然恣意。炽热爱情折磨得他身心衰竭,在内志沙漠谷地间疯疯癫癫地游荡,唯有听到莱拉的名字和有关莱拉的谈话才能振作精神。莱拉很理性,深知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一面要维护贞操的圣洁,一面割舍不下心爱的人”(第一幕),她最终用理智战胜了情感。他俩的爱情产生于自小一起放牧、嬉戏中,也是先相知后相爱的。
罗朱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无所顾忌的。他俩一见钟情,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是先相爱再相知的,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最后,在捍卫爱情的行动上。
梁祝“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8]。梁得知父亲将她许配马家时,先是“惊愕良久”,委婉拒绝;后与父争辩,愤然离去;再是深锁闺中,饮食不进,这便是祝她最激烈的反抗行动。梁欢天喜地来到祝家提亲,知晓祝已明花有主,要祝退婚并想告官,祝则劝道:“梁家无势又无财”,告状“于事无补要先吃亏”,况梁是“单丁子”,请他“另娶淑女”。在爱情留存的危急时刻,它们不是商量对策以求生路,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死。祝要梁将坟墓筑在马家娶亲花轿必经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忧思成疾慢慢地死去,也不愿公开地为爱情决一死战。
盖斯为争取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疯狂而丧失理智的。他不顾阿拉伯礼教,在诗中大胆歌咏莱拉。不怕流言蜚语,佯装到莱拉家借火种,去见心上的恋人。向莱拉倾诉爱情,连火盆的火烧着了衣袖,灼伤了皮肉,竞无知觉,最终被莱拉的父亲赶走。请朋友帮忙打探莱拉的心思,还请地方官替他向莱拉父亲求婚。莱拉嫁人后,盖斯来到莱拉的新家,对其丈夫冷嘲热讽,质问他与莱拉有否夫妻生活。见到莱拉后,要求莱拉与其私奔。莱拉劝他等她离婚,而盖斯竞责备莱拉变了心,伤害莱拉“明天将另觅新爱,将其迎娶进门”(四幕二场),并不顾莱拉的恳求,负气而去。莱拉嫁人后,为盖斯守身如玉,与丈夫“同床不共衾”。“她是个固守礼教的贝督因少女,又是个矢志忠于爱情的恋人”[9]。
罗朱为捍卫爱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斗争方式。罗杀死朱的表兄遭流放,朱派人送去她的指环安慰罗,以表她的诚意和决心。面对母亲的逼嫁,她一面巧妙应付,一面与罗秘密结婚,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渡过新婚之夜。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不惜用撒谎、假死等手段。而罗密欧被爱情的火焰点燃后,一切行动变得无所顾忌。初识朱后,便冒着危险翻墙潜入朱家花园,向朱吐露爱慕之情;随后又大胆进入朱的闺房,与之分享爱情的幸福。可见罗朱为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大胆又不惜代价的,具有一反到底的精神。
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下三部爱情悲剧男女主人的爱情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徐剧表达爱情隐蔽、含蓄;对爱情的态度清醒而不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软弱,不坚决、彻底。邵剧表达爱情公开、率直;对爱情的态度冲动而丧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鲁莽、疯狂。莎剧表达爱情明确、袒露;对爱情的态度热烈而无所顾忌;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大胆而有所作为。 相映生辉之美
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外在的物化形态,并通过个体的参与活动将本民族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审美标准显现出来,多少能折射出其文化的内涵和基质。中国、阿拉伯、英国剧作家依存各自的文化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三部纯殉情文本中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观地再现了本民族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和宗教信仰,并在剧情安排、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方式和剧情结尾处作出了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需求的诠释。
徐剧描绘的是中国江浙一带的封建社会,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和南方秀丽的田园风光,有员外、相公、千金小姐、书童等身份的人物,祝家庄、草桥亭、古庙等场景,展现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剧中,祝父劝女儿在闺房描龙绣凤、裙钗之女不能抛头露面、父母之命不得违抗、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俨然一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祝英台着白衣素服、带着白纱灯、三千纸银锭拜祭梁坟也有着浓重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于事“和为贵”、“和为美”便成了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审美凝结,这体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情节较简单,不错综复杂。从梁祝初识的“草桥结拜”,到两人感情发展的“托媒”和“十八相送”,至梁山伯迫切求婚的“思祝下山”、“回忆”乃至梁祝倾泻感情的高潮“楼台会”都很少有正面冲突,一味平铺直叙优美雅致的故事,起承转合中不见波澜。唯一的冲突在“逼嫁”时,祝与其父争辩并采取绝食的行动以示抗争。在殉情方式上,梁“刻骨相思染重病”,祝捎来亲笔信和一束青丝发,以示结发夫妻到白头。祝来到梁坟前立誓不同生求同死,这感动天公,坟墓豁裂,祝纵身跃入,实现了“生不同罗帐死同坟”,突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不敢正视客观存在,以中庸之道弥补人生的缺憾,补偿心理的失衡。结尾梁祝化作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双飞双栖,更有着中国古典悲剧所特有的“大团圆”之趣,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情趣的必然要求:追求心理满足的完整性;强调和谐的中正和平;求得思想慰藉的阴柔;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完美性;善恶终须有报的目的性”[10],营造出一种清意缭绕、余韵飘渺的意境美,极富东方色彩的人情魅力。
诗剧《莱拉的痴情人》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初建伍麦叶时期的内志沙漠地区,因而剧作家邵基在诗剧中展示了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生活习俗、社会状况和宗教信仰,既具有浓郁的阿拉伯游牧文化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有部落青年男女、部落长者、地方官、传诗人、精灵、赶驼者等身份的人物,有沙漠、阿米尔部落、商队、帐篷等场景。风俗习惯上,他们用双手拍掌、倒穿衣服表示迷途忘返。阿拉伯人思想意识中因果观念薄弱,依靠占卜、巫术排忧解难。盖斯爱上莱拉后,常神智错乱。在第二幕,女侍白勒哈给盖斯带来他母亲烹调的食品:一只掏去心脏的羊,巫师在上面贴了符咒- 这是医治盖斯痴病的药方。另外,古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精灵离人很近,离诗人更近,人的精神错乱便是精灵所为。每个诗人都有一个精灵向他启示诗句,并有一个传诗人相随相伴。邵基在剧中写了盖斯的传诗人齐亚德和其精灵伍麦维。齐亚德不仅是盖斯的传诗人也盖斯的忠实的朋友,即使在盖斯最困难的时刻也寸步不离,为他日夜操劳回击挑衅者。盖斯的精灵伍麦维不仅见证了莱拉的贞洁,替盖斯保护莱拉,还在盖斯精神错乱、迷失荒野时将他引到莱拉家前,使两人得以相见。在道德上,他们固守部落礼教,让苏丹裁决用诗歌谈情说爱者,甚至允许莱拉的父亲可以将盖斯杀死。伍麦叶时期的阿拉伯人已信奉伊斯兰教,剧中出现了在昏厥者耳边高声呼唤“至高无上的真主”或对话中有“敬畏真主”、“愿真主怜悯他”、“天堂”、“火狱”等穆斯林信徒用语。沙漠是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家园,它空旷单调、贫瘠荒凉却有着自由奔放的生命,这在阿拉伯民族审美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由度与简朴感,因而阿拉伯文化崇尚直朴、简洁的美,体现在邵剧上情节简单,单线条地以盖斯的爱情展开。从盖斯热恋莱拉受挫、害了心病神志恍惚到地方官带他求婚遭拒绝、一对情人重逢不欢而散、莱拉陵墓前悲伤过度咽气,结构不复杂,道也是波澜起伏,紧张气氛突起,地方官领着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刚走近阿米尔部落,便见阿米尔人个个手拿器械,准备杀死盖斯。地方官好言相劝,平息了众人的愤怒,不料盖斯的情敌又对盖斯进行恶意中伤,阿米尔人柏什尔挺身站出,揭穿其险恶的用心,阿米尔部落宽容了盖斯,“一个不谙事理、易于冲动的部落民族形象地表现于舞台上”[11]。在殉情方式上,莱拉乃忧思成疾而死,盖斯墓前拜祭,从墓穴中传出呼唤他名字的声音,便应声而亡。诗剧结尾处响起盖斯的声音:“尽管我们没能结合,仍活在世间;莱拉没有死,痴情人更不会亡”(第五幕),这有着浓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神秘色彩。因为伊斯兰教信徒“信前定”,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真主预定安排的,《古兰经》经文就是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修行而得到的天启。另外,伊斯兰教要求人们顺从和忍耐,诗剧结尾处也正是追求这种神秘、宁静的境界。
莎剧反映的是欧洲中世纪末期英国的社会情况,出现了亲王、贵族、伯爵、神父等身份的人物;庄园、教堂、广场、街道等场景,显示了英国封建社会十分繁荣的景象。劳伦斯神父竭力促成罗朱的爱情、婚姻结合,显示了欧洲中世纪末期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禁欲主义思潮的一种具体反映。在宗教观念方面,莎剧时代的英国人信奉基督教,剧中对话常出现“祷告神明”、“亲一下《圣经》”、“阿门”、“英魂已经升上天庭了”等宗教术语。西方文化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悲剧心理的戏剧冲突,这体现在莎剧中剧情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每每“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又变成“柳岸花明又一村”。开场就气氛紧张,互相仇视的两个家族的仆人开打,罗朱在这种情形下一见钟情。自此爱情悲剧揭开了序幕,之后又有少年贵族向朱求婚,罗杀死朱的表哥更使矛盾激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幸好有劳伦斯神父相助,得以缓解矛盾。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带信人延误了时间,终使这对恋人双双而亡。恐怖和流血场面使人触目惊心,让人感到战栗。在殉情方式上,朱举剑自刎而死,很血腥、悲壮,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其悲剧“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英勇的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12]。结尾作者通过亲王之口,用人性感化了两个世仇家族,让他们彻底握手言和,这使得罗朱的爱情悲剧有一种朝喜剧方向发展的“暗示”。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爱情终于感化了仇恨,爱能战胜一切,彰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分属中、阿、西三个民族的爱情悲剧文本无论从母题、素材来源、情节结构乃至表现主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以叛逆的姿态声讨了旧礼教下的家长制和婚姻制度对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的摧残、扼杀。若将其置放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视点上挖掘,三部悲剧中男女主人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抗争意识却全然不同,这是由其所依存文化体系的特质决定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实质的不同,三部爱情悲剧在凸现爱情悲剧凄美、悲壮的同时,闪射出汉、阿、西方民族心理结构所特有的儒家文化、阿拉伯游牧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和审美情趣。毕竟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统属东方文化,都有着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注意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两者与西方文化那种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截然对立的。就风格而言,中阿悲剧都以浪漫主义的笔触、乐观的情调、深邃的寓意性,使人的心灵纯化,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贴与适度的满足。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悲剧的写实主义风格。 注 释:
[1]郅溥浩:《马杰侬和莱拉,其人何在?—关于原型、类型、典型的例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2] 阿拉法特·谢黑德:《再忆邵基》,黎巴嫩国家出版发行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3] 阿尼克斯特(苏)著、徐克勤译:《莎士比亚的创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38页。
[4] 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5] 程裕祯:《中国文化概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 艾哈迈德·爱敏(埃及)著、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页。
[7] 艾哈迈德·邵基:《邵基全集》第8卷,阿拉伯作家出版社 1994年第1版,贝鲁特,第124页。本文所引均出自此版本。
[8] 陈爱敏:《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9] 汉纳·法胡里(黎巴嫩)著、郅溥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9页。
[10] 焦文彬:《中国古典悲剧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11] 汉纳·法胡里(黎巴嫩)著、郅傅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631页。
[12]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