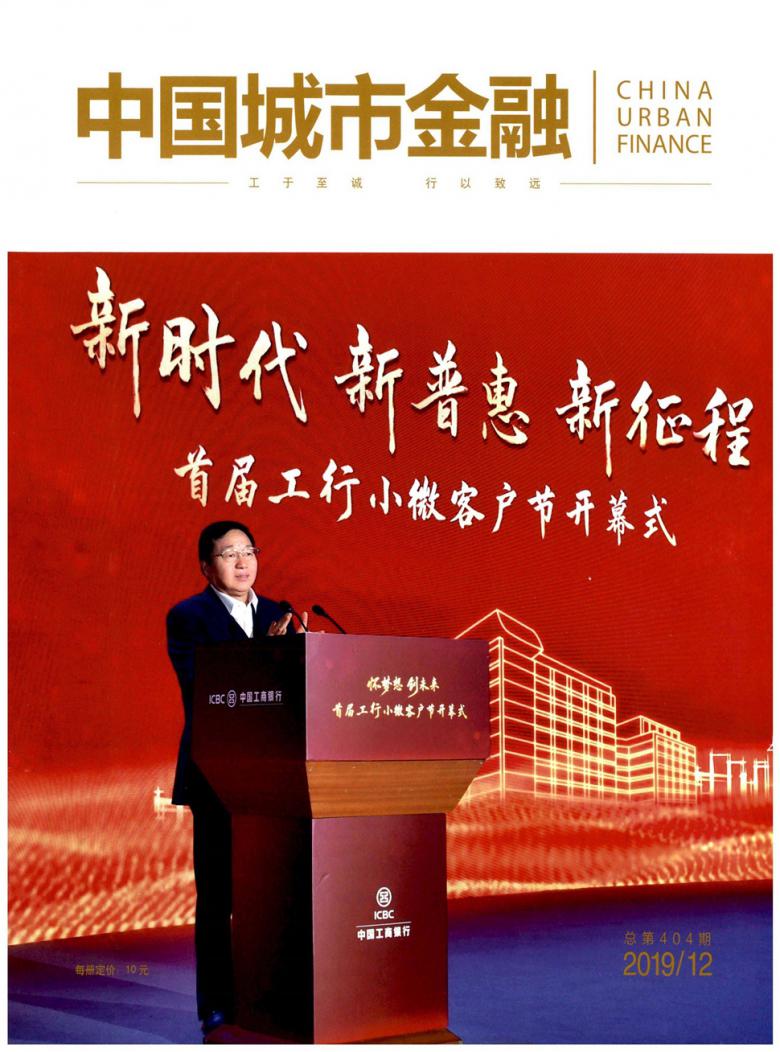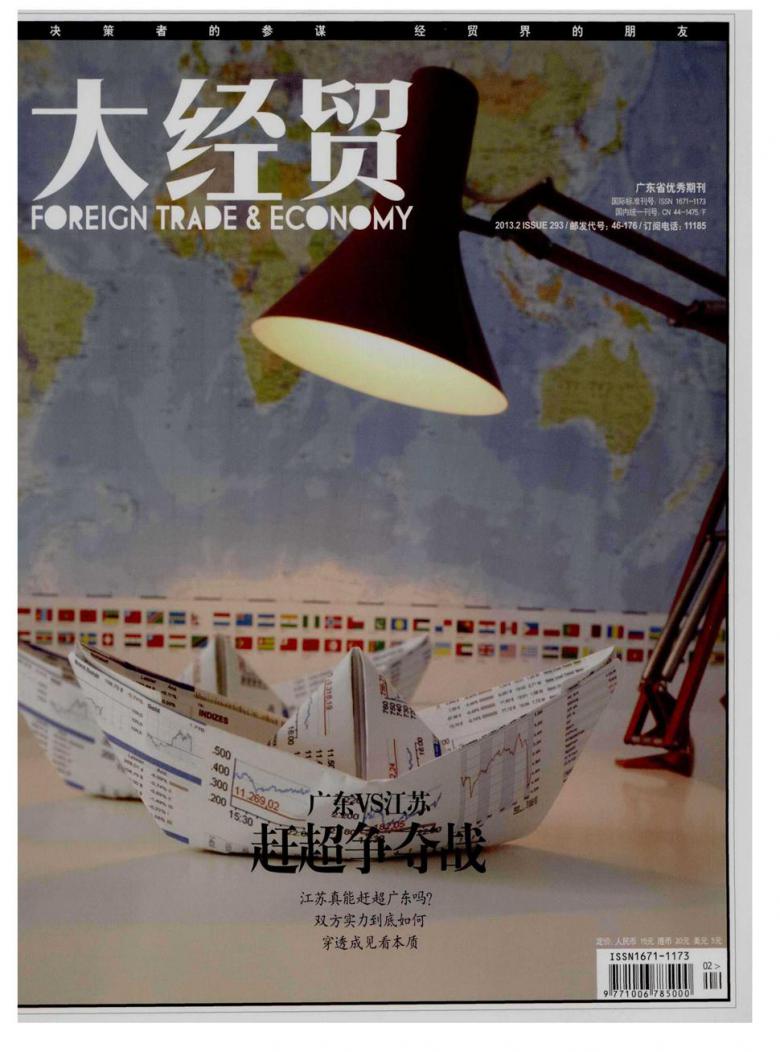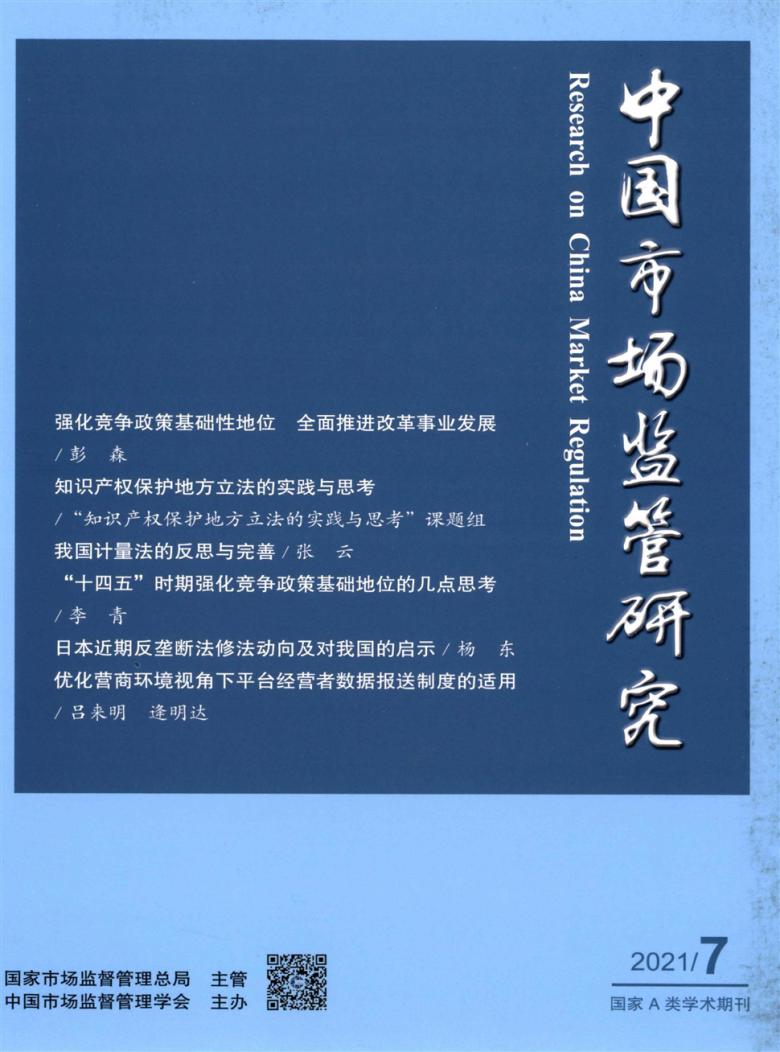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沈松勤 2008-08-15
唐宋词的功能和价值,不完全表现在形而上的、具有崇高审美意义的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首先体现为形而下的、非文学的实用功能。换言之,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首先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文学性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是在非文学的实用功能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非文学因素贯穿唐宋词史的始终。
一
吴熊和师曾经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唐宋词史则又表明,在由这三大功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社交与娱乐功能尤为突出,甚至成了抒情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
就体性而言,唐宋词首先表现为应歌。自中唐文人词始告确立至北宋近三百年的词史,主要是应歌的历史,在南宋,应歌词也绵延不绝。所谓应歌词,就是在社交娱乐活动中,词人为歌妓歌以佐欢而作的歌词。应歌词中的内容不象诗歌那样属于“夫子自道”,而是像唐代幕府中的“刀笔吏”一样,属于“例行公事”,其创作主体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严重的“性变”,即所谓“男子而作闺音”。其实,“例行公事”的应歌词是唐宋士大夫在社交和娱乐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种遥远而又通常使用的语言,也许可称之为诗化了的社交语言。而其中流露出来的“夫子自道”的闺情,便是以社交娱乐为前提的,为社交娱乐所需。所以,这种应歌词所抒之情,并无特定的时空限定或独特性,而是具有明显的普泛化、共通性的特征。该普泛化、共通性的情感,就是建立在与歌妓交往中所产生的特殊心态之上的。
词人应歌填词,歌妓歌以佐觞,是唐宋两代士大夫社会司空见惯的风俗行为,也成了中唐以来约定俗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交仪式。这种仪式渗透到了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这种仪式还出现在各类节序和祝寿活动中。节日即兴填词,按谱唱歌,是唐宋节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节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词的创作,填词唱词则又成了节日社交、娱乐和抒情行为的一种表征,一种特殊的语言,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同样,文人士大夫在“一张一弛”中形成的日常风尚习俗,也是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节日是短暂的,表征节日风俗行为的,除了词体外,还有杂技、戏剧等富有表现性的文艺样式;那么,士大夫在日常生活的风俗行为,则随时随地地发生着,不时地编织着“生活文化之网”。而这张“生活文化之网”的构成,则主要是按谱填词,付诸歌妓,歌以佐觞。因此,在唐宋产生了大量融社交、娱乐和抒情三大功能于一体的词。这些在唐宋词的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以社交与娱乐功能为主导,辅之以抒情功能的词,并非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其显现的首先是形而下的实用功能。词的实用功能虽然缺乏纯文学、纯审美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所给人的那种崇高性,而且,在所谓“思想性”、“艺术性”上,正如周济在指斥应歌词时所说的“无谓”,即无聊、毫无价值。但对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而且作为被后世称诵不已的新的文学样式,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动力,正来自这种实用功能。
二
唐宋词体的社交、娱乐、抒情三大功能结构,源自当时社会的风俗尤其是围绕宴乐所表现的风俗行为;而该风俗行为是在彼此关联的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其中歌妓是个中介因素,词人按谱填词、歌妓歌以佐酒则是该行为中的两个核心因素,并由此形成了以歌妓为中介、音乐上的歌唱主体与文体上的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事实表明,该运行系统是唐宋词体的原生状态,也是词体三大功能结构赖以生存的关键所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环节上。第一、在词与乐的配合上。词与乐的配合,归根到底就是以歌妓为中介的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配合。支配酒令艺术与从酒令转化为令词的核心规范,一是以曲子歌舞为形式的依调撰词和以词入乐的“以曲拍为句”;一是以酒令的核心人物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互为驱动。前者是酒令艺术之所以成为燕乐的一个分支和酒令转化为令词的方式,后者是该方式得以运行的系统。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第二、在词的创作上。以曲子歌舞为形式的酒令的出现,推进了“以曲拍为句”的令词创作,也标志了盛唐以后宴乐风俗的演变;新的宴乐风俗,又为词的创作及其功能的发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与条件;而词体及其功能赖以生成的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则是新的宴乐风俗的重要标志。以歌妓为中介的音乐文学系统的运行,既使词与乐、文人填词与歌妓唱词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有机体,又孕育了一批擅长填词的人。第三、在词的传播上。与文学样式诗文的传播不尽相同,词有自己的传播方式或类型。其类型可大致概括为即时性传播与历时性传播两种。即时性传播的唯一传播媒体是歌妓,传播的对象是包括词人在内的听众。历时性传播的媒体除了歌妓以外,又多了词集包括选集和别集一项。如果说即时性传播的过程,就是词体及其功能结构的生成过程,那么历时性传播则是词体生成以后的功能不断发挥、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就运行系统而言,为了“蕲传之有所托,俾人声其歌者”而集歌征词与为了“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而“所为乐府新词”的性质是相一致的,两者皆融社交、娱乐、抒情三大功能于一体,都是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的产物;就社会文化学而言,两者主要是宴乐风俗行为的表征,都体现为世俗文化的品格。
三
风俗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与经典文献式的理论形态的高层次文化相比,属于习惯性的生活形态的低层次文化。低层次文化是社会各阶层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人们直接参与其中、宥于其中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它具有一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标准和心理积习,又具有继承性的特点,一方面蕴涵着很深的历史积淀,一方面又是近乎日常的社会意识。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观之,唐宋词的文化层次和性质首先是属于低层次的世俗文化。确切地说,唐宋词从它的产生到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表现为具有世俗特征的宴乐风俗的一种载体。词作为宴乐风俗的载体,不仅具有社交、娱乐和抒情功能,是士大夫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交语言,而且集中的反映了该风俗的构成因素如心理积习、趣味原则、行为方式及其表现形态;但在文化品格上,词与载道言志的诗文相比,厥品甚卑,所以在时人的心目中属于“小道”、“小技”,甚至将填词听词视为“有玷令德”之举。
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限制了词的艺术肌体向多元化发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歌妓这个中介。从社会意义上说,艺术作品的创作成功并不意味着自身意义的终结,只有被接受者接受后,才能算是完成,其间往往离不开中介的作用。词不仅在作品的完成与听众的欣赏过程中,需要歌妓的配乐歌唱及通过歌唱在声音上的再度创造,而且词人文体的构思与创作过程中,也与歌妓密切相关。因此,歌妓不仅在作者与听众之间架起了必不可少的桥梁,同时融入了词体的创作中,限制了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和艺术肌体的多元化。从文化意义上讲,在歌妓这个中介支配下的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虽然孕育了崭新的词体,广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喜爱和接受,但积淀其中的是世俗化的低层位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歌妓能融化词人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换言之,朱唇皓齿的歌妓辈“可歌,方是本色”的灵魂与母体,是世俗化的文化品格,与作为高层位文化的礼教道统或诗教、文统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而且在文化层次上,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封闭性。
从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自足自立的独立性的角度出发,坚持词的“本色”论,有其合理之处,也不乏科学性。然而,从社会文化的多元价值与意义而言,由于体现“本色”的词体具有天生的不足,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冲破原有的运行系统和在此系统中形成的“妩媚”可歌的“本色”,健全与扩展其艺术肌体,赋予骚雅的艺术与文化品格,使之担负起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职能,成了南宋词林中势不可挡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