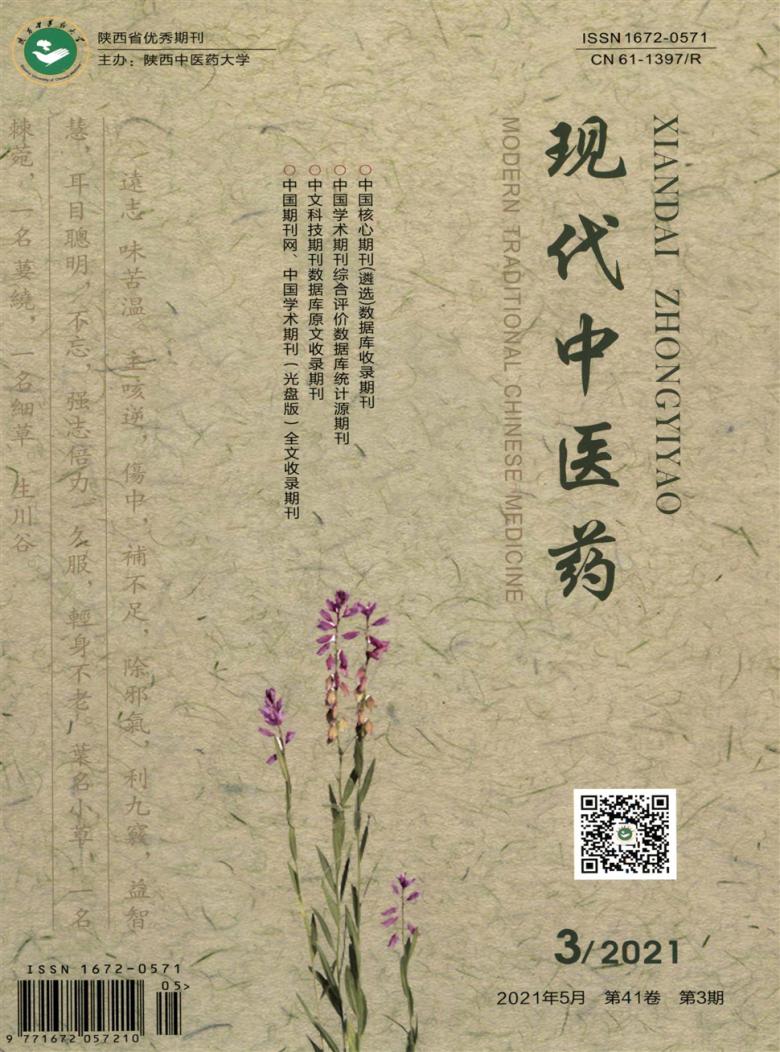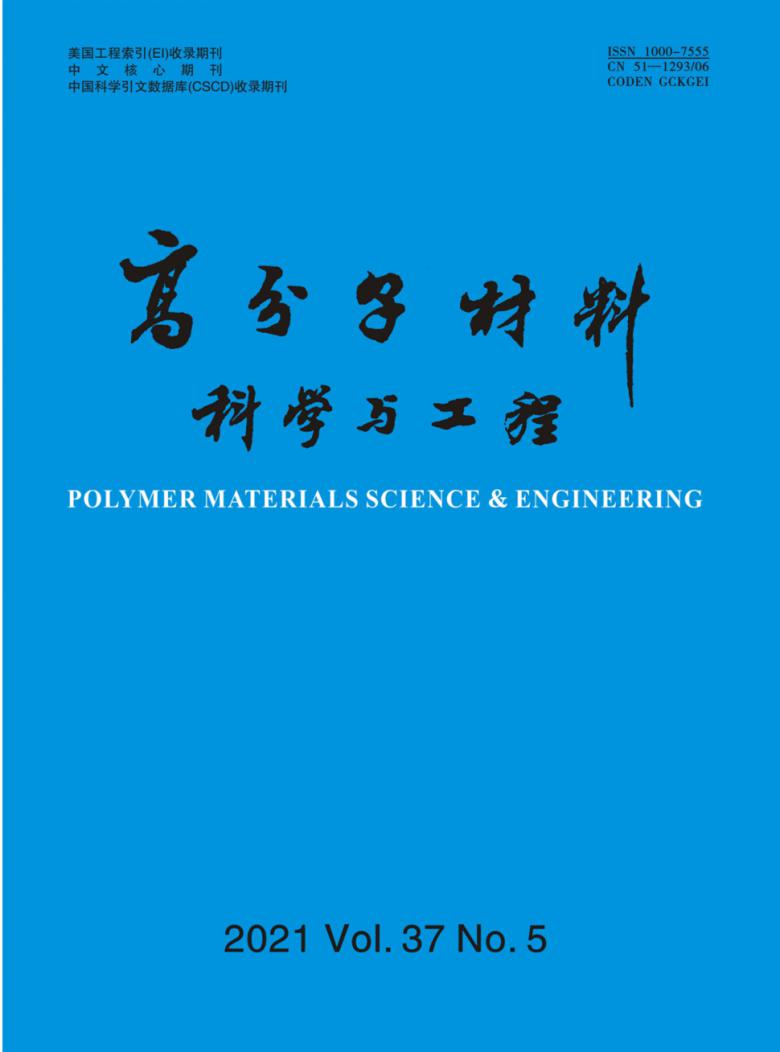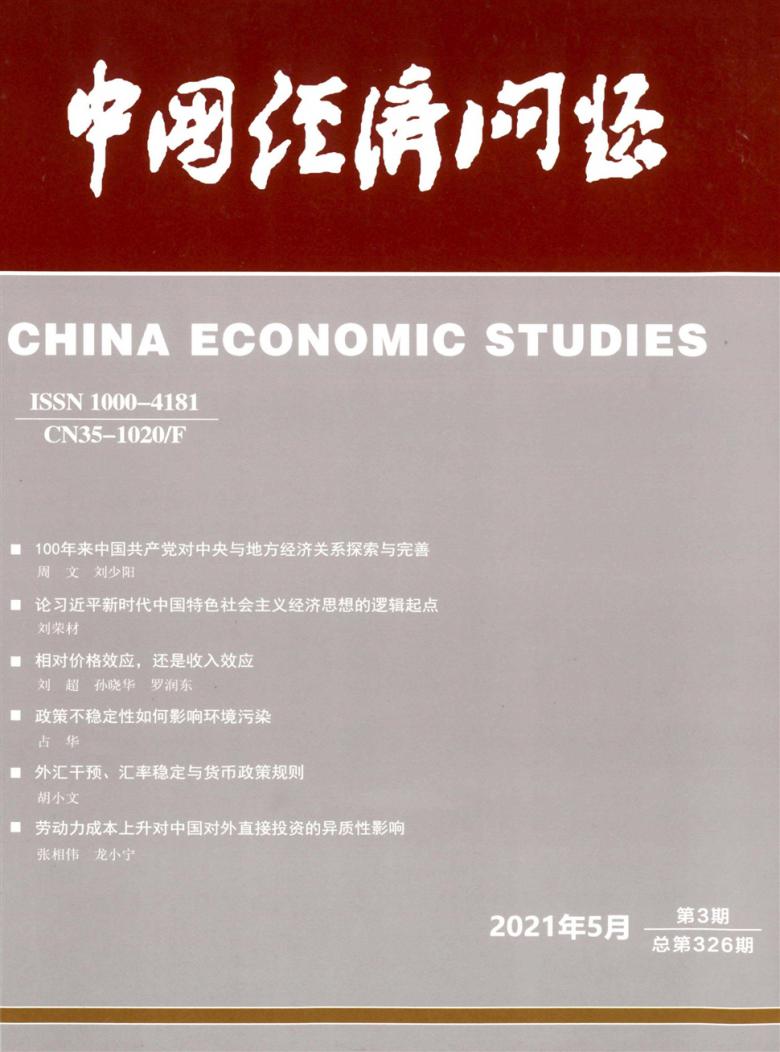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胡沧泽
【内容提要】福建与日本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联系。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的部分。早在唐宋时代,随着福建的开发与发展,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并频繁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进行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诸家。
【 正 文】
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 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贴,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出发时,朝廷一般还赠给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各种人员以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这些物品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团成员在到中国后作为费用而赏赐的,使团人员也会带上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这次遣唐使舶到达福建的还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 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由陆路跋山涉水,前往长安。空海在唐朝留学期间,与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归国后,努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注:[日]《大师御行状集记》、《桔逸势传》。)。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 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注:[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 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注:[日]《智证大师传》。),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乃,南方小国林立,福建为闽国所统治。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由随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任之,张睦“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注:《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在福建泉州, 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邽为泉州剌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注:《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当时这些船只主要是发往东南亚各国,但也会间接或直接与日本有往来。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政局较为稳定,福建在唐五代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事业勃兴。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七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滕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注:《宋史·日本传》。)。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第二年(公元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记》。)。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注:[日]《小右记》)。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注:[日]《续本朝通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注:[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这艘宋朝商船船头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两位。
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两次到日本从事贸易(注:[日]《朝野群载》。)。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时,呈上本国的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这份公凭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所有货物的名称及船上的其他器具,还记载了有关舶船出海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之间的海船组织、市舶制度及进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
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还比较落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随着中西交通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兴起,福建的各项产业也迅速发展。宋代,福建的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事业已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且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频繁地来往于福建与日本之间,从事磁器、丝绸等商品的贸易活动。
唐初的日本,生产力还较为落后,贵族专权,朝臣倾轧,社会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他们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派遣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经验。遣唐使团到福建,也与福建人进行了交流。
经过遣唐使时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渐丰,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样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了,中日之间的交往便逐渐由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元967年(北宋乾德三年,日本康保四年), 日本藤原实赖出任关白,朝臣尽归藤原氏,开始了百余年的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权期间,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本土文化正处于发展繁荣时期,统治者并不主动与中国建立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中日海上之间活跃的主要是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船。
南宋建立不久,在日本,武士平清盛以平定保元之乱(公元1156年)的军功,出任大宰府大宰大贰。平清盛接触宋日贸易并从贸易中获得巨利,便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宋贸易。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日本仁安二年)平清盛升任大政大臣,日本政权归平氏,启武士掌权之滥觞。平氏修筑港口,整治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向前发展。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日本养和元年),平清盛死,朝政归于源氏,源氏幕府和平氏一样,热衷于对宋贸易,南宋商人到日贸易时常受将军召见。源氏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亲造大船,准备赴宋朝佛。由于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和生产力的发展,故南宋时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不仅有包括福建船在内的中国船,还有不少日本船。
其次,福建造船业和港口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前提和物质基础。
福建与日本隔着浩瀚的海洋,没有船只根本不可能交流。而福建的造船业在我国则属先进地区。早在三国时期,立国于东南的孙吴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在温麻(今福建宁德地区)设有温麻船屯,负责建造船只。孙吴曾数次派军队北攻辽东、南取珠崖、儋耳(两地均在今海南省),又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 派遣有甲士万人的庞大船队到达台湾,这些大规模的航海所使用的船只也很多来自福建的温麻船屯。
隋唐时期,福建造船业继续发展,福州、泉州是两个造船中心。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高僧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睿、 普照曾派人到福州买船,准备东渡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福州的造船业已名闻遐迩、蜚声海外,并且具有横绝东海的能力。
宋代福建造船业加速发展,造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3。)根据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以后的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3。)。有学者据此推算,当时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注:陈高华、 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140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而且出现了“番船主”,为海商提供船只。
在港口建设方面,唐宋时期,泉州港、福州港等福建港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唐代后期,泉州港已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府(今广州)、江都(今扬州)并列为唐代的四大贸易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对外交往,又在闽江口外的黄岐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到了宋代,泉州港、福州港继续发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是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奠定了泉州在宋元之际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基础。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东方巨港。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和日本人的奋斗精神。
福建山多地少,有漫长的海岸线、无数的海岛和辽阔的海域,居民具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强悍气质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秦汉魏晋时期,很多中原人民南下,他们和当地人结合,成为福建的主要居民,共同开发福建的山区、沿海平原和海洋资源。唐代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隋时仅有12420户(注:《隋书》卷31《地理志》“建安郡”。), 到唐中期德宗建中时期(公元780—783年),户口却一跃而为93535 户(注: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为隋代的7倍多。隋时福建仅有建安—郡和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到唐玄宗天宝前后,福建已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和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建安、晋江、南安、莆田、长汀、龙溪、漳浦等23县(注:详参拙文:《唐朝前期对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这些州县除了一部分在山区外, 大部分是建置在沿海地区,从中也可看出福建沿海的迅速发展。沿海的福建人除了发展农业、手工业,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事业,他们积极与世界各国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注:《全唐诗》卷208。)在泉州,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很频繁。五代至宋,福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宋代泉州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竞相传播和发展,也显示出福建人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魄和胸怀。
日本地处海岛,日本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精神和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好学精神。唐前期,日本人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派出庞大的遣唐使舶赴中国学习。唐后期,尽管遣唐使已停止,但中日海上往来还是持续不断。到了南宋,在中国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和商人便有很多是日本的了。 三
唐宋时期,是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福建由僻处海隅的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为富庶之区、文物之邦。促进福建发展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之一乃是福建发挥自己的海洋优势,加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北宋泉州市舶司设置以后,市舶收入不断增加。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八年间,泉州市舶司仅因一个番舶纲首招致舶船,就获得“净利钱”98万缗(注:《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平均每年12万缗以上。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每年的收入有100万缗(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 《市舶司本息》。)。这些收入,已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支持了福建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和公益事业。福建输入日本的物品主要有瓷器、丝绸、干鲜水果、铜钱、书籍等。这些物品的远销日本,也反过来促进福建制瓷业、印刷业、水果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日本输入福建的产品主要有硫磺、木板、黄金、水银、珠子、折扇、日本刀等,这些物品进入福建,满足了福建人民在这些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丰富了福建人民的生活。
对日本来说,由于加强与福建的经济文化交流,福建物品、技术、人员输入日本,也促进了日本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据考古学者研究认为:日本古窑址的建造方式,深受福建古窑的影响。福建德化的盖德、屈斗宫和晋江磁灶等古窑址出土的碗、瓶、杯、军持等标本,在日本古窑址中也先后找到同类型的实物,可见日本制瓷业的发展与福建技术的传入有一定的关系。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的传入日本,也促进了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日本输往福建的各种物品,同样也促进了日本自身的硫磺生产业、黄金生产业、木材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