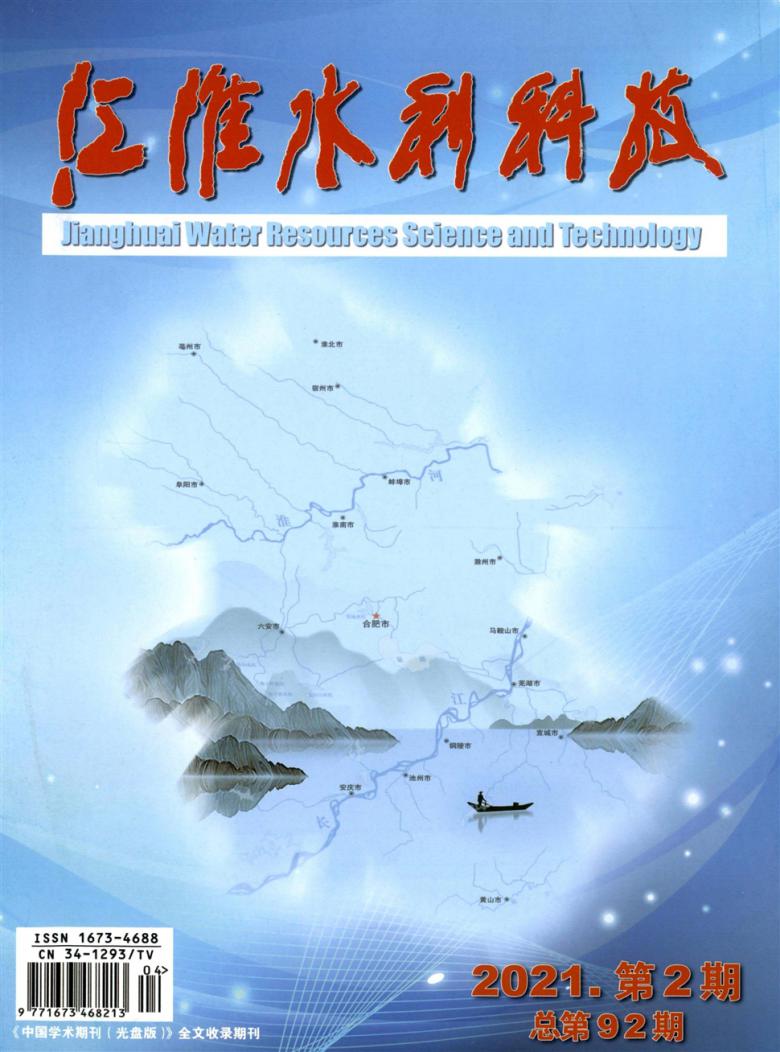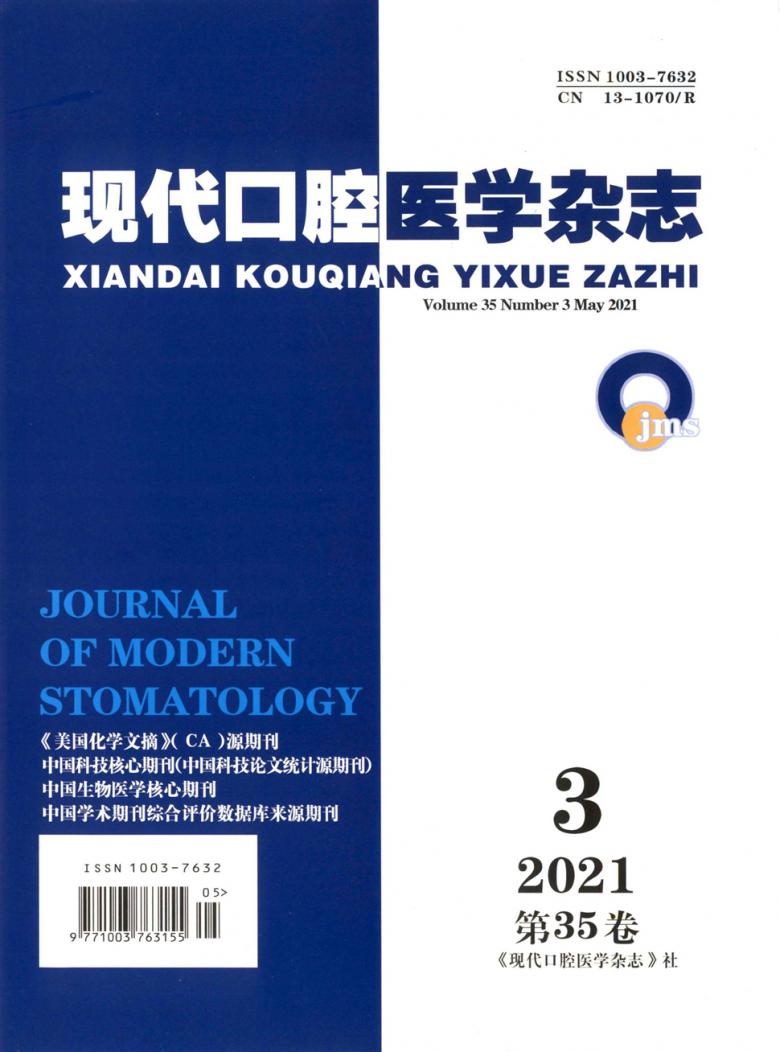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
佚名 2006-01-12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谁也没有预料到,曾经被当做靡靡之音的邓立君的《美酒加咖啡》在中国风靡一时,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引发了大陆的武侠小说热,为精英作家所鄙视的琼瑶小说令无数少男少女如痴如醉,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巨大转折。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无论是现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流行音乐、卡拉0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曾几何时,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种戏谑调侃下变得虚弱、甚至虚伪,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浦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50、6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80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来坞明星道格拉斯、黛米. 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马拉多纳。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而电视则成为这一时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媒介霸主。
电视可以化铁成金,也可以积毁销骨。电视不仅作为一种机器进入了千家万户,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甚至支配着芸芸众生。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在90年代末期,由于各电视台、电视频道的激烈竞争,也由于各种传媒之间的激烈竞争,也由于处在特定历史状态中的电视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的增加,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还珠格格》、《天龙八部》、《鹿鼎记》这样的娱乐消遣性电视剧风靡一时,《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玫瑰之约》、《幸运52》这样的游艺节目层出不穷,各种滑稽、戏说、打斗、言情、游戏、竞赌性节目纷纷出笼,甚至出现了多家重复覆盖的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一部娱乐电视剧、同时推出一类游艺栏目的"奇怪"景观。
这些娱乐性节目,提供的大多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消除了时间感、历史意识、与现实生存的真实性联系的自我封闭的文本游戏。在这些娱乐性节目中,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因而,在电视剧《戏说乾隆》中,一代乾隆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小生,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英雄豪气的故事也被写成了一个多角恋爱的滑稽、浪漫与狭义混杂的杂交戏,在《玫瑰之约》等栏目中,过去人们奉为神圣情感的男女爱情变成了逗人开心的现场速配表演。这些娱乐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个世俗梦想、儿童乐园和文化游戏,它不需要我们殚思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人们走进电影院,坐在电视机前,目睹琼遥言情故事的缠绵或金庸的武侠电视片的山重水复,目睹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英雄终于化险为夷,那些凡夫俗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些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人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共享一种被文化产品制造出来的欢乐。
在许多文化人看来,这些娱乐性作品如果不说是粗俗、平庸、浅薄,至少也与精致、高雅、深刻相去甚远,但它们仍然风靡中国,甚至令许多妇孺街谈巷议、涕泪沾巾,对此,不少文化人都痛心疾首,悲哀文化之堕落、艺术之堕落、人的品位之堕落。然而,在一个消费社会里,娱乐性节目的风行,有它自身的"现实合理性", 它们用对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对那些虚伪的道德寓言和价值观念的瓦解,以及那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超然于胜利与失败之上的人生态度,都为处在生存压力下的大众允诺了一种文"解放",它兴高采烈地抛弃了那些由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重负,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在清扫着文化垃圾的同时也满足着人们的一种"轼父"欲望。它们提供的是一个欢乐的平面,一个世俗化的万众同乐世界。
但是,也许应该清醒的是,当娱乐文化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产与经济利润相一致的时候,"金钱乃是评判所有这些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一个公分母"(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引自汪辉、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88页)娱乐节目很可能因为其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市场机制的操纵下而成为一种新的霸权文化,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它迎合的是文化公民"最低的共同文化"或者"最低的大众素养"(参见J.Baudrillard: Revenge of The Crystal, London, Photo Press, 1990) ,它排斥包括精英文化、边缘文化、前卫文化,甚至现实主义文化在内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这是以大众名义所施行的一种一元化专制。这种专制的结果,不仅意味着大众中的许多成员的文化诉求被否决,而且也意味着文化的多元格局被破坏。我们只有一种平均化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状态中,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众也失去了获得丰富多样的文化营养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只有一种宣泄性的、游戏性的娱乐文化,而我们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需求,我们从文化中获得知识、智慧、思想的精神需求,我们体验那些永恒的审美经验的精神需求都将被忽视和否定。文化工业所关心的始终是金钱而不是人,因而它所建立的文化帝国是一个能够换取利润的娱乐文化的帝国,而人的发展所必须的全面的精神需要对于文化工业来说,则被看"票房毒药"、"收视率毒药"而被禁锢。
显然,在包括文化、包括爱情、包括一切神圣和不神圣的东西都被消费化、商品化的时候,娱乐节目兴起所形成的对文明的挑战,与其说是娱乐节目本身的游戏化,还不如说是这种节目很可能因为其经济效益的本质,被文化工业生产为一种霸权文化,一种垄断产品,于是,不仅是那些脱离大众平均文化消费趣味的大量的大众的文化需求被剥夺,而且也意味着那些处在平均消费趣味线上的大众也将只能得到一种唯一的文化营养,造成一种文化的偏食,就像我们只能得到一种食品、一种维生素一样,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
因而,尽管电视是一种大众传媒,但新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应该不仅仅是一种被平均化、单一化、模式化的"大众"的文化,而应该是一种多元的丰富的现代文化,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它不仅是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大众的文化,而且也是那些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的大众中的若干小众的文化;它不仅要满足受众宣泄、松弛、好奇的娱乐性需要,它也要满足人们认识世界、参与社会、变革现实的创造性需要;它不仅要适应受众已经形成的主流电视观看经验和文化接受习惯,而且也要提供新鲜、生动的前卫和边缘的文化经验以促进人文化接受水平和能力的不断提高。总之,未来的电视文化既不是一种少数人垄断的霸权文化,也不是由"多数人"垄断的霸权文化,既不只是一种传达强制性意识的宣教文化,也不只是一种供大家相逢一笑的消遣文化,它不能用一种普遍主义的专制来否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它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一种大众与小众、共性与个性、高雅与通俗、主流与边缘、认同与超越、正统与前卫、男性化与女性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传播与接受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并存、互动的文化,它承认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它尊重人们所有的精神需求,只有这样,电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政客获取政治权利和商人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
也许,目前我们还缺乏建构多元电视文化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的建立只是需要我们以一种对文明、对我们自己负责的方式去探索而已,目前电视娱乐倾向的过度膨胀必将随着人们对电视文化的重新认识而得到调整。世世代代,人类曾经面对过许多挑战,最终都度过了危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依然会寻求到一种能够维护、鼓励和推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途径,而且这种途径不仅是政治性的同时也是经济性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符合人自身利益的文化需求不能经受文化市场的检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质素的提高,电视文化的多元性将不仅是一种公益需求,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产业需求--而这一点,在国内外的文化产业运作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正为我们提供了对电视文化多元前途的信心。
在任何时代,思想的多样性、个性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精神的多样性都始终是人类社会繁荣、健康、发展的文化基础,正如同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也正如我们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我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那样。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文化的多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正是那无数的溪涧沟壑为人类文明的江河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汩汩泉源。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的时候,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H.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Garden City &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P.53.)垄断、单一、霸权--无论是以专制者的名义或者是以"大众"、"人民"的名义--永远都是对民主、对人权、对人的发展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