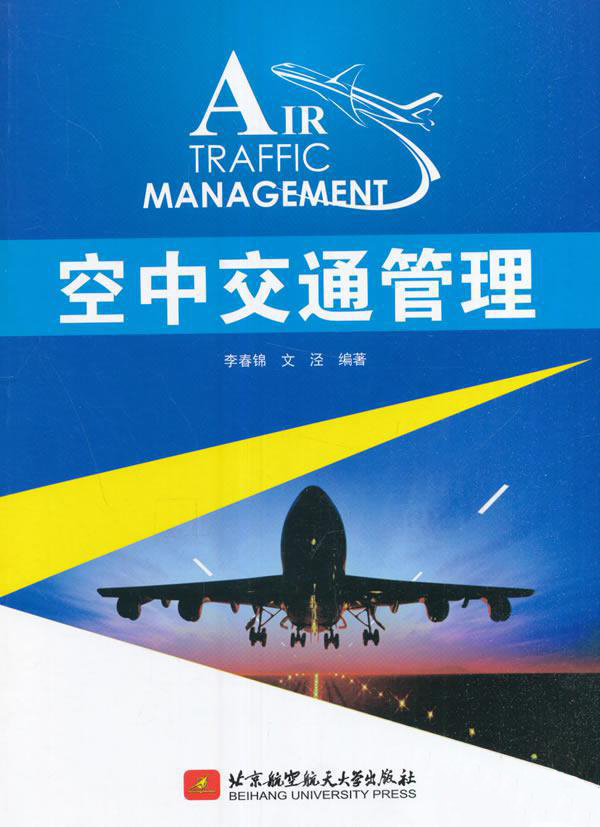关于在绝望处坚守从审美中突围——谈王晓明近年来的文化批评转向
郑文 2010-12-03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绝望;审美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家王晓明先生近年来的文化批评转向,源于他对当下社会的绝望和不满,希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介入,更批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就这样在绝望处坚守,靠审美来突围。
自上世纪80年代初,王晓明先生就投身于文学研究。他探索“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与茅盾一起在“惊涛骇浪”中寻找“自救之舟”;他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与鲁迅的心灵碰撞,虽然面对的是“无法直面的人生”;他也读老子、孔子、孟子和韩非子,从这些人物名声上的“大”看出他们精神上的“小”;他还和朋友一起倡导“重写文学史”、“重建人文精神”,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可以说,这几十年来,王晓明先生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中心人物,文学批评家们的典范,知识分子的“良心”,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著作也成为立志从事文学批评者的必读书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良好艺术感觉和人文气质,在文学批评界有着很大声誉的学者,近年来却一头钻进了广告、影视,甚至休闲杂志、娱乐装潢的研究里,不由让人心生诧异,一如他在一篇分析王安忆小说的文章中所写:“一个素来小心翼翼的人,忽然变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一个生性腼腆、动不动就脸红的人,竟然在公共场合放声高歌,唱个不停。你遇见这种事情,一定会停下脚步,多瞧他几眼吧?”…他是追风赶潮,还是对文学研究丧失了信心?他的文化研究指向的究竟是什么?他还会不会回到文学研究中来?当笔者读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的《半张脸的神话》,内心的疑惑便一扫而空,而对这位批评家的敬重又加深了几分。
王晓明的文笔是明快的,情绪是阴郁的。读他的文章,你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你满怀期待地打开书的第一页,迫不及待想去体味他娓娓道来的叙述给心灵带来的愉快;而当你合上书的最后一页,却总是陷人一种无可自拔的绝望与阴郁之中,甚至长久不敢触碰这样的文字。你看他的《潜流与旋涡》,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的“退化史”,那书中所分析的十二位作家,实际上是十二幅心灵的萎缩图;你看他的《追问录》,本打算从先秦诸子中找出解决精神危机的办法与思想资源,却读出了他们的可怜与可悲;你看他写鲁迅,发现这位一向被奉为精神巨人的“神”却和我们一样有着世故和功利的时候,有着忍不住清冷孤寂的时候……
这种绝望和阴郁的情绪来自于他对社会与人性悲观的洞察。如果说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动,而王晓明这种悲观的心境一直没有变。你也许会怀疑他这种悲观的真实性,你也许会说这不过是来自鲁迅的文字,是鲁迅思想的“存货”。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王晓明对鲁迅的认同,倒不如说是他和鲁迅一样获得了对人性、对社会同样深刻的洞悉。应该说,这是两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一头一尾所达到的心灵共鸣。
如果说早期的王晓明更多地是从文学文本、从作家的文字中去发现国人人性卑微和精神委琐的根源,并且不无乐观地相信自己以及自己的同道们在这种批评上的努力与文字上的呼告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1990年后的现实却破灭了他的这种设想。“当汹涌的激情消退以后,那种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现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迅速占满了我的全身。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我原有的陌生感上,又迭加上一层新的陌生感。”
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90年代以后的王晓明,蓦然发现原有的知识结构、仅仅局限于文学之内的批评分析,无法解释上述问题,他再度陷入无所适从的彷徨与看不清现实的绝望之中。他是这样描述今天的中国所经历的几个不同的变化的:“新崛起的‘权力——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和掠夺社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有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却开始承受全方位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破产……”“无疑,这种状况是让人沮丧的。面对绝望,一方面,王晓明用“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来表明他的态度,这跟鲁迅“绝望的反抗”有着近似的内涵,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避免失败还在绝望处坚守的人世态度,这就是他为什么转入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认为惟有打破原有的知识格局,采取一种更开阔的视野看待现实,用更为综合的办法(可以是人类学、社会学,也可以是心理学、政治学)分析问题,才能批判性地深人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而这正是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
无可否认,王晓明有着很好的艺术感觉,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他自己也曾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最愿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小说,写那种具体作品分析的文章”,“从内心来说,我对那种从容安静的书斋生活,又真是非常神往”。面对自己得心应手并且取得极大成就的研究领域,面对自己其实渴望宁静的内心,面对师长、同辈和朋友对自己偏离文学的质疑,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这个词语越来越遭人忌讳,很多人已不愿意再以这个“过时”的名词称呼自己的年代,他还是以知识分子自居,他非常赞同萨依德对知识分子的信念:“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能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既能成功地达到那个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觉、扎实——任何感到这种欣喜的人,将体会到那种融合是何等的稀罕。但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和权威来引导之间作出选择。”简单一点说,知识分子永远站在主流的对立面,永远站在“边缘”和“弱势”群体的一边,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文化研究领域后的王晓明,不厌其烦地去揭露正遮蔽和粉饰现实的“新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去揭露“成功人士”的另一半“肖像”和“新富人”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他关注改革问题,分析社会阶层,着手他的“三农问题”研究(王晓明《L县见闻》,见当代文化研究网)。他更愿意去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问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丢失一个人文学者的敏锐,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纷繁的现实和虚饰的意识形态所遮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践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当然,王晓明的文化研究也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对“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会不会有概念先行的隐患?比如,他一以贯之的精英态度会不会影响他的判断?又比如,学术资源的不够全面会不会导致研究成果的不够可信?这些都是。但有一点,王晓明把学术当成微观政治,毫不掩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永远从弱势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算是真正触碰到了文化研究的本质。在西方,无论是对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为大众文化辩护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无论是着眼于意识形态分析的阿尔都塞,还是致力于“东方学”研究的萨依德,他们的学术立场无一不是站在主流和强势的对立面,为弱势者说话,为边缘者张目。
正如有人认为,鲁迅的思想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或者说,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者批判现实的时候异常深刻,而重建现实的时候却偏于幼稚。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对未来是绝望的,他不相信所谓的“黄金世界”,认为在那未来的“黄金世界”里依然会有“绞刑架”,依然会有人牺牲,所以他宁愿做一个“历史中间物”:“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问,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王晓明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你对“新意识形态”的揭露之后,用什么来重建中国人的信仰?现实的泡沫消失之后我们该往哪里走?他对摩罗说的一段话让人非常触动:“我头脑中没有上帝,没有如来和安拉,其他的东西,我现在也都看破了,剩下的都只有艺术,只有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性,我当然要抓住不放了。”是啊,偏离了文学(或艺术)研究的王晓明发现最终的拯救力量还是在于文学(或艺术)。因为艺术指向人的直觉和想象力,指向他的整个灵魂,它以表象的方式激动人最深刻的内心情感,这样造成的“感动”是单用那一套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分析方法所难以解释的。所以,他坚持给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上文学作品课。他相信当学生们接触到好的文学作品时,哪怕对其作品背景一无所知,也会被作品牵带着,进入一个他平常不大进入的情感世界,他这样说:“蔡元培说过,‘以美育代宗教’,文学艺术能不能替代宗教姑且不论,但它是有力量的。虽然它看不见,你也无法像数钱一样把它数清楚,它可以无限大,也可能很小,但它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所以我相信它的作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王晓明暂时地离开文学是为了最终回到文学,因为这是他的精神底线,是他精神的最后一块阵地(在今年一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可以看到王晓明先生的近作《红水晶和红发夹》,是对一部当代小说的细读,文章细腻的洞察和绝妙的感悟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王晓明)。他总觉得千百年来那些伟大的作品感动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这份感动本身是元论如何也无法颠覆的,所以他才会一再强调《卡拉马佐夫兄弟》给他带来的震撼,所以他才会对王安忆的创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一方面他对现实极度悲观,对一切都持以怀疑的目光,另一方面他又对文学(或艺术)抱有罕见的乐观,坚信文学是最终重建人类精神的力量。他自己也曾说,很多年轻朋友对他这种“审美的突围”不以为然,但他还是打算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一如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期必胜”。
“我不相信庸俗、粗劣和黑暗的事物能够永存,但是,只有当真正优异的文化发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地消失。在几无退路的绝境里,积聚全力,一点一点地激活和创造优异的文化,一寸一寸地去击退四周弥漫的庸劣和黑暗……”’无论如何,这种批判家的悲观与绝望、乐观与信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