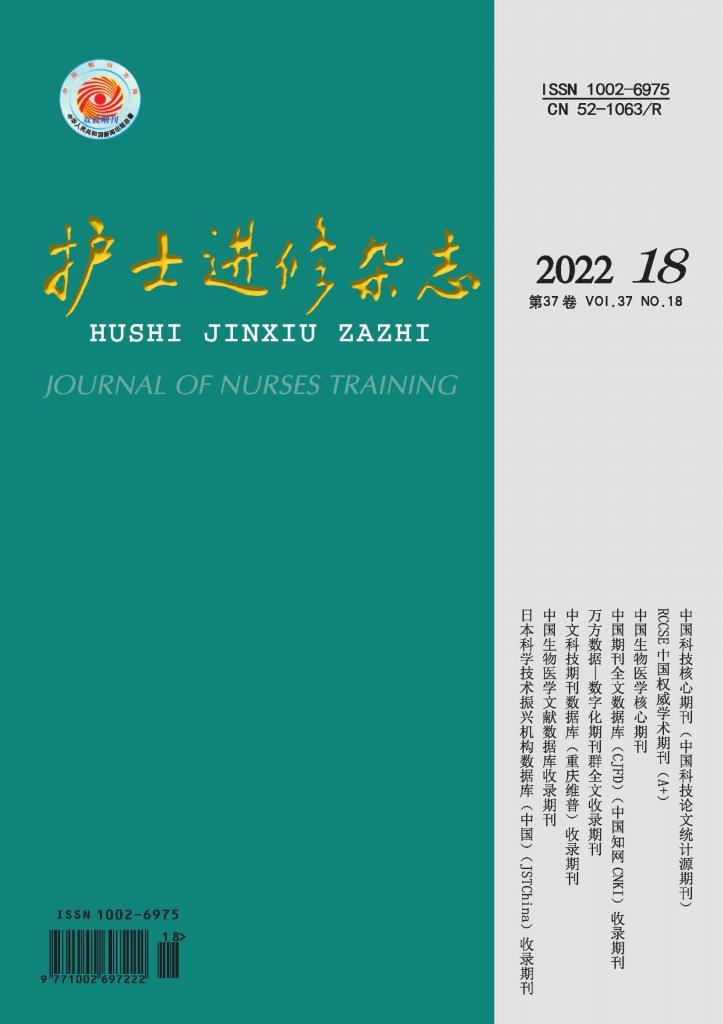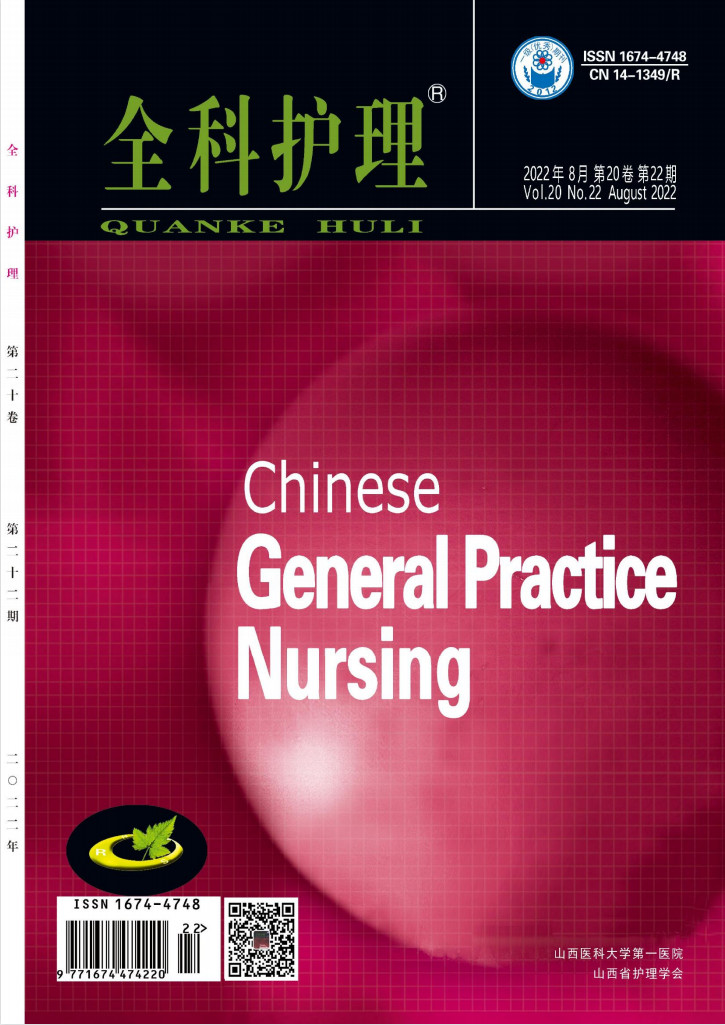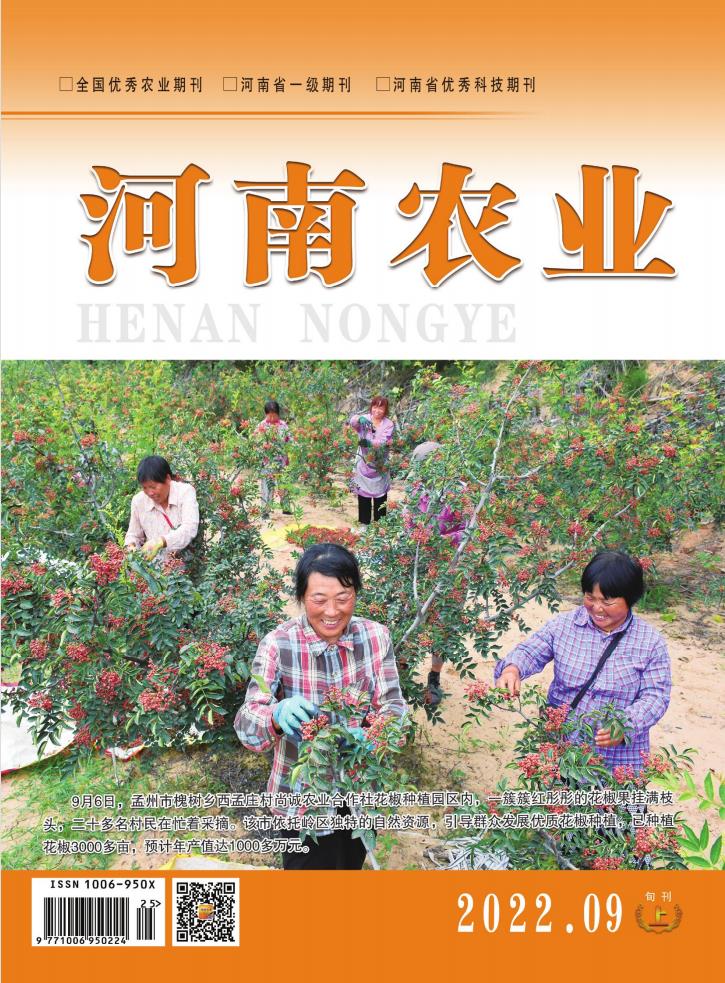皇权·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
汪 兵1 汪 丹 2006-04-12
摘要: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由此生发出迥然不同的两类国家模式。在中国式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中,皇权、绅权与族权都是血缘群体共有制的产物。三者的同构性在于:它们都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祖权的制约——都必须遵守群体利益至上的祖宗成法。因此,三者的关系,绝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私有制上“公共权力”与“个体私有权”二元对立的分权关系,而是父家长专制集权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绅权也并非是国家的“授权”。
关键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皇权;绅权;族权;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摘要: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由此生发出迥然不同的两类国家模式。在中国式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中,皇权、绅权与族权都是血缘群体共有制的产物。三者的同构性在于:它们都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祖权的制约——都必须遵守群体利益至上的祖宗成法。因此,三者的关系,绝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私有制上“公共权力”与“个体私有权”二元对立的分权关系,而是父家长专制集权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绅权也并非是国家的“授权”。
关键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皇权;绅权;族权;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宗族与乡族自治问题是当前社会史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少社会史家把宗族和乡族的自治同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对立起来,如当郑振满先生提出明清“基层社会的自治化”时,就“有人批评说如果都‘自治化’了,那么‘国家’到哪儿去了?而且似乎和通常认为的‘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相抵触”。对这种非此即彼,既未打通历史,又缺乏辩证观点的批评,郑振满先生的回答是:“所谓自治化……是明代中叶开始形成的一个‘授权’的过程,就是说政府把原来属自己管的一些事情交给乡族去管,但是很多人却把自治化理解为“闹独立”,搞割据。当然,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会有闹独立,搞割据的问题。但在常态下,民间是尽可能地利用政府认可的那些象征符号来做事。”[1]这个回答只强调乡治与国治同一性的一面,但并未对“自治化”作明确的理论阐述。自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是一回事吗?它仅仅是政府对乡族的授权过程吗?
我认为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需把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放到中西两种不同的国家模式的大背景中进行整体比较,并将对比的时间严格限制在近代东西方文明发生剧烈冲撞以前,而比较的方法则是辩证的综合分析法。
个体与群——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脱离整个文化背景就不可能理解文化的任何一种特质。”[2](P2) 毛泽东则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就是说,要鉴别乡治与自治的不同特质,就必须将它们放到中西文明不同生发模式的“文化背景”上去加以比较。
众所周知,西方(特别是欧洲)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3](P21)因此,面对人口压力和资源枯竭的挑战,便无可选择地采取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这是欧洲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这一文明生发模式,意味着:
一、彻底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用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体私有制取代氏族公社的血缘共有制。
二、主要以掠夺战争和殖民战争推动文明进程。
三、建立以经济发展和占有财富为根本目的,以保障和发展个体私有制经济为主旨,通过立法和法制支配社会的国家。
四、基于个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根本原则,国家只能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超血缘个体的联合。国家与团体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二元对立契约关系,即由团体或个人基于同意信托,经过自由选举,推选出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公共权力”执行者。即恩格斯所说的:“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4](P168)
五、这样的国家机器不仅担负着对内协调社会秩序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对外开拓与殖民的重任。因此,一部西方的文明史,大抵也就成了一部扩张、掠夺和殖民的历史。用恩格斯的话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P174)
六、国家的结构必然是建立在分权和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从西亚的早期城邦式国家苏美尔、巴比伦到欧洲的城邦联盟式帝国古希腊、罗马,直到近现代的由联盟放大而成的联邦帝国大英联邦及美利坚合众国,大抵如此。
中国则得天独厚地具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加之又地大物博、处于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所以,中国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枯竭的挑战,便以类似细胞分裂的方式,繁衍出许许多多同质的、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村落,由此又通过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和相互间的融合,逐渐形成同质文化的大一统国家。因此,中国的文明生发模式便不同于西方,大抵是一种集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发模式。这也是中国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这一文明生发模式,意味着:
一、文明进程始终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原始血缘氏族制度的基础之上。原始手工业和商业始终是农耕生产生活的辅助,而没有向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展。
二、至氏族社会晚期,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相对枯竭的矛盾姗姗来迟时,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旨在争夺祭祀、军事和农业的宗主权和领导权的内敛式兼并战争,来推动文明的进程。即一方面,在氏族制度基础上,以最强大的部族为核心,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为分层的标准,使拟血缘的部族联盟,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越滚越大;另一方面,血缘族群内部男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血缘群体内部等级越来越森严,权力逐渐集中到最有权威的氏族父家长手中,以姻亲为纽带的父系制逐渐取代了以血亲为纽带的母系制。其结果,便是将政治权力渗透到氏族制度之中,使之向血缘的宗族化和异血缘群体的拟血缘化发展。从而将不同地域分散的同质文化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原先分散而自足的氏族公社,经历了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三个阶段,开始向方国和帝国方向过渡。[5]大约至夏、商、周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三、由此形成的国家,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式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集私为公的国家,而是、也只能是建立于血缘和拟血缘共有制基础上的家国同构的国家。它的职能自然不是保护和发展个体私有制,而是保护和发展血缘和拟血缘群体共有制——即政治权力与生产资料(土地)的按差等共有共享制度。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6]。
四、在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家国同构的原则,因而,中国的国家并非西方式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超血缘个体的联合,而是建立在血缘和拟血缘共有制基础之上的群体的交融与共享。国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二元对立契约关系,而是一元的伦理关系,即国君始终是血缘氏族的族长和拟血缘国族大族长,最终形成了位居于大大小小父家长之上的、高居于政治金字塔的顶端——被尊为“天子”的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不过是这些父家长们的总家长,只具有共有财产的使用权、管理权而非所有权。[7]
五、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群体共有制,决定了这样的国家既不存在对内扩大剥削的可能,也限制了向外扩张、掠夺、殖民的可能。因此,国家的权威主要不是靠暴力专政和立法司法,而是靠祖先崇拜和个人品德。国家的主要职能,也不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原则,发展经济,聚敛财富;而是以血缘或拟血缘群体利益至上为最高原则,来处理群体之内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的分配或冲突。对外则以防御和教化为主,无论国力如何强大,也未用于向外掠夺和殖民,与其说“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6]。
六、国家的结构自然也非西方式的建立在分权基础之上的联邦制,而是建立在专权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即不仅全国上下左右政令一律,舆论一律;而且,由古至今一以贯之。
要而言之,中国的国家与西方的国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明乎此,我们才能不为名词和概念的相同或相似所惑,对中国的文化特质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列宁所一再强调的“辩证法的灵魂”。
家国同构——皇权与族权的同构性
我们常说,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国家,管理这个国家的只有三个层次的权力:皇权、绅权和族权。三者同处于父家长专制集权的金字塔式统治结构中,皇权是金字塔之顶,族权是金字塔之基,绅权居中,是为皇权与族权的中介。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欲明白绅权的性质,必叩皇权与族权而竭焉。
若以分析的眼光看,君者,天下之尊也;宗者,家族之尊也。皇权无疑是拟血缘群体父家长权力的代表,族权则是血缘群体父家长的权力的象征。若以综合的眼光看,在这个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结成的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家国同构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层层套叠、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他既是血缘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是若干拟血缘群体中的一员,都必需遵循独特的伦理规范,必需遵守公私杂糅的群体利益至上原则和利益共享的所有制原则;必需承担着多重的责任义务并相应地享有多重的权力与权利。他们也都必需受祖权(一种为着保障家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集祖宗智慧之大成的家族宪法或集体领导权)的制约。只有祖权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能遵循它的原则,谁才能拥有父家长的实权与威严。以此观之,上至一国之君,下至一家之长,每个父家长都是这一独特结构的实际统治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即所有父家长都兼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或主子与奴才的双重身份,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概莫能外。他在代表或象征着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祖制”面前,同样也只是不得不俯首帖耳的“被统治者”。与此同时,家长小皇帝——关起门来,一家之长就是小家国的君王,在外面的卑躬屈膝,并不妨碍他在家中尽显君父的威严。
正因皇权与族权具有这种在血缘与拟血缘共有制下的同构性,所以,在古代中国治国如同治家;治家亦如治国。族权是皇权的基础,皇权则是族权的保障。它们的关系绝对不是西方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二元对立,而是公私杂糅、公私兼顾,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
首先,分散的小农家庭虽然在分配土地和纳税服役时,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却非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家族,个人或家庭都完全消融于“家族”之中,不仅夫妇不完全是家族关系的配轴,父子也不是它完整的主轴。包括逝去祖先在内的祖辈,与生生不息的子孙,共同构成了家族的生命流。在这始终强劲的生命洪流中,传统的中国人也无不把传宗接代视为天经地义的义务;将光宗耀祖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齐家”,归根结底也就是“齐族”。特别是在乡村生活中,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迫使他们一直为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勤苦地劳作,这种生存态自然限制了他们活动的圈子,他们终生所接触到的人际关系不外乎血缘姻缘群体和拟血缘的邻里关系,日常生活的外求很少,上赡父母、下育子孙已经够他们终生为之操劳的了,因而很难再生发出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对于官府,他们一向敬而远之,种种民事纠纷,通常都是由族人三老或地方绅缙排解,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与官府打交道,甚至以几辈人不登公堂为荣。《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与我哉!”便形象地概括了社会处于常态(而非失衡状态)时中国平民百姓的普遍心态。若按近代以来西化的国家观念分析,这种心态是典型的无政府心态,所以,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才将中国人比喻为一盘散沙。但依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家和万事兴,齐家正是治国之本。“家和万事兴”,无论是之于家庭、家族还是国家,皆是中国传统文化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其次,中国社会的族权绝对不是血缘群体父家长个人的权力,“齐家”也绝对不是西方私领域的治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族本位也就是群体本位,父家长与其他家族成员一样,都没有独立自由需求、意识和可能。族权与皇权一样,只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家是全体家族成员共有的家,是每个人生命之所系,父家长只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因此,“主事”也就不等于“独裁”,他行使权力、获得权利的大前提条件是,必需为全家人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着想,无论能力是强是弱,几千年来,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孝亲育子,已经成了父家长们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责任和义务,任何谋一己之私的行为,都必定导致父家长的大权旁落和家族的分崩离析。
再次,族权是皇权的基础。这不仅在于家齐于下,君才能治于上;更在于它与皇权的同构——皇帝不过是国族的大家长,治国与治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传统的“齐家”是关乎家族生存和国家安定的家国大事,它既不是私人领域的个人私事,也不是公共领域的国家公事,而是上至皇帝官吏、下至贩夫走卒共同肩负的基本职责。之所以自古天子提倡而且能够以“孝”治下,就在于“孝”与“忠”的同构——对于皇帝的忠,也就是对于国族父家长的孝。所谓国法,也就是拟血缘的血缘伦理。所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原本就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公私领域,也没有非此即彼的公私观念。韩非曰:“背私为公。”只要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群体利益着想,便是公。所以,孝即是德、即是公。只不过它相对于更大的公——拟血缘的“忠”而言,才带有“私”的成分和色彩。齐家也同样,只是相对于治国来说,它才具有“私”的含义。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共有观和共有制下,公与私是皆对立统一于“共”中,需视圈子的内外、大小,因人、因事、因时而判定。[8]
最后,皇权绝对不是皇帝个人的权力,治国也绝对不是西方“公共领域”的管理。皇帝是全国最高等级的皇族血缘群体与国族拟血缘群体的父家长,具有双重父家长身份。作为国族拟血缘群体父家长,他虽号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但一方面,偌大一片江山,既不是靠他一人之力打下的,更不可能靠他一人之力来管理,所以,他必须把“王土”按军功或在国家管理中所负责任的大小,以及与他的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给各级官吏共享;另一方面,由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整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他又必须将“王土”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编户齐民,以保证国家基本的税收。而作为皇族血缘群体的父家长,他更要将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保证皇家血缘群体的消费和奢侈需求,他必须分配给他们足够的土地和财产,从而使他们成为全国最大的血缘群体共有经济集团。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土地所有权就成了“观念形态上的天子所有权”[9](P9),而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则被按血缘和拟血缘差序等级层层分解为管理权和使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实际上是属于全体父家长按差序等级所共有的。而皇帝只不过作为全国父家长的总代表,凭借“观念形态上的天子所有权”,对全国土地行使着支配权和管理权,即使用权,而不具有实际上的所有权。[7]相应地,所谓的皇权,自然也不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及个体私有经济基础上的君主独裁专制,而是以皇帝为首的整个拟血缘官族金字塔的中央集权专制。
共同的权力与权利,把以皇帝为首的官族凝聚成一个层层套叠在一起的巨大的金字塔网络,他们共生共存、生死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官族父家长都是金字塔网络中的一个结,而每个结的上下左右,都是一张张千丝万缕、相互勾连在一起的大网。对官族父家长而言,倘失去家族根基,他们便无以在官族立足;若失去官族特权,他们便不能让家族显贵。因此,在统治和管理拟血缘国家时,他们也只能像皇帝一样,公私杂糅、公私兼顾地同时履行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父家长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或中央集权的强化、成熟与发展,便是拟血缘官族数千年群体统治的经验与教训、智慧与能力的强化、成熟与发展。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性质是“为保障、发展个体私有制,并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而产生的权利机构”的话,那么,中国皇权则是“为了保障和发展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并将各种伦理群体的利益‘均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产品和财富,任何奢侈和聚敛的行为都会破坏自然经济的平衡,而社会过分的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失衡,并由此引发民众的造反和起义。从夏代后羿驱逐太康“因夏人而代夏政”开始,直到太平天国的数千年间,造反或起义已成为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的某种“阀门”,“阀门”打开的结果,便往往得改朝换代。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历代统治者不得不把“均平”视为治国之根本大计,不得不致力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和由土地买卖带来的土地兼并,以确保拟血缘统治群体的共同利益。由此,不仅生发、成熟了欧洲封建社会不曾有过的以户籍制为保障的税收赋役制度,还相应地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拟血缘共生共荣观和“以民为本”的统治宪法。公乎?私乎?说它是为民之公也好,说它是为帝之私也罢,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大家的生存罢了。
中介作用——乡治与自治的本质区别
自治这个名词,古亦有之。例如,《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曰:“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这里所谓的自治,乃自律或自觉的意思,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治,虽然名词相同,内涵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所讨论的自治,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概念一样,都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
概括地说,西方的自治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以一定的契约为保证的分权制。这种分权制意味着、或至少在道义上意味着:
一、制定契约的双方的关系是对等的或有条件的,即主要靠契约维系和保证的,契约一旦失效,双方便再无任何关系。
二、双方的义务和权利皆由契约作出明确规定,除了契约所规定的内容外,契约双方皆可以独立自主地自行其是。
三、契约是通过谈判制定的而非单方面的宣言或授权,若出现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谈判修改契约来解决,不存在绝对服从的问题。
尽管在“强权即真理”的现实生活中,契约常常是一种“不平等条约”或沦为一纸空文,但毕竟是西方社会通行数千年之久的游戏规则,正如中国的伦理道德往往流于言行不一的虚伪,依然是通行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生存法则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是靠契约维系的,正如中国是靠伦理道德维系的一样。
明乎此,便应该明白:中国近代以前基本上不存在这种西方式的自治。或者说,中国式的乡治与西方式的自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如果说自治的本质是分权,乡治的本质则是集权,但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集中到皇帝老倌一个人手中,而是集中到乡一级的父家长的手中,亦即皇权与族权之间的绅权的手中。也就是说,皇权、绅权、族权都是父家长权,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如俗话所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罢了。
绅权可以说是“泱泱大国”——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近1/5的产物。俗话说:“山高皇帝远”,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皆不发达的古代,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管辖权大抵只能延伸到县一级(西汉全盛时就有1587个县或县一级的结构。清代全盛时,包括台湾共设1380个县),乡村的平民百姓甭说是难睹天颜,就是县太爷,也终生都未必见得着面。而族权的权限大抵只能限于族内,二者之间便是绅权的领域。也就是说,古代农民的直接管理者不是县官,而是大量或贤或恶或平平庸庸的土皇帝。他们是官与民的中介——进则是官,退则为民。或之于官,他们是民;之与民,他们又相当于官。换言之,绅权既是皇权的延伸,又是族权的放大,所维护的都是父家长的权威和权力,所奉行的则是同一个千古不变的、或有变化而无进化的“祖宗成法”。
换个角度说,绅权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产物。早在原始农业大发展时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农业,使得原始血缘氏族以类似细胞分裂的方式,繁衍出许许多多同质的、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村落。累世聚居的生活方式造成原始初民很早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地结成亲缘关系盘根错节的自然村群落,形成了一个个错综复杂的耕作圈、婚姻圈、社交圈、信仰圈。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交往的增多,加之各自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从而扩大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但不管地域文化多么不同,农耕文化的同质性决定了乡村始终是血缘群体生存之根。正因为血缘之根太发达、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拟血缘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只能是血缘群体的等级化、宗法化、政治化和异血缘群体的拟血缘化、伦理化、礼制化双向互动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由“亲亲”到“尊尊”的过程。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便是典型。伯禽受封于鲁,三年后才报政周公,就是为了“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世家》)。中国的礼,是中国农耕先民历经纷争磨合、日积月累而成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它既是拟血缘国家的统治宪法,也是中国式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无论是周公还是孔子,不过都是把它理论化、制度化、时代化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血缘群体不断拟血缘化或政治化、血缘氏族村落不断乡族化或伦理化的历史。
在这一漫长的拟血缘化历史进程中,雄冠一方而又知书达理或见过世面的乡绅,便始终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尽管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有所不同,而且良莠不齐,社会作用和贡献也各异,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则一以贯之。而且,中华帝国的版图越大,皇帝便越“远”,绅权的作用也就越重要、越张显。
支持这张硬件网络运行的,则是一整套伦理道德软件——以儒家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国家统治宪法。按照钱穆的观点,中国传统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士人政府”[10](P122)。从皇帝到士绅,大都受过儒家的教育,遵循着孔子的治国原则。但这个教育应是广义的教育,不一定非得认字才懂;相反,读了圣贤书,若没有社会经验,也“识”不得孔夫子的真义。因此,最早的绅权大约就是三老权,他们或许认不了多少字,但却一定是有经验有能力的德高望重之人。其职责与使命,也是双向的——对下代表政府实行教化;对上则代表乡人切身利益。他们的双重身份,也正是礼的双重内涵——“礼者,理也,利也”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绅士”不过是士人化了的“三老”罢了。
再换个角度看,绅权又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正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局限,决定了中国只能是维系生存态、具有内敛性和无为色彩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它既没有外拓、殖民的需求和能力,也没有对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需求和能力,就连地方官吏的数量和经费都有限。因此,上下官吏大都遵循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原则,任由一些具有权势或经济实力的家族,结成拟血缘群体父家长网络,管理地方日常事务。以致“父母官”暂时空缺,地方社会也会照常运作。正所谓:“不痴不聋,不成姑公。”就像《红楼梦》里平儿说的:“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但这并不等于姑翁真的痴聋,他们只是装聋作哑而已,一到关节之处,他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决不手软。也就是说,平时装聋作哑的皇权不仅是绅权和族权的最强有力的后盾,而且还是均衡制约它们的巨大力量。就拿军队来说,比起西方国家,我们是无兵的文化,我们的军队或许难以抵御异族的入侵,但若集中起来对付地方动乱,还是不成问题的,除非中央暗弱到地方势力足以取而代之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绅权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自给自足。
从政治结构看,乡绅特别是士绅,是生成国家官僚队伍的庞大后备储蓄力量;而故乡也是大小官吏退休致仕的叶落归根之地。乡绅的势力之所以能让地方官与他们合治一方,不仅因为他们是地头蛇,还因为他们与皇族和官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知道一个小乡绅背后,会有一张怎样的“一表三千里”的“官系网”?正是这种通天接地的网络输出输入,维系着官族与乡族、乡族与家族各种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开放与内敛的动态平衡。
梁任公在其《中国文化史·乡治章》中,就为我们详细描述了他的家乡茶坑村集“组织制度、机构运行、办理事项、社会制裁、争讼公断、征工服役、地方保卫、公共娱乐、经济合作、子弟教育”[11](P276-278)等各种功能于一身的乡治状况,充分体现出乡村自给自足的特性。乡村的土皇帝亦如君王,既不都是横行乡里的为恶霸,也不都是积德行善的菩萨。他们也和皇权一样,不得不大体遵循群体利益至上父家长统治原则,甚至比皇帝多几分忌惮,毕竟世代居乡,远亲不如近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风水轮流转;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兔子不吃窝边草……倘若绝了乡情,等于绝了自己一家子孙后代的根。所以,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土地爷”式的地方保护神的角色。近现代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便根于绅权。
要而言之——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总之,中国的乡治不是西方的自治,绅权也并非授权,而是与皇权一样,都是天授。这里所谓的天,也并非通常所谓的老天,而是被神化了的祖先。祖先的广义延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传统。换言之,族权、绅权、皇权皆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所授。与西方式的通过契约授权,完全是两回事。
族权、绅权、皇权三者既有同构的一面,自然也有权力与权利矛盾对立的另一面,但无论是忠与孝、公与私、理与利诸如此类的矛盾,也都不是西方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或“意义理性”与“实践理性”二元对立的矛盾。传统的中国很少有为个人牺牲家族利益的,也很少有为主义献身的。他们获取或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也绝非西方式的自由竞争,而是通过维护皇统和道统(或至少打着维护皇统、道统的旗号)去获利——不仅族权与绅权要以此去获得皇权的认同和封赏,皇权同样要以此来获得绅权与族权的认同和支持。维系和保证三者间的关系的也不是西方式的契约,而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
要而言之——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只有划清了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之亦然,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二者相辅相成。
[1]郑振满 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6]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J].《文物》,1985(2).
[7]汪兵.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论父家长的权限[J].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5).
[8]汪兵、汪丹.血缘·土地·共有观——兼论中国人的公私观[J].历史教学,2003(3).
[9]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A].冯尔康、常建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C].台北: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
[10]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