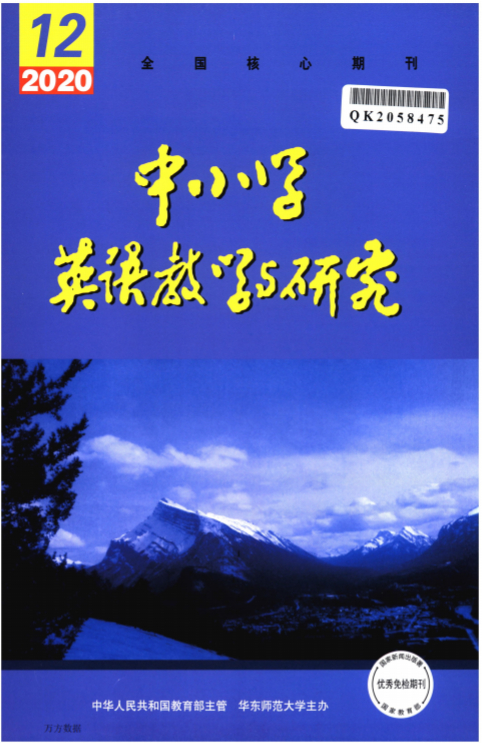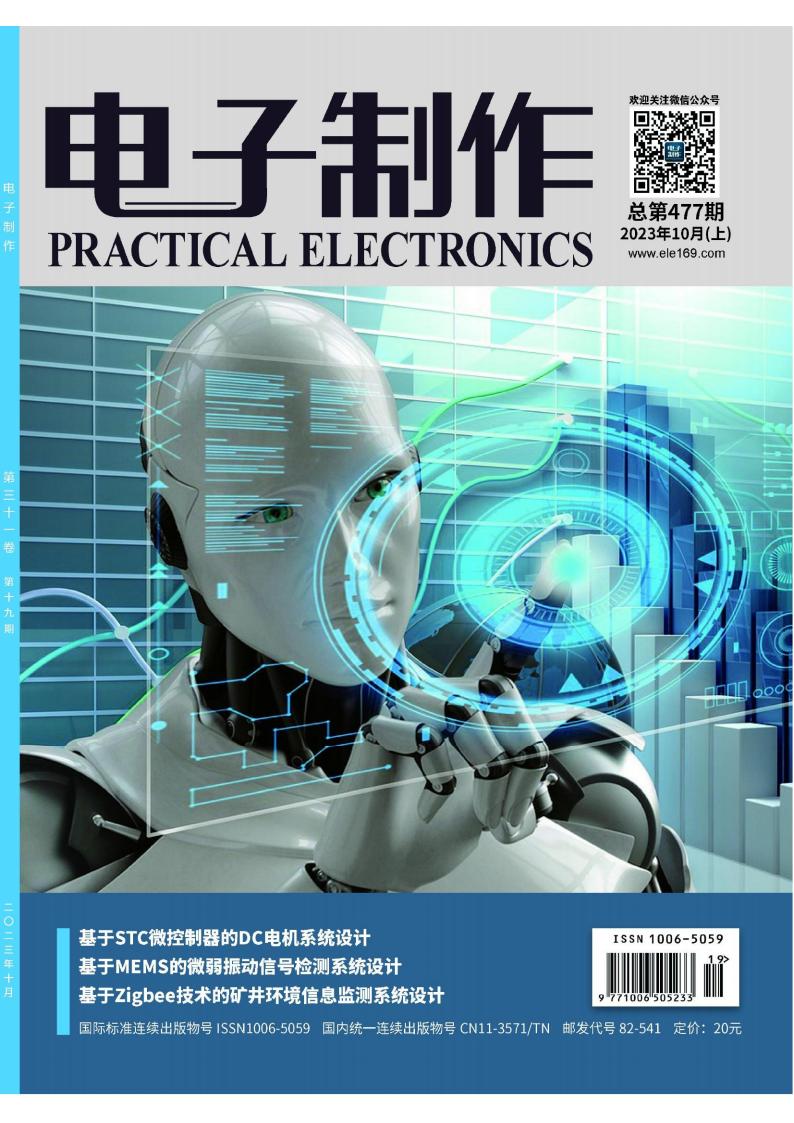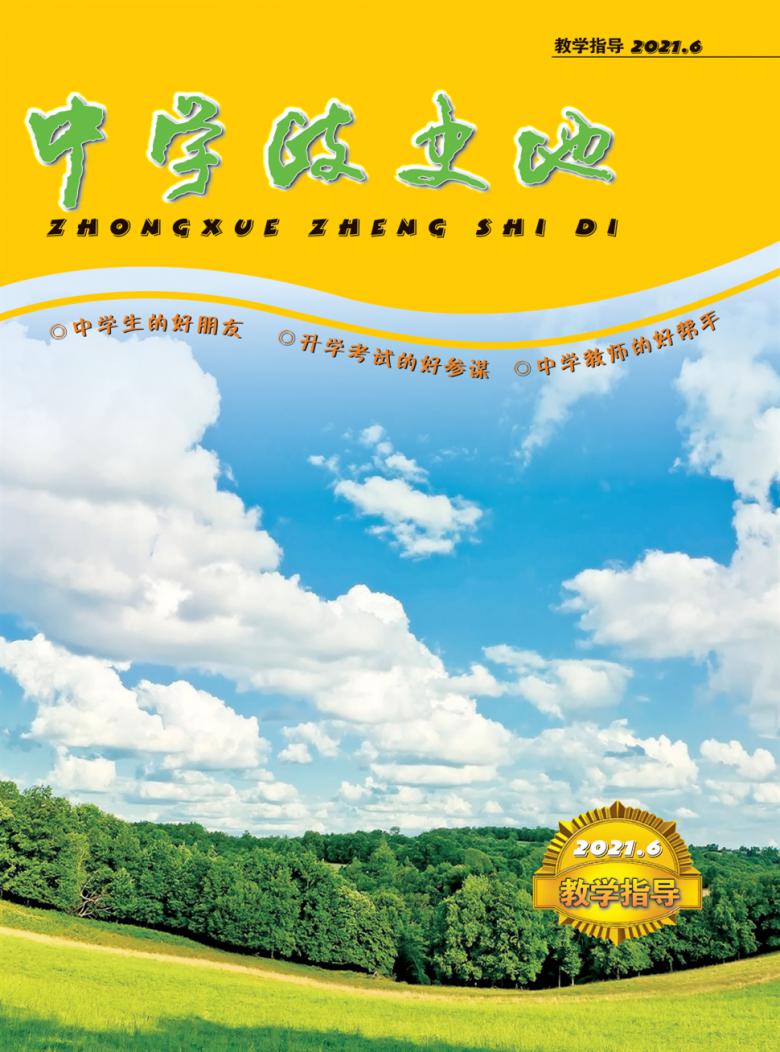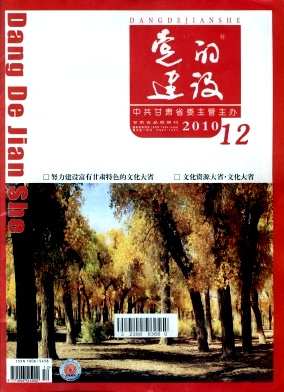试论西方文化对周作人文艺观形成的影响
陈平 2009-02-09
摘要:西方文化对周作人文艺理论中的现代性价值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以希腊的现世精神和理性精神和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重,这对周作人形成其”人的文学“等极具现代性内涵的文艺观点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现世主义;人道主义;人的文学;自由
站在20世纪风口浪尖上的周作人面对形形色色的中西方文化有着丰富的抉择机会,这对他成为一个文艺理论大家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我们都知道他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提出过“人的文学”、“文学的最高体现是自由”等极富现代意义的文艺理论主张,但这些理论主张的学理来源和产生根源却并没有被郑重其事地分析和研究过,殊不知这些决定着他文艺思想的“本质之源”的来源的蠡清,对于认识他文艺思想的现代性特征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他对西方文化的接收和借鉴这一方面。
周作人虽然在古代儒家文化中看到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把这种意识深入化、系统化、现代化还是在他随洞开的国门一起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文学之后。在青年时代进入了江南水师学堂之后,周作人开始真正学外语接触异域文化,最初的客观原因是为能读一般的理化及机械书籍,后由于兴趣和革命运动使然,他选择了希腊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蔼理士的性心理学,对于所谓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表示尊重与亲近,这里边波兰、芬兰、匈牙利、新希腊等最是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由于时势和本身气质的影响让他选择了颇具现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文学,而反过来讲,这些文化和文学又强化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
1921年五四落潮后,他在写给友人孙伏园的信中对自己的思想有一总结:“托尔斯泰的无我爱和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和尊重,却又不能调和在一起。”[1]这时他脑海里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模式,但要梳理起来也殊非易事,不过从他一生的言行里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条较为清晰的源流。
西方文化里首先不容忽视的是希腊文学的潜在影响。1917年在北大受命讲《欧洲文学史》以前,他了解得最多的是关于古希腊与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部分知识。当时他认为翻译希腊神话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发现希腊神话与其他国家神话相比更有独特之处:
希腊神话……最大的特色是其美化,希腊民族的宗教其本质与埃及印度本无大异,但是他们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诗人悲剧作者化雕刻家的力量,把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逐渐析出,使他们转变为美的影响,再回向民间,遂成为世间唯一的美的神话。[2]
希腊神话……最大的特色是其美化,希腊民族的宗教其本质与埃及印度本无大异,但是他们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诗人悲剧作者化雕刻家的力量,把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逐渐析出,使他们转变为美的影响,再回向民间,遂成为世间唯一的美的神话。[3]
因此,周作人在辛亥革命至五四期间写下大量关于希腊神话及希腊文学的文章,或译介,或评价。在他看来,“希腊文化,为欧洲先进,罗马以来,诸国典章文物无不被其流泽,而文艺学术为尤最。故言欧洲文学变迁,必溯源于希腊。虽种族时地,各有等差,情思发见,亦自殊别,唯人性本原,初无二致,希腊思想为世间法之代表,与出世间法之基督教,递相推移,造成时代。世之论欧洲文明者,谓本于二希,即希腊与希伯来思想,史家所谓人性二元是也。物质精神二重关系,为人生根本,个人与民族皆所同具。唯性有偏至,则所见亦倚于一端。故希伯来思想为灵之宗教,希腊则以体为重,其所吁求,一为天国未来之福,一则人士现在之乐也。”[4]而希腊精神中略言其要有美之宗教与现世精神,这两点是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盖希腊之民,唯以现世幸福为人类之的,故努力以求之,径行迅迈,而无挠屈,所谓人生战士之生活。故异于归心天国,遁世无闷之徒,而与东方神仙家言,以放恣耽乐为旨者,又复判然不同也。”[5]他在文艺上的影响便是:尚艺术之美,重现世之人。而且在为文和为人上都强调一种理性和节制的精神,这正是希腊日神精神的遗产,也是后世西方艺术精神尤其是古典艺术精神的源头。所以周作人在这一点上算是找到了一个本源,也难怪他能将之稳妥地和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习来的中庸精神和现世精神结合起来,探寻出一条中西合璧、既本位又极具超越精神的文艺理论思想。
其次是对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家的重视和借鉴。作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艺理论大家,周作人很注意从西方近现代文艺家身上吸收和借鉴适合当时文化革命要求和能促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理论,对他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文艺理论家主要有美国的汉特、丹麦的勃兰兑斯等,五四以后有列夫·托尔斯泰和蔼理士等。周作人对他们各有取舍,结合时势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注入了现代因素和人道基础。
汉特是上个世纪初一位美国文艺理论家,他的著作是周作人在1906年留学日本后接触到的,同汉特一起被接受还有持相似理论的十九世纪英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和十九世纪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汉特的《文学概论》被认为是在上个世纪初产生最大影响的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著作,他阐述的是一种带有某种折中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继承了以丹纳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社会历史学派的传统。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十分重视文学与社会的精神联系,强调作家必须浸透着社会运动,指出文学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文学必然地要接受社会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制约除了来自丹纳所谓的时代、环境、种族三大因素以外,还有作家本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又不可忽视文学巨大的精神教育和鼓舞作用。反对利用文艺来达成某种庸俗的物质与功利目的,否定西方当时风行一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汉特的理论显然深深地契合了周作人当地通过文学唤起国人精神自觉进而达到民族复兴的愿望,在1908年作《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能够看到很明显的影响,他几乎花了一半的篇幅来介绍了汉特的主张。汉特的理论不仅帮助了周作人确认了文学的巨大精神作用,同时也帮助他确认了作家崇高的精神职责,在文中周作人指出,当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这种责任更为重大且不可推委。“盖世运衰弱之际,所以籍于文人者,在能暴露时世精神,谴责群众以谋改造,无取乎漠然坐视或务一世之名遂以自足。”[6]而且和鲁迅一样,他主张救国的根本途径在于“立国精神”,即对人民进行精神启蒙,培育一种伟大健全的国民精神。“国人有此乃足自集其群,使不即于离散,且又自为表异以无归于它宗,然后视其种力,益发挥而光大之,渐以成为文化力而强也。”[7]文学担负着唤醒和振兴中华民族国民精神的职责,这是当时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也是周作人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体认。
这些理论很显然帮助周作人形成了他早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他自己把这种早期形成的思想特征概括为民族主义,并说明不同于传统那种盲目排外保古复古的“尊王攘夷”与“严夷夏之大防”的封建卫道者的复古主义,而是西方近代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发生的以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国民而非臣民”的民族主义,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现代民主意识的现代民族主义。这样看来,他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变相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他忧心的是在历史理性下民族内每个个体的命运,而非高悬于个人之上的概念上的家国利益,这使得他的文本多了些向下看的内涵,其范畴包括了儿童问题,妇女问题,民俗问题,国民思想问题,传统文化问题等,而非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什么主义,所以,这种人本主义是本位的,个体的,是脱离了传统含义上的人本主义,当然,这也因此使他的理论主张一开始便具有了现代性内涵和人道主义基础。
然而,真正在他的文艺思想中牢牢种下“人道主义”种子的还有西方的基督教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周作人自己曾经试着解释过自己理论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内涵,他说它不是悲天悯人和广施济众的慈善主义,强调了他人道主义与佛教精神的区别,但事实上他的人道主义是有宗教的“博爱”因素的。而西方狭义的人道主义根植于近代自然人性论,如爱尔维修所言,一为爱人,一为爱己。周作人两者兼具,其来源一是西方基督教精神,一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他虽然反感基督教对思想和人性的压抑,但对其博爱主张却极为赞赏,认为“近代文艺人道主义的源泉一半就在这里”。[8]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那种渗透着“对于全人类温暖的爱” 更是给他以深刻的影响。早在留日时期,周作人就特别钟情于俄国文学,翻译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深为俄国文学“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所感动。而这之中综合了上述两种来源的思想并给予周作人重大影响的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文艺著作《艺术论》被周作人多处引用并加以发挥,其一是为当时“提倡平民的文学,打倒贵族文学”的文学改良找到理论依据,要求文学真挚与普遍;二是艺术应当表现宗教感情,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合而为一,这些都是托尔斯泰的主要观点,而且,周作人还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那里间接吸收了托尔斯泰的世界主义理想,曾在五四后和李大钊等在中国发起过乌托邦社会运动实践,可见,他对托尔斯泰的信仰的虔诚的,这为周作人的文艺观在社会价值上提供了人道主义基础。
西学中还有一个较大的影响来自英国性心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蔼理士,其理论的核心是以生理学和人种学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人在谈到清末明初知识分子美学思想背后的哲学基础时也谈到,王国维背后有叔本华,鲁迅背后有尼采,周作人背后有个蔼理士,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基本不错的。周作人自己也曾一再强调蔼理士对他的影响,在《我的杂学》中他说道:“蔼理士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我最初所见的是他的《新精神》,其次是《随感录》、《断言》。这三种都是关于文艺思想的批评,……处处有他对于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高贵的,……看了他的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还要多。”[9]在五四高潮后,周作人频繁翻译引证蔼理士的著作。从周作人的自述与行动看来,蔼理士的影响主要有二:其一是从蔼理士的书中认识到政治运动只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反对群众运动。青年时代蔼理士卷入过十九世纪末英国兴起的社会改良运动,曾积极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热情地撰写过歌颂人类兄弟之爱的诗歌,但他很快就脱离了这种政治运动。因为他感到那种宣传家的谋划和说服与他格格不入,他不仅不是社会的,而且不是团体的。而从生理和人种上看,人先天存在着智、愚、贤、不肖等种种差别,除少数精英人物之外,广大群众始终是盲目、被动、和无意识的。因此蔼理士出于对群众的不信任,对诉诸群众运动的政治极其反感,甚至在后期著的《随感录》里把政治称为一种“疾病”,这对周作人产生了不小的启示:改造社会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个人发展的必要出发点和手段。因此他也反对诉诸群众运动的政治,反对以政治为目的的暴力。因此,在五四退潮和新村理想破灭后,周作人陷入了思想的混乱,在蔼理士的影响下,经过短期调整后,他决定躲进苦雨斋经营“自己的园地”,不再关注革命运动,以至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运动兴起后他不是支持而是冷静地批评;其二是为自己在中外文学中发现的“人”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周作人那里,“人”获得了高悬于其他一切思想之上的地位,以前,从古希腊里他看到了“人”的一生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他看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在蔼理士这里,他找到了这一切的理论依据,那就是:人是社会的,更是生物的。人的一切冲动包括性的冲动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伤害自己),一是关系法律(伤害别人)。因此他在文学中肯定人性人情的正当描写,主张文学是自我真实的表现,并说道:“欲言文学须知人生,而人生亦原以动物生活为基本,故如不于生物学文化史的常识上建筑起人生观,则其意见易流于一偏,而于载道说必相近。”这为他远离社会运动专注“胜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他心安理得,但在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上却有促进他肯定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作用。
此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英国现代思想家柏利的《自由思想史》对周作人自由思想形成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意义。幼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初步萌生的反抗专制向往自由的意识,在后天所受的教育中这种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曾著文多次强调柏利该著作对他的影响,而对希腊文学与文化的喜爱与倾慕也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知音。在该著作里,柏利追溯了自由思想从古代希腊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历程,并探讨了思想自由的阻力及其前景,并认为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于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周作人也因之相信:人类思想的历史,是由蒙昧走向文明、由压制走向自由的历史。其间纵然多有黑暗时期出现,企图以思想权威的专制精神取代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光芒势必冲溃黑暗,建立理性王国与自由的王国。[10]因此,一方面周作人本着对自由思想的自我追求在言语态度中表露出与众不同之处,另一方面在文学中提倡文学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进而是人的自由,这似乎体现着他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最高追求。
在西方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资源里,周作人充实了他人道主义理解中“人”的现世主义内涵、人性论内涵和世界民的外延,并实现了一种自由理念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提出了在五四时期甚至今天都极有影响力和借鉴意义的“人的文学”、“诗言志”、“文艺的最高体现是自由”等命题和论断,形成了他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体系。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周作人的文艺理论远没有现在丰富和精深,而且,他也可能因此够不上“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大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美誉。所以,在梳理周作人文艺理论思想的学理来源和挖掘其人道主义思想背景上,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和近现代文艺思想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一个大的方面。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一)致孙伏园》.
[2] [6]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3]周作人:《立春以前·神话引言》.
[4][5]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之希腊》.
[7][8]戈特尔堡:《蔼理士传》第127页.
[9]周作人:《夜读抄·性的心理》,另参阅三联书店版《性心理学》1987年第1版页256.
[10][英]柏利·思想自由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