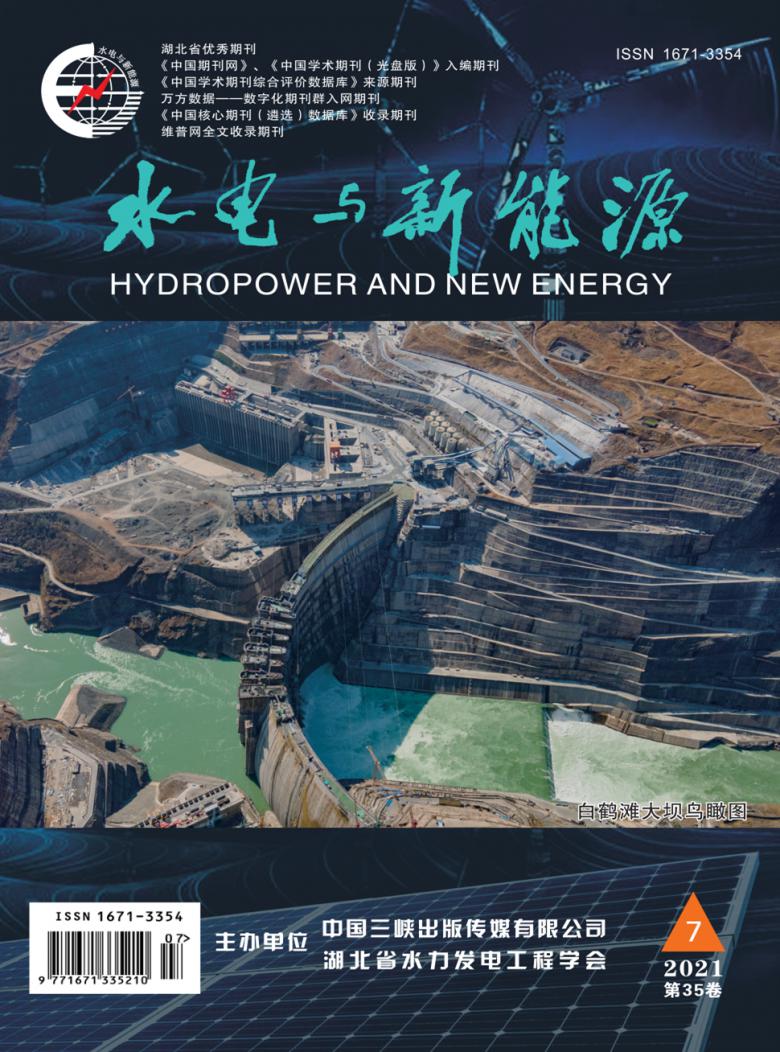关于“大众”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中的历史涵义
易前良
世界性民主观念的普及,使大众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在驯服少数人的强权时,因为历史的机缘,大众又形成了新的强权,“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法则”。①在文学领域里“大众”同样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20世纪文学的乌托邦就是建立在“大众”基础上的。从“小说界革命”到新中国文学的文学主流,以“大众”的名义,文学在革命和政治的语境里膨胀,“大众”就像一个幽灵,其巨大的身影覆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历史场景。“大众”的所指和它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其实是流动模糊的,而正是这一模糊性为文学的向外膨胀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大众”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简单的概括就是“文学的大众化”,文学大众化运动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后来进一步发展而被体制化,实际上,文学大众化已经在20世纪初新文学的源头埋下了它的种子。过去从雅俗之辩和文学功利性等角度,研究者对文学大众化现象表示了足够的关注,本文不拘泥于讨论“文艺大众化”的特定文学现象,而试图从大众意义的流动性和它与文学的关联入手,从整体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走向大众”作初步的分析判断。
1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文学的大众化时,把“大众”理解为一个恒定自明的概念,而忽略了“大众”所指的模糊性,这就导致对文学大众化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仅仅把它视为对文学进行普及的运动,没有顾及到它策略性的一面。“大众”一词最早可见于《吕氏春秋》,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大众”却来源于日本,郁达夫1928年在《大众文艺释名》中作了解释②。1920年代发起的大众文艺运动和1930年代《申报·自由谈》主持的大众语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大众”作出的种种界定③。可见,“大众”是对“群体”、“多数”的抽象指称,并没有具体的含义,它的所指因时而变流动不居。20世纪初,在“文界革命”诸君子眼里,大众就是“妇女粗人”;新文化运动中,变成了“庶民”、“平民”、“劳工”;三四十年代,又变成了“无产阶级”、“工农兵”;建国以后,统一的称谓是“人民”。
以上涉及到的是“大众”一词所指对象的丰富性和模糊性,同样“大众”和文学的逻辑关联也是不定、多向度的,具体而言,“大众”对文学有三种意味:1、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要求文学能最大限度地被理解和接受;2、从作者来看,文学要成为多数人自己能运用的手段,大众能直接创作文学作品;3、从文本的创作来说,文学要有一种面向大众关怀大众的理性的创作精神,它不应该摆在案头供把玩自娱,而要有真诚的看取人生的态度,去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把“大众”和“文学”合成一个词“大众的文学”,是单纯就读者接受而言的。而即算是“大众的文学”,其所指也是流动的,在共时的中西方不同语境和历时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指向不同的文学类型。在西方,大众的文学有两种类型:一是大众文学,严格地可称为市民大众文学,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大众市民社会形成后,文学被整合到市场的机制中,被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产物;另外一种含义可以理解为民间文学,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大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活跃于民间。讨论中国文学的大众性问题,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此前,中国的文学完全是精英化的,民间大众的东西仅仅是“观风俗、知厚薄”的资料性存在,不能作为“文学”而被认同。第一次从受众范围和主体发生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类型的划分,并给予梳理的是周作人,他在文学里给了“大众”一个位置。在1932年《中国新文学源流》的讲演中,周作人把全部中国文学分为纯文学、原始文学、通俗文学三种,并予以了界定,1933年,又在另一次讲演中修正了这一划分,用民间文学的概念替换了原始文学,可能考虑到民间文学与时沉浮或湮没无闻或被改铸,已与通俗文学纠缠在一起(换言之,纯粹的民间文学并不存在,只是知识分子脑海中理想化的审美类型),他具体的论述对民间文学存而不论,主要围绕通俗文学展开④。鉴于二者的胶合状态,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合称为民间通俗文学,这一文学类型的主要受众是几千年宗法制文化状态下的大众。
周作人的文学类型观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也基本上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历史形态,但另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却被他有意的摒弃了,那就是作为市民大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小说滥觞于1910年代的上海,渐成气候。它与民间文学有交叉的地方,夹杂着很多民间趣味和民间形式,但它面对的主要是都会市民大众,其创作中的许多现代性因子以及娱乐趣味性和商业化,无法被民间通俗文学所通约,因此把鸳派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市民大众文学——是合适的。市民大众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溃不成军,直到90年代中国市场商业社会的姗姗来迟,中国才再度大规模地出现这一类文学⑤。而民间通俗文学则非常发达,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
大众自身及其与文学关联的模糊性,使新文学和大众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把这种关系简单概括就是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新文学的大众化要求是与生俱来的”⑥,新文学产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在启蒙的目标下追求文学的大众效应,因此文学走向大众化也就有了它先天的因子,再加上后天的因素,民族存亡历史语境的设定和政治氛围的形成,使得其大众化诉求逐渐深化。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大众化,源于对古典文学的反动,显示了它鲜明的现代性追求。古典文学大多是文人骚客怡情养性、应吟酬唱之作,趣味高雅,流通范围主要局限于少数人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情况毕竟不是普遍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把古典文学称为“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从梁启超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拓者们改变了这一文学观,意识到文学必须面对大众,他们相信,民众具有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改造民众思想以唤起民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的大众化从一开始就是自明而无须追问的,文学要大众化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大众化。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历程就是它和大众的文学互动发展的呈现。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五四新文学反对把文学作为“快乐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对市民大众文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流风所及,将近一个世纪,市民大众文学一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对立面而遭到严厉的拒斥。新文学的主体,精英知识分子们,所面对的是长期处于宗法制统治下的民众,而不是有一定独立意识、生活相对优裕的市民。所以,市民大众文学被边缘化,或者在某一时段里以潜隐的形式被新文学熔铸于作品里,成为气质性的东西,这种整合主要是不自觉的审美意义上的继承。两相比较,民间通俗文学的命运则要好的多,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大众化,在否定市民大众文学的基础上,把民间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先定的理想模态,在理论上大力鼓吹,有时甚至不惜赋予以政治和道德的含义加以框定,创作上则要求在文学形式、题材、美学趣味和思想意识诸方面向民间通俗文学靠拢,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的主脉。
2
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大众性一方面与小说的文体性质相关,另一方面和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也不无干系。对小说进行发生学的溯源,就会发现这一文体原本就具有极强的大众色彩。《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出现“小说”一词,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20世纪初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本身就体现了文学对大众的诉求,梁认同传统中小说劝惩教化的作用,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说“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与这一传统小说观相联系,新小说家以封建等级观念为基础,把大众理解为“妇女粗人”,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把读者分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粗人”“惟妇女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⑦因此,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表面上大张旗鼓地提高小说地位,实际上包含了“学士大夫”站在精英立场上对小说和大众的蔑视,但小说在新思潮的推动下,获得了大批读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即滥觞于此。
随着维新浪潮的低落,适应上海大都会市民社会的趣味,新小说马上蜕变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民”的启蒙目标并没有实现,反而促成了市民大众文学的形成,这恐怕是带有强烈功利性的“新小说”的提倡者们所始料不及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从旧文化里走出来,新旧杂陈,和现代严格的市民大众文学有一定的区别。其发展断断续续达半个世纪,派别众多,趋尚纷呈,但大都有两个主要特点:才子气和商业气。鸳鸯蝴蝶派小说采用亦骈亦散的铺陈文体,语言雅致华丽,才子气十足,单看这一点它并不俗气,言语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情愁哀怨也是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他们提供了炫才使气的好机会,一批落魄才子把作八股文的工夫全使在这上面;同时又因为吸收了古代小说的章回体和其他叙事法则,使得它明显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的某些特征。因此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里第一次称它为“旧小说”后,马上得到了广泛认可。但鸳鸯蝴蝶派小说更多地带有古小说所没有的品格,如惊险、侦探、黑幕、恐怖等题材的开拓,思想观念的时尚化,尤为不同的是,它为现代的出版传媒业所催生所激发,完全融入了现代的文化市场中。文学研究会在批判这派小说时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⑧话说的有点过头,但说到现代趣味(即商业市民气)这一点却极其到位,算是击中了要害。
鸳鸯蝴蝶派小说遭到了新文学的猛烈抨击,其“现代趣味”成了新文学“为人生”的猎猎祭旗下的牺牲,在1920年初的那场大批判中,几乎成一边倒之局势。饶有趣味的是,文学研究会也打过“民众文学”的旗号,只不过这里的民众指的是生活在半宗法制社会的大众,而不是上海洋场的市民的大众。循着这一思路,表面上看来,新文学与鸳派文学的对立是历史进化链条上新旧文学的较量,其实不过是两种文学类型的争斗。经过封杀后,1920和1930年代,在文学研究会和乡土文学中基本上见不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响,在创造社的作品里却留下了它的痕迹⑨,以潜隐的方式,市民大众文学被整合到新文学中。创造社作家与鸳鸯蝴蝶派才子们的气质有契合之处,使二者的相亲近成为可能。从成立之日始,创造社活动的大本营一直在上海,其运作形式和趣味受海派文化濡染日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才子气在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里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商业气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则被张资平继承发扬了。
才子气在小说里具体表现为:作品无处不在的感伤情调,题材上偏好男女情爱,小说人物的任情使气。证之以郁达夫以《沉沦》为代表的大量作品,无一不符,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如《牧羊哀话》也是典型的才子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他很不满意小说里“科白式的对话和概念化的人物”,但却“难以忘记小说所流露的那种趣味”,而这种为作者所垂青的趣味就是才子式的感伤情调。另外,和《沉沦》一样,《牧羊哀话》在叙述中插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谣,炫才煽情,让人想起《花月痕》和《玉梨魂》的文体。可见,晚清以降,自艳情狎邪小说至鸳鸯蝴蝶派文学再到创造社小说之间的承传关系是有迹可寻的。当然,才子气只是对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进行概括以后气质上的认定,对人性的逼近和心灵的袒露决定了他们迥异于鸳派文学的精英立场。为了同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调相和谐,他们在个人书写时自觉地附加上一些宏大主题。《沉沦》结尾的爱国主义式的呼喊,显得非常突兀,与文本整体上的不符,人所共知;而郭沫若则借朝鲜之事来反抗日本,在《牧羊哀话》里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本着精英文学对时代的承诺,作者有意识地在叙述上进行了修辞性的处理。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小说中“大众”的因子,有利于新文学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尤其是郁达夫,在当初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除了真率大胆的笔触令人震惊以外,他的文体与情调对大众也是极有魅力的,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了。
如果说,新文学对市民大众文学的整合后留下的裂痕在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中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在张资平那里,随着创作的发展则得到了历时性的凸现。在求学阶段,张资平最喜欢看的是《留东外史》、《花月痕》等狎邪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后来的文学趣味。在创造社成立之初,由于受到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影响,自觉配合创造社整体的创作风格,他的前期作品,如《冲积期化石》、《木马》、《她怅望祖国的田野》,在感伤的氛围里表现诚挚的亲情和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30年代,从武汉到上海后,与创造社基本上没有了多少关联,他尝到以小说获利的甜头,开始想方设法地使自己的小说流行起来。据说因为供不应求,他雇佣了一批人按他的意图代为拼凑,开设“小说工厂”⑩。为了出版出售的快捷方便与获利,又创立了乐群书店,从生产到销售实行流水线市场运作,其小说的不堪可想而知。三角和多角情爱题材,平庸的趣味,机械复制的操作,使得他的小说彻底地通俗化商业化了,在小报上小打小闹的鸳派小说莫与能比。
3
1921年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以文学研究会为主体展开的关于“民众文学”的争论,可以说是文学大众化讨论的开始,不过正式以“文艺大众化”为名目的运动,发起于1928年9月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这一次讨论的范围大,延续时间长(从1929年到1932年,胡风曾把它分成三阶段,并进行过认真的总结[11]),1930年代末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讨论又起,延安根据地遥相呼应,最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政策文件的形式作出了总结。以上都是浮出时代水面的正式讨论,实际上文学革命就已经蕴涵了文学大众化的诉求,只不过其态度是暧昧的,既要保持精英立场又要照顾到民众趣味,如何适当地维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问题的关键。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要求文学从贵族走向大众,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否定封建等级观念和呼唤普遍的人性作为起点的,表明了强烈的现代性追求,但没有从正面作出阐释。周作人进一步于1918年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但他同时对此作了个人主义的解释,认为平民文学“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12]以个人本位主义顽强地维护着新文学的精英立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为内核,提倡“普遍的”“诚挚的”文学,但他对大众的思想趣味以及其历史作用一直持保守的看法,强调是文学精神的“大众性”,如前文所述,是一种理性的真诚看取人生的主体创作精神。此后,1921年文学研究会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也力图持此立场,“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却万万不可!”[13]但在谈到具体的创作时,他们就显得有所松动了,有人认为创作时要放弃个人风格,因为“个人风格很难引起普遍的趣味,而民众文学里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趣味。”[14]的确,新文学并没有按照周作人的路子走下去,1920年代只有鲁迅、郁达夫等少数几人得周氏之心,文研会和乡土派的大量作品反映了中国宗法制社会在解体的过程中的黑暗现实,描写了民众的悲惨遭遇,抒发了知识分子的激愤伤感情绪和悲悯情怀,这种真切的道德关怀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他们普遍丧失了自己的个人风格,缺少应有的认识和审美深度。“平民文学”的理论内涵没有准确地付诸于文学创作,它在“民众文学”的大讨论中被悬置起来。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文学里,这两个概念还有内在张力的话,那么后来的情况是张力逐渐消失乃至阙如。
从1918年到1921年左右,中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劳工神圣”的呼喊中,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第一次被质疑。民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美化了乡村和农民,“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15]它对新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民粹主义与“民众文学”的倡导裹挟在一起,相互支撑,扭转了中国文学主流的发展方向。如果说晚清倡新小说开了文学大众化的先声,则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的质的规定性品格到这里才得以确定。周作人在1918年12月7日提出“人的文学”,十天后又代之以“平民文学”,虽然仅仅是概念的置换,这种策略性的表达也说明他亦难免受到影响。当时很多小说叙事存在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形象对立”模式,即把知识分子和农民、学徒放在同一个语境里进行对照,通过前者的眼睛来观照后者,这一形象对立的高低比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时代特点,大众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即算是不易为外界思潮所左右如鲁迅者,也于1920年写了《一件小事》这样的作品。另外,知识分子们又为自己不理解民众,和民众之间有难以填平的沟壑而感到困惑。叶圣陶的《苦菜》写“我”与农民福堂对劳动和人生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和理解,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则细致地表现了“我”和学徒定儿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缘故,周围的人竟对他们俩采取如此迥异的态度,作者为之困惑。这些读书人虽然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的地位,但他们已经开始为这种优越而感到不安,这种自我缴械式的不安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历史事实是,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逐步丧失,最后沦为工农兵的学生,接受再教育再改造。
当然,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产生巨大影响、能作为时代精神资源而足以为人法的鲁迅,对民众的文学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的审视,然而毕竟是极少数的。文学语境也在变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锤定音,“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小资产阶级要“作群众的学生”,这种论断和“歌颂与暴露”的讨论互相应和,给大众披上了神圣的面纱。国统区的情况稍有不同,但也不离其宗,当时整个抗战文学里,很少有描写民众出色、值得一读的作品。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算此中翘楚了,叙述者对“差半车麦秸”这个农民兵不是概念化地把握,而是予以了客观细致地描画,甚至带有喜剧式的嘲讽和奚落,但同时又把他的邋遢、委琐写得颇富有诗意,分明已不是从前的阿Q了,耐人寻味。
4
从19世纪末王照、劳乃宣等人倡拼音字母运动,到裘廷梁的俗语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人们一直在努力拆除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语言障壁。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操纵了文言的使用权,凭文言参加科举获取功名,用文言对传统经典进行诠释注疏来强化这一权威,语言的圈子化是文学走向大众的最大障碍,因此文学走向大众,没有比语言的革新更重要的了。胡适的所谓“文学的国语”,力图把白话上升为一种优美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但30年代肇始的大众语运动对它并不满意。瞿秋白甚至极端地认为,“五四”以来的欧化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新文言”,主张再来一次新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16]应该说,“欧化语”是一种应时而生的富有生命力的新语言,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优良传统之一。周作人在1922年曾指出这个称谓容易引起误会,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否定国语改用西语,它“实际上不过是根据国语的性质,使语法组织趋于严密,意思益以明了而确切,适于实用。”[17]“大众语”同“欧化语”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语言使用上难易的差别,而是包含了精英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权利关系,胡愈之认为,“‘大众’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18]说出了大众语最本质的东西,即用大众意识去颠覆新文学以来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启蒙关系。
大众语急切地否定“欧化语”,要“绝对地不依赖汉字,依赖文言去造成一种新的文学的语言”[19],由语言上的革命进而要求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式进行大众化改造。后来的所谓“旧瓶装新酒”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它的延续,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产生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20]这样的观点。抗战时期的文学大众化注重的是所谓“民族形式”,认为大众化就是用旧形式去表现新内容。抗战时期的大众化有两个症结,一是形式和内容被理解为瓶和酒的关系可以相分离,旧形式能不能干净地从旧内容上剥离开来,旧形式能否适当地表现新内容,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的提法显然是不科学,搞不好,徒为保守主义授柄而已;二是民间通俗文学的文体形式被等同于民族形式,大众化在民族抗战的大时代里以民族化的面貌出现,章回体、旧剧、鼓词成为民族形式备受推崇,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被判定为“非民族”的,受到批判。对民间通俗文学旧形式的借鉴,产生了一大批街头剧、秧歌剧、新章回体小说、新民歌,对抗日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有一定的帮助,这种借鉴有特定时代的必要性,但把它夸大为文学范畴里面的创新加以鼓吹,并以此来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进而以政治的手段把这种大众化规定为主流的方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早在1940年就有人把这一趋势恶谥为“新的国粹主义”[21],不算是冤枉。
胡适揭橥白话文学的大旗,找到了白话这一把大众同文学连接起来的基点,又撰写《白话文学史》,向传统文学资源寻源溯流,为新文学确立合法地位。他找到的资源就是民间通俗文学,第一次革命性地把列入另册的民间通俗文学奉为正宗。显然,这种文学的造反举措带有策略性的考虑,若是过分地肯定民间通俗文学,就会成问题,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和《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对民间通俗文学进行了史的梳理,并没有从文学上给予过多的肯定。周作人同样是寻找传统的文学资源,在《新文学源流》中严格地在精英文学的范畴里,论证“言志”和“载道”的交替循环,把新文学认定为“人的文学”,根据这一标准,他痛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22],就包括《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民间通俗文学,而这些正是文学革命需要大加推崇的“活文学”。“人的文学”观对“白话文学”并不是否定,而是很好的补充,因为前者坚持清醒的主体创作精神,不致于使文学走向大众的偏执,这两个口号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五四文学的新传统[23]。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学大众化中“人的文学”精神逐渐被抛弃,在政治的高压下,要求作者放弃独立的创作立场和清醒的主体意识,向大众的趣味——更明确的说是应时而生的意识形态——无条件认同,同时,民间通俗文学以民族文学真正代表的面目出现,被理想化,这在本质上已经疏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
注释:
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②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载《大众文艺》杂志,1928年9月20日;文章称:“‘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时下政治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低级的适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无聊小说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这名字,范围可没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是有些人之所说,应该把它局限于一个阶级的。”
③关于“大众”一词的意义的梳理可参见文贵良:《大众话语:生成之史》,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2000年第3期。
④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现代》杂志,第2卷,第6期。
⑤2000年曾有人提出“休闲文学”的概念,“休闲”是市民文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强调文学作为娱乐和消遣的存在,参见2000年4月25日《文艺报》魏怡、童庆炳等人的文章,以及《常德师院学报》2001年第2期李作霖等的讨论。
⑥朱寿桐:《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⑦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⑧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小说月报》杂志,第13卷11号。
⑨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谈及鸳派文学和创造社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作具体的论述。
⑩关于张资平开设“小说工厂”的传闻,不少人信以为真,但至今查不到确切的证据,不过,在1930年代他作品数量之大是惊人的,五六年里仅长篇小说就有15部,参见鄂基瑞、王锦圆:《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11]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争点》,《中苏文化》杂志,第7卷5期;还可参阅丁易编:《大众文艺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2]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见《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9页。
[13]张侃、王砥之、雁冰:《怎样提高民众的文学鉴赏力?》,陈荒煤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
[14]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第230页。
[15]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16]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1927-1937》。
[17]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18]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23日。
[19]易嘉:《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1927-1937》,第250页。
[20]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二·1937—1949》。
[21]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二·1937-1949》。
[22]周作人:《人的文学》,见《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23]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