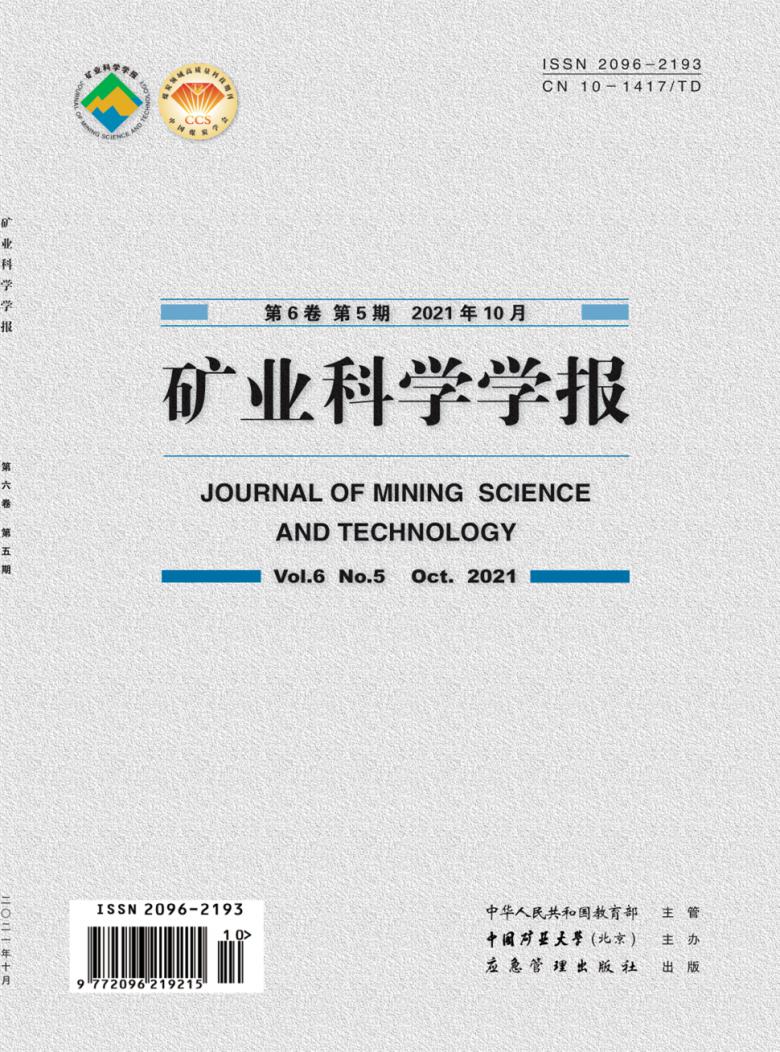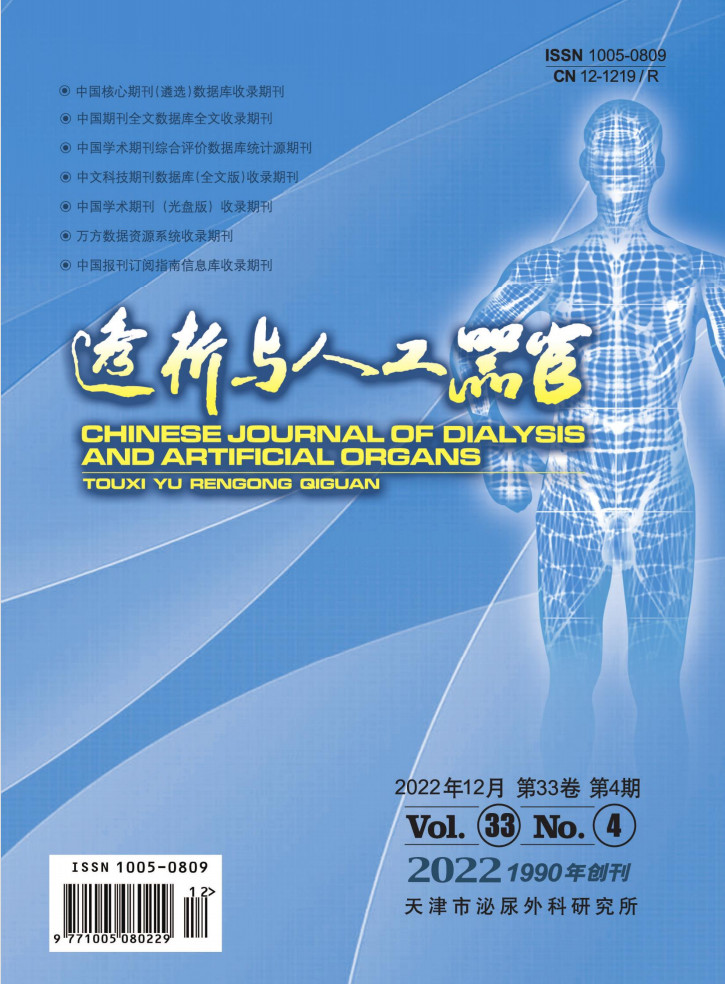宗教与西方环境伦理学
尤金·哈格罗夫 2009-01-21
摘要:林恩怀特争论始于怀特关于对基督教进行重新思考或者由非西方宗教取而代之的呼吁。林恩怀特争论已经被证明成为处理环境危机的一个障碍。由此而起的对基督教的辩护制约了亚洲和其他比较环境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没有产生对环境有益的结果。无论何时,当人们谈及宗教和环境的关系的时候,讨论都会迅速转向有关基督教对环境危机责任的讨论。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怀特的论文在很多方面是对的:基督教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自然的世俗化,并且在中世纪,基督教在政治上对现在看来有害的人口增长的政策提供了支持,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很多诸如此类的政策已经被证明对环境是有害的。但是,基督教还存在另一种对环境友好的传统,Assisi城的“圣芳济”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这种传统也许对于从环境角度重新认识基督教是有益的。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环境伦理的发展,基督教将很难能够有所作为,非西方宗教也不大可能成功地在西方产生出某种环境伦理。因此,对于研究宗教的学者们而言,重要的是要走出谁应该为环境危机受到指责的争论,找到世界各主要宗教如何在其各自的文化范围内对发展环境伦理提供最佳帮助的方法。
关键词:林恩怀特争论;宗教;西方环境伦理学;比较环境伦理学;传统;文化
Abstract:The Lynn White debate, which begun when White called for a rethinking of Christianity or its replacement by a nonWestern religion, has proved an obstacle to dealing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defense of Christianity that followed inhibited Asian and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West and did not produce environmentally useful results Whenever the relationship of religion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raised, the discussion quickly shifted to the issue of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problem with the debate is that in many important ways, the White thesis is correct: Christianity is indeed responsible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in that Christianity desacralized nature and it supported policies politically in the Middle Ages that encouraged now harmful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promo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ch of which has proved to be environmentally problematic There was nevertheless a second tradition of which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was a part that w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that could be useful in rethinking Christianity environmentally It is however unlikely that Christianity will prove usefu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vironmental ethic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or that nonWestern religions will succeed in producing an environmental ethic in the West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hat religious scholars move beyond assigning blame for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find ways for the major world religions to help develop environmental ethics as best they can within their own cultural spheres
Key words:Lynn White debate; religion;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tradition; culture 尽管佛教,尤其是禅宗,在20世纪60年代在学者和学生中间非常盛行,但佛教和其他亚洲宗教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七八十年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极其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有铃木大拙(D T Suzuki)的著作和艾伦•瓦兹(Alan Watts)非常流行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1]人们尤其喜欢将禅宗和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萨特和加缪的哲学相比较。[2] 专业学术期刊上经常刊载论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思想和禅宗之间关系的文章。[3] 然而,除了深层生态学之外,学术界对佛教和亚洲哲学的普遍兴趣并没有延伸至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是70年代早期由阿伦•奈斯(Arne Naess)在挪威创立的一种哲学流派。在美国,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运动广为人知。后来,深层生态学因其对东方思想的不恰当的借鉴受到批评。[4]评论家们认为深层生态学对东方思想的运用是殖民化的、绝对的和帝国式的。 196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美国科学学会有关进步科学的一本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成为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对相应的亚洲维度进行研究的障碍。这篇文章就是由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土壤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所撰写的《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5] 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1)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使得对自然世界的剥削成为可能;(2)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对自然的剥削提供了手段。 怀特用下面的观点总结了他的分析:“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6] 怀特将佛教禅宗看作新宗教的主要候选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禅宗普遍的兴趣,但他又补充写道:“但是,如同西方的经验于基督教一样,佛教禅宗深植于亚洲的历史,因此我很怀疑它是否能够在我们中间获得生机。”[7]他接着建议人们根据Assisi城的圣•芳济的教义来重新思考基督教。圣•芳济是一位因给动物和鸟儿布道而著名的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他被认为是“生态学家的保护神”。 [8] 怀特这篇文章的影响可以清楚地体现在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儿子,斯塔克•利奥波德指导编辑,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和丹尼尔•麦金利(Daniel McKinley)编辑的具有生态学导向的论文集《颠覆性科学》。[9] 这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民族精神、生态学和伦理学”以怀特的文章开始,但并未包括任何亚洲的或者其他比较哲学或宗教。可以确信,当时除了利奥波德这位研究野生动植物管理的教授的“大地伦理”之外,还没有哲学家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因此这类哲学著作的缺乏显得可以理解。但是,迟早会有人意识到,由于编辑们认为第五部分开始的那篇怀特的文章使得任何超越基督教视野之外的讨论都没有必要,所以才出现了没有任何非西方宗教的论文这种奇怪的现象。 怀特这篇文章对早期环境伦理学文献的影响在宗教哲学家约翰•考布(John B Jr)的第一本书《是否太晚?——一种生态神学》的结构中有所体现。[10]这本书的第一章介绍了环境问题;后两章以生态学和工程学为主要讨论的议题;接下来的三章专注于宗教的作用,其中第一部分讨论了“基督教的责任”,反映了怀特的观点。第二部分关于“非西方的自然观”的论述中,他遵从了怀特的观点,认为非西方宗教,包括怀特没有论及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思想都很难对化解环境危机有什么作用。他所讨论的亚洲思想主要是儒家和道家。他在第三部分从圣•芳济(Saint Francis)谈起,讨论了阿尔伯特 施韦泽的观点,接着呼吁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布第一次试图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出发来探讨环境哲学,但该书结尾的三章仍然是有关新基督教的。整本书中,亚洲的思想只是被用来检视由怀特所引发的对基督教的新诠释而已。 同样,两年之后,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摩尔(John Passmore)也在他的反环境伦理的《人对大自然的义务:生态问题和西方传统》一书中将焦点对准了怀特的文章。[11]帕斯摩尔写道:“有关怀特文章的研究成为了一种不断再版的经典。我们很难说他的观点有多少人认同,但我恐怕人们的认同度足以引起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高度关注。”[12]但帕斯摩尔的观点比考布要消极得多。它不仅不想要一种来自于非西方的新宗教,而且也不想修正基督教。该书的前两章,“作为暴君的人”、“托管人精神和与自然的合作”探讨了什么是西方人应该对待自然的恰当的态度。帕斯摩尔为支配自然辩护,声称这正是文明的全部意义,而且声称,与对自然的支配相比,托管人精神不过是西方宗教和思想中没有什么影响的细枝末流而已。 帕斯摩尔在他的书中偶尔提及印度教、佛教、拜火教,认为这些非西方的思想不能作为环境伦理的资源。他认为,伦理“不是那种能够简单的决定去要的东西;‘需要一种伦理’绝不同于‘需要一件新衣服’”[13] 。帕斯摩尔勉强承认环境主义者们也许有可能在西方创造一种环境伦理,但是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对“现有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程度。他之所以愿意承认存在这新伦理出现的可能性是因为“西方传统中存在一些可能被改革者培养成为花朵的‘种子’”[14]。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新伦理,那它不会是来自于东方影响的结果。相反,这种影响是西方给予东方的。他还十分消极地写道,东方哲学和宗教“并没有阻碍日本发展出对人们五官带来强烈冲击的工业文明(译者注:指电子产业)”[15]。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去除垃圾”为题作为总结。在整本书中,东方思想都被隐晦地描述成与西方科学技术相对的神秘主义谬论。 有两本主要的著作对帕斯摩尔的书作出了回应。第一本是罗宾•阿提菲尔德(Robin Attfield)1983年出版的《环境的伦理学》。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与帕斯摩尔的观点进行争论。阿提菲尔德主要是重新思考了西方传统中的控制、支配与托管精神,他认为托管精神比对自然的控制更有影响。我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主张,西方的环境伦理产生于现代的不同领域,如自然历史科学,景观绘画和摄影,景观园林,自然诗歌和散文。[16]阿提菲尔德和我都没有谈及东方传统,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否定东方对建立环境伦理可能作出的贡献,但我们更关注论证西方存在着发展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但是,对西方环境伦理基础的积极关注并不能有助于创造出产生比较环境伦理(东方的环境伦理)的有利条件。 比较环境伦理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只有极少的著作可以认为是环境伦理学文献。可以说,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环境伦理学始于1979年《环境伦理学》这一专业期刊的出版,它为想要在此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发表机会。在此之前,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本期刊不定期的为数量不多的论文提供发表的机会。环境伦理学发展的阻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领域的很多预设与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在整体上是不一致的。对于大多数哲学家而言,直到1975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主流伦理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环境伦理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前景才逐渐变得明朗起来。[17] 当哲学家们艰难地开拓环境伦理学领域的时候,哲学之外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们正在展开一场由怀特的文章所引发的激烈的争论。[18]“林恩怀特争论”与基督教抑制对环境友好的新的非西方宗教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基督教的辩护极大地抑制了亚洲以及其他比较环境伦理。 1982年,当我组织在丹佛大学召开“环境的伦理问题:从宗教的视角”大会时,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林恩怀特这篇文章的消极影响。这次大会本来想开成一次评审大会,但却没有受到一篇有关亚洲和其他比较环境伦理学的论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涵盖这一领域,我将先前PoKeung Ip给《环境伦理学》杂志的投稿《道家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一文纳入进来。尽管PoKeung Ip坚持这篇文章与宗教毫不相干,他还是勉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当我向佐治亚大学出版社提交论文,希望作为原创论文集出版的时候,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变得尤为清晰。当审稿人向出版社推荐出版当时手头上已有文章,包括一两篇从东方视角进行论述的文章时,我竟然发现即使费了很大力气,我也没有再找到任何其他的此类文章。最终,出版社接受了这本名为《宗教和环境危机》的论文集,没有要求我再去寻找有关亚洲及其他比较哲学和宗教的文章。[19]考虑到这种情形出现在距离怀特文章最初出版几乎二十年之后,我很明显地感受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对环境伦理学所造成的非常消极的影响。它极大地阻碍了东方思想对该领域的贡献,将环境伦理学基本上限定为一种西方的学术研究活动。 整个70年代,有关林恩怀特文章的争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基本议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到宗教与环境的关系,讨论很快就会转向基督教对环境危机的责任。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结束了这一争论;但实际上即便在今天,这一争论仍可能在任何时候卷土重来。有关林恩怀特文章的辩论之所以引发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对的,基督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危机负有责任。首先,在欧洲,基督教使得自然世俗化。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将自然想像为充满自然灵魂的,而在基督教里,这种神圣的东西只限于和教堂相关的事物。这种对自然世界的世俗化使得人们更容易开发资源。比如,采伐者在伐木的时候不用再去顾忌树精。 第二,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在整个欧洲实施了的一项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同现在一样,由于教会反对控制生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引起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因此,教会非常支持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以推动更加高效的粮食生产和提高产量。这种对农业技术给予的经济上的支持逐渐转化成为对科学技术普遍的支持。尽管今天我们经常认为宗教和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主要起源于17世纪伽利略和教会关于地球和太阳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的冲突),但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却扮演了今天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即推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哥白尼诞辰5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教会推翻了伽利略有罪的指控,希望借此为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加分。但是,如果天主教教会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因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那么教会就成了环境危机的根源了。 对基督教的辩护一般认为,东方哲学和宗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丝毫不比基督教好。尽管有人认为东方宗教与自然更加和谐,但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环境退化在东方同样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了。因此,基督教是否比东方宗教更加敌视自然并不能造成任何区别,因为没有什么宗教能对未来的环境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从东方寻找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实际上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也许如果没有一个决断,关于林恩怀特文章的争论将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这些议题也将毫无意义地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及。1984年,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作为比较哲学研究所的成员去夏威夷大学进行了定期的访问。1985年3月,为了配合克里考特的访问,亚洲和比较哲学协会决定组织一系列题为“作为环境伦理学精神资源的亚洲传统”的讨论会。1985年12月,在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进行了前两次讨论,第三次讨论于1986年5月在芝加哥亚洲研究年会之际举行,第四次讨论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举行的美国宗教学会会议上进行。这些讨论会上的文章随后发表在《环境伦理学》和《东西方哲学》两本期刊的特刊上。[20]很多来自讨论会的文章也被收入到由克里考特和罗杰(Roger T Ames)编辑的题为《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一书中,并由SUNY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