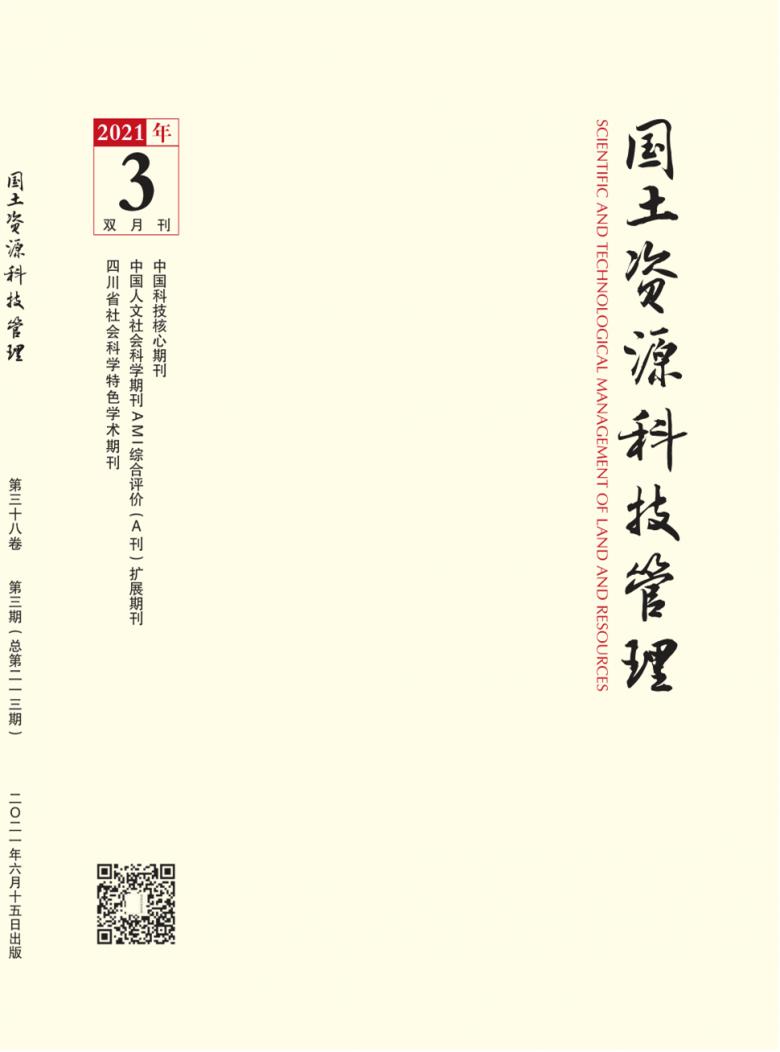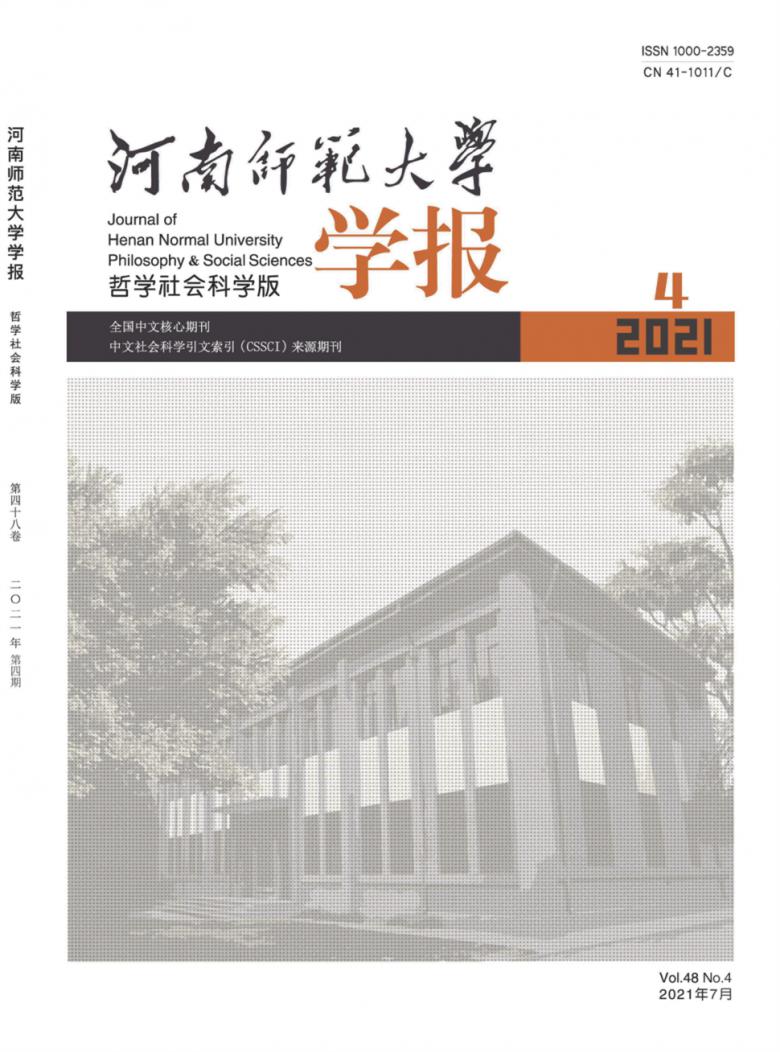让人性自由舒展——试析王安忆文学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反拨
朱恪娴 2010-11-16
论文摘要: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关注人性自由舒展,她质疑儒家“仁义”学说,大胆颠覆旧的道德规范,张扬女性意识,解构封建家长制权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反拔与解构,表达她有关文化与人性的理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王安忆;传统文化:思考
当代女作家王安忆自1984年的美国之行经受中西文化强烈撞击后,开始理性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她以1985发表的(小鲍庄》为开端,相继推出《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反响巨大的佳作。她以人文关怀视角,剖析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悖于人性自由舒展的因素,解构了“仁义”古训,张扬了女性主体地位,鞭挞了封建家长制权威。她的创作也因此日益成熟,由自发写作进入到自觉写作,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界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
一、质疑封建伦理核心。解构“仁义”学说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倡扬“舍生取义”,“仁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关封建伦理的核心内容。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多次涉及这一话题。特别是在她那被誉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小鲍庄》里,这一千百年来的道德礼仪规范颇令人深思。小鲍庄里的人口口声声标榜“仁义”,而实际上人的自主、自由、尊严却倍受践踏。捞渣幼小的生命一降生就遭到忽视;小翠子活泼开朗的天性很快被压抑;拾来与二婶的自由结合,加上外来人的身份遭到全村人乃至孩子们的仇视与欺侮;鲍秉德的女人因不孕而常招丈夫毒打……自以为恪守仁义遗风的人们处处施暴而不自知,一个个披着“仁义”大善的外衣公开实施着人性的恶,轮番上演着一场场扼杀人性的悲剧。王安忆用作品中一个个人物遭遇的命运解剖着人们对“仁义”古训的背道而驰,顶礼膜拜仁义的小鲍庄人根本就没能做到真正的仁慈。在她的另一篇小说《香港的情和爱》中,王安忆再一次表达了对“仁义”的虚伪奉行。小说中的老魏与逢佳决定分手之际,劝她到澳大利亚后找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有爱,我们中国人有义。说“爱这东西不如义,中国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全是一个义。爱只是小善,义,却是大善,爱只对人的,义却是对道理的,你说谁大谁小?爱其实是最不讲信用,只要说一声爱,什么万恶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连良心也交代了,而义却是笃信笃诚,没有空子好钻,也没有便宜占,那些白种人,爱得你死去活来,把你比作耶酥的母亲,可是去吃汉堡包,还是各付各的帐,我们中国人,凭着一份义都是可以送上命的。”“义”被老魏赋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这个香港人作为一有妇之夫,在外与逢佳逢场作戏、始乱终弃,他够不够仁义,是不言而喻的。他帮她出国但要“用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三年”,这种合约是建立在践踏年轻女性人格尊严基础之上的,充分暴露了他对他所推崇的“仁义”的虚假奉行。一如小鲍庄那里的“言”与“行”的极大反差,最崇拜“仁义”者行的多是不仁不义之实,且都没有自我觉察和丝毫的自我反省,这不能不说是对“仁义”的一大讽刺。笔者认为,王安忆文本中似乎并不认同“仁义”的死守,这从她的小说《文工团》中不难发现,文工团曾经招一小男孩演李玉和,男孩长大后一变声就没使用价值了,可团里没把他退回去,而是另外安排到舞蹈队。“我们团从来,从来也不会抛弃不幸的孩子,尽管他穷途末路。像市歌舞团那样,将人招来又打发出去的事我们团是不会干的。这就是从一个旧戏班沿袭下来的文工团的仁义之道。”而文工团兴之所致招来的男女,“这些孩子特别忠实于我们团交付于他们的命运,从没动念要在我们团之外寻求发展。”曾经走到一起,从此就不离不弃,团里辞退员工或员工辞职离团似乎就是种不“仁义”行为,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维持原状,既不利于个体的合理发展也无益于整个团队,如此的“仁义”只会是制约彼此发展的羁绊,所以她笔下所写文工团的命运并不乐观,它急剧下滑,无望振兴。仅仅为了互不相弃,而捆绑在一起,这种忠实履行但不管后果的“仁义”行为,和那些徒有虚名的“仁义”学说一样无疑都令人深思。王安忆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成长、平等生存和合理发展,对打着“仁义”招牌行不仁不义之实的行为,对恪守仁义之道却置真正的发展要义于不顾的观念,均予以了大胆质疑和有力的解构。 二、打破传统道德规范,张扬女性意识
王安忆审判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合理性,大胆颠覆传统道德规范中扼杀人性的因素,张扬女性生命欲望。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禁锢的语境因袭着封建文化中那种重视社会性、轻视自然性的传统人性观,爱情被列为文坛禁区,性被视为人性之淫恶,人的自然属性被极度压抑。1986年4月至9月,她一连发表《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这“三恋”,从人的生命本体价值的角度对“性”予以肯定,细腻刻画生命原欲与文化制约的冲突,在当时文坛引起震撼。王安忆可说是当代首位把性爱当作目的来写的作家,她认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小城之恋》叙述人的自然性在文化规约极度压抑下导致的内心极度不安。被社会规范同化了的个体,内心与本性不一致时所表现出的自责矛盾和痛苦,使小说通篇笼罩在一种社会道德规范的深重制约之中,他与她,男未婚,女未嫁,身份问题的尴尬,道德良心的不允,性欢愉的短暂与空虚,使他们有着不可言说的难堪,转而成为罪恶感的不安,内心的自我审判与听任本能的自我释放构成两极对抗,巨大的罪孽感使他们深陷放纵和忏悔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解脱。“传统观念中,女性充当‘母亲’的权利为社会文化所认可,但是,女性的性欲这一同样真实的权利却时常为社会文化所否决。女性的性欲只能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附带部分,女性单纯的性欲是不洁的,甚至是有罪的。父权制社会压制女性性欲,那些触犯父权制社会的性戒律的女性无一不受到了野蛮甚至毫无人性的摧残。”王安忆通过男女两性的关系拓进人性的复杂层面,寻求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和生命权利、平等与公正。她关心女性的现实生存,“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弥补了以前作家们取消女性欲望的局限,彰显了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她从肯定女性欲望的主体地位出发,对两性欲望的表达呈现出和谐与美的性质。她的《妹头》则反拨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性别价值观,父母为儿子留在上海而让妹头去杭州时,小说多次提到妹头根本没生气,并指出大城市里仍有这种陈腐风气。可见,从女性生命意识的涌动到平等地位的争取,传统观念中凡针对女性的不公平处,作家都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观照,并予以了全面而彻底地颠覆。她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从《岗上的世纪》到《妹头》等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显而易见地多具“硬性”,远比男性强大,在《纪实与虚构》里,就表达了那个家族一连几代都是女性在支撑着家。所有这些都表明,王安忆已经大大超越了那种视女性为男性附庸、仅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性别价值观。
三、鞭挞封建家长权威,体现人文关怀
儒家传统文化要求赋予男性长者以绝对的权威,王安忆审视并看破了这种权威的管制与服从、畏惧与压抑、传统礼教的规范与自觉遵守,敏锐地捕捉到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对正常人性的扭曲。《姊妹们》里男人都以打自己女人来获得征服快感,《荒山之恋》里祖父可以任意用拐杖殴打儿媳。即使内心存有温情,也刻意加以掩饰,不善于也不屑于流露对子女的爱。《伤心太平洋》里小叔叔看“我”父亲演《日出》,“我”父亲在台上“明明看见了他却装作看不见,可心理却得意无比。他从来不正眼看小叔叔一下,为保持他兄长的尊严,这种作派是爷爷的传统。”王安忆解构着父兄形象的神圣崇高和神秘恐怖,揭示封建家长为维护权威形象而刻意制造假像的心理。“爷爷其实最爱父亲,可是他却是使父亲变成最不开心的孩子。”因为“他特别羞于流露他的亲子之情。”父亲去大陆时,爷爷偷偷去码头送。“我父亲不回家的日子,他天天等他回家;等他到家,却作出视而不见的样子,依然骂不绝口。”父权社会里,男性长者为一家之主,拥有绝对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神情严肃,以示权威。作家开掘这些行为的动机只为执着地体现秩序化功能和“代”际标志,表达了正常人性在这种传统文化习惯压抑下的被扭曲。她在《荒山之恋》里,通过大提琴手的怯弱性格形成及其生存困境,折射出封建家长制传统权威下导致的男性人格意志的稚弱。对封建家长制权威桎梏下造成的亲情淡漠、人格成长焦虑,王安忆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她关注人的健全、正常发展,体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